吳敏樹《鶴茗堂百二詞鈔》研究
高德華
(湖南理工學(xué)院 中國(guó)語(yǔ)言文學(xué)學(xué)院,湖南 岳陽(yáng) 414006)
吳敏樹以經(jīng)學(xué)、詩(shī)文知名當(dāng)世,亦能詞,刻有詞集《鶴茗堂百二詞鈔》(下文簡(jiǎn)稱《詞鈔》),內(nèi)有一百二十四首詞。他曾經(jīng)與從弟吳士邁在君山島上建“九江樓”“鶴茗堂”“聽雨樓”與“北渚亭”,“鶴茗堂”的取名與君山茶有不解之緣。吳敏樹在《鶴茗堂記》中寫道:“茶產(chǎn)君山,名天下……天下后世之嗜茶者皆有清風(fēng)兩腋之樂(lè),而無(wú)渴死不得一啜之憂,余之此堂其與有功乎哉?”[1]于同治十一年(1872)春二月初一為《詞鈔》做序。《自序》曰:“余獨(dú)喜誦古人如蘇、黃、辛幼安之作,雖小詞,聲動(dòng)人心,及柳耆卿輩曉風(fēng)殘?jiān)拢嘧杂衅焱の汲侵狻D酥~之一道,故不后于詩(shī)也。”[2]又《自序》曰:“老年詩(shī)趣大闌,忽創(chuàng)新調(diào)......以馀興成詞一闋,殊助嘲笑。遂日為之,凡岳樓、呂亭、君山、湖上及荷塘幼年讀書之寺,無(wú)不有寄。”吳敏樹老來(lái)作詞,風(fēng)格不落前人窠臼,又自創(chuàng)新調(diào),獨(dú)樹一幟。他年輕時(shí)醉心科舉,苦心經(jīng)營(yíng)八股文,儒家經(jīng)世致用思想在晚清士人的追逐之下依舊保持蓬勃生命力。而年至花甲,他卻轉(zhuǎn)向作詞,通過(guò)質(zhì)樸、淳真的語(yǔ)句描繪晚清洞庭湖一隅的農(nóng)村生活。本文將分別從《詞鈔》的內(nèi)容、思想和藝術(shù)等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考察作者及其作品。
1 情感真摯之內(nèi)容
《詞鈔》中一百二十四首詞,大致可分為山水詞、贈(zèng)答詞、悼亡詞、詠物詞、感慨詞等幾類,其中僅贈(zèng)答詞有三十五首。吳敏樹生平交友廣泛,又因文名傳揚(yáng)于當(dāng)世。往來(lái)的朋友中不乏當(dāng)朝權(quán)貴。如官至兩江總督的曾國(guó)藩、晚清外交大臣郭嵩燾、湘軍將領(lǐng)劉蓉、軍事上多有謀劃的趙烈文等。吳敏樹雖出身于鹿角鄉(xiāng)村,亦不乏志同道合的好友。如他詩(shī)中所述:“生居窮僻鄉(xiāng),恨少文墨士。同志得二三,吾意亦良喜。”[3]他與知己毛西垣惺惺相惜,與湘潭名士歐陽(yáng)兆熊多年互通往來(lái),與同鄉(xiāng)方大淳的莫逆之交,與孫由庵同賞洞庭景,無(wú)論友人身份,吳敏樹皆以真摯的感情待之。
1.1 與身居要職的朋友交往
道光二十四年(1844),吳敏樹奔赴北京參加會(huì)試,因崇尚明人歸有光之文而攜帶《歸震川文別鈔》入京,此舉與桐城派文人不謀而合。因此,不少聚集京城的桐城派作家慕名前來(lái)與之結(jié)交,吳敏樹在京城文人圈一時(shí)聲名大噪。正是這一年,吳敏樹與曾國(guó)藩建交。同治十一年(1872),一代名臣曾國(guó)藩去世,吳敏樹為其作挽詞《臺(tái)城路·長(zhǎng)沙迎曾太傅喪》:“江南一片青山路,落日斷霞飛燕。艦引黃龍,潮迎白馬,兩岸旌旗飄轉(zhuǎn)。軍官跪見。看鳴炮吹笳,霜戈明練。羽扇綸巾,晚風(fēng)橋上萬(wàn)人羨。今來(lái)江水恨咽,正臺(tái)星乍隕,丹旐飛旋。楚士哀迎,吳民哭送,山外杜鵑紅遍。殘年眼倦。侭湖海浮云,生涯流電。手折菖華,待靈輀一見”。[4](此詞收入《湘人詞》,又收入《詞綜補(bǔ)遺》。《詞鈔》未載此詞,今據(jù)《詞綜補(bǔ)遺》收錄。)這篇挽詞所流露出的纏綿哀婉之意,讓人痛心疾首。吳敏樹與曾國(guó)藩建交三十余年,二人關(guān)系甚為密切,雖不為曾氏幕僚,卻常為之排憂解難。二人常有書信往來(lái),見《曾國(guó)藩日記》記載。同為晚清湘軍將領(lǐng)的劉蓉,又身為桐城派古文家常與吳敏樹有學(xué)術(shù)交流。同治六年(1867),劉蓉罷陜西巡撫南歸,吳敏樹為之作文《劉孟容中丞歸臥南陽(yáng)圖序》,文中舉顏淵之例安慰好友不要因?yàn)榱T官歸家而陷入困頓之中,又以諸葛武侯之例勸慰友人莫要以出仕作為衡量人生價(jià)值的尺度。劉蓉歸家時(shí),途經(jīng)巴陵,與吳敏樹、郭嵩燾、羅汝懷、高心夔等人同游君山,書有《游君山記》。吳氏作《跋劉仙霞中丞游君山詩(shī)》和《臥盧春·寄劉霞仙中丞》。劉蓉作詩(shī)《寄懷吳南屏學(xué)博王子壽比部》,稱贊吳氏與王子壽為:“大湖南北兩清流,文字相娛到白頭。”[5]由此可見,吳敏樹與劉蓉交往頻繁,私交甚好。吳敏樹結(jié)交的人當(dāng)中不乏當(dāng)朝權(quán)貴,但在互相往來(lái)之余從不利用友人的職務(wù)之便謀利,反而主動(dòng)保持距離,可見吳敏樹的君子品質(zhì)。
1.2 與閑居鄉(xiāng)村的朋友交往
孫由庵和郭建林與吳敏樹的友誼長(zhǎng)久,他們生平絕大多數(shù)時(shí)間寓居在洞庭湖畔的村落,相處時(shí)間甚多,吳敏樹在詩(shī)文中常提及二人。孫由庵與吳敏樹年紀(jì)相仿,都已是古稀之歲的老人了。吳敏樹在《雞談過(guò)·寄孫由庵》一詞中寫道:“前日走來(lái)過(guò)我,喜譚健飯,相看七十年翁。……話長(zhǎng)甚,多惜匆匆。”[2]即使他們?cè)卩l(xiāng)間小道匆匆遇到,依然有道不完的話。在吳敏樹所作《孫由庵六十壽序》中:“由庵孫君年未三十之時(shí),余家延之塾中,教童子句讀,連更八歲,童子皆稍知文義。而由庵為師名益著,乃別開館余里中,里中學(xué)者多從之,其后業(yè)皆成就。”[3]得知,孫由庵是吳家鄉(xiāng)里的私塾先生,在作學(xué)問(wèn)上又志趣相投,因此成為朋友。他們常常一起出游,山園看菊、將臺(tái)山登高、游大云山、中秋賞月……相識(shí)四十年,依舊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可見其感情淳真可貴。
郭建林是一位隱者,他們之間的交往總是離不開呂仙亭。正如詞人所寫:“卻思少日聯(lián)床,語(yǔ)連三夜,何曾半句填空。惺忪呂仙亭下,摩船偷覷窗中。”[2](《仙亭夢(mèng)·寄郭建林翁》)。道光年間,二人同寓呂仙亭,傍晚時(shí)分蕩著小舟,往南津泊船所。郭建林比吳敏樹年長(zhǎng)十余歲,這首詞所作之時(shí),郭建林已至耄耋之年,然精神抖擻。吳敏樹將步入古稀之歲,對(duì)于年輕時(shí)二人的游歷,至今歷歷在目。郭建林超然灑脫之個(gè)性深深影響著吳敏樹,他曾在文章中說(shuō):“自其少壯時(shí),即有灑然之志,不為祿利學(xué),家計(jì)粗足,即不訾問(wèn),亦不遠(yuǎn)出。獨(dú)好遨游近鄉(xiāng)山水,時(shí)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即喜與之游,嘗偕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shù)數(shù)來(lái)余家山館,共晨夕言笑不倦。”[3]郭建林與吳敏樹亦師亦友,相交近五十年,郭建林對(duì)他產(chǎn)生極大影響。在上述詞中,已然揭示其對(duì)待老友真摯的感情。
2 自覺生命觀之思
吳敏樹個(gè)性恬淡,雖久困場(chǎng)屋,卻不疲于治學(xué)修身,曾任瀏陽(yáng)教諭,深受經(jīng)世致用思想影響卻因與同僚不和而辭官。田園生活閑適安逸,亦能時(shí)常自省。他始終保持清醒自覺的生命觀,許是與晚清飄零的社會(huì)背景有關(guān)。天朝大國(guó)淪為半殖民半封建國(guó)家,不僅國(guó)家喪失獨(dú)立自主權(quán),連人民也感受到遮天蔽日的壓迫。吳氏的隱逸之思及敏感的生命意識(shí),對(duì)我們探究其對(duì)生命存在的體驗(yàn)和感悟大有裨益。
2.1 隱逸之思
隱逸即醉心山水田園,隱而不仕,是古代知識(shí)分子為擺脫官場(chǎng)束縛、追求自由生命而做出的選擇。他們自幼飽讀詩(shī)書,才華滿腹,初時(shí)大多躊躇滿志,熱切地渴望在政治舞臺(tái)上大展拳腳,建功立業(yè),但事實(shí)上能得到重用之人寥寥無(wú)幾。失意文人遭受壓抑而苦悶,于隱逸避世之際尋求精神的解脫。莊子稱“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wú)為有國(guó)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6]即是如此。
咸豐元年(1851),吳敏樹四十七歲,因與時(shí)任瀏陽(yáng)的教諭不和,二人矛盾無(wú)法協(xié)調(diào),于是稱病辭去瀏陽(yáng)縣學(xué)訓(xùn)導(dǎo)之職。[7]一年后赴京參加會(huì)試落第,自此吳敏樹決意仕途。當(dāng)時(shí)太平天國(guó)連年戰(zhàn)爭(zhēng)導(dǎo)致詞人無(wú)家可歸,只能借住在岑川好友家中,身邊親友接連生離死別,加之自身年事已高,使得吳敏樹將目光從現(xiàn)實(shí)苦痛轉(zhuǎn)移到自然山水。他幽居洞庭湖畔,自放于山水之間,不僅將自然景勝作為觀賞對(duì)象,更作為隱逸避世的理想場(chǎng)所。郭嵩燾記《吳南屏墓表》:“……有湖山花木之勝。君樂(lè)之,為堂于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渚亭于其左。……視人世忻戚得喪,無(wú)累于其心,以自適其超遠(yuǎn)曠逸之趣。”[8]一語(yǔ)道出吳敏樹尋求山間田野之趣,實(shí)則為暫時(shí)躲避殘酷現(xiàn)實(shí)。《詞鈔》中隨處可見詞人逍遙樂(lè)哉之情狀:“人世風(fēng)波不管,光陰爛漫誰(shuí)收。一壺村酒在船頭,春色無(wú)人消受。”(《江村子·即事有懷》)“最憶岳陽(yáng)樓夜,老方道士,沽酒烹魚。恰有滿樓明月,滿湖秋水,對(duì)飲同渠。”(《希夷夢(mèng)·岳樓憶舊》)“待我騎驢日子,暮暮朝朝,等閑行藥。買酒無(wú)人,尋詩(shī)少伴,也要籠鵝放鶴。閑閑臥,蘧蘧覺。”[2](《青牛引·題洞庭瞿道士屋壁》)類似展現(xiàn)山水田園之樂(lè)的語(yǔ)句比比皆是。吳氏徜徉在煙波浩渺的洞庭湖上,駕一葉扁舟,與三五好友吟詩(shī)飲酒。面對(duì)山水田園景象,詞人視野開闊,心情亦豁然開朗。像歐陽(yáng)修“醉能同其樂(lè),醒能述以文”沉浸山水之樂(lè),吳氏愈發(fā)向往隱逸生活。正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吳敏樹在鹿角的“一畝三分地”既是現(xiàn)實(shí)依托,亦是精神家園。正因?yàn)樗麑?duì)生命內(nèi)在自覺地觀照和重視,使其更能感悟生命價(jià)值與意義,即對(duì)自由的不懈追求。盡管外部環(huán)境紛亂動(dòng)蕩,吳敏樹卻能以內(nèi)心平靜為旨?xì)w,脫離外在的榮耀富貴、功名利祿,安享內(nèi)心的寧?kù)o與自由。
2.2 生命意識(shí)的抒寫
陸機(jī)言“遵四時(shí)以歡逝,瞻萬(wàn)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9],劉勰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10]之感。季節(jié)已不單是節(jié)氣更替,這種節(jié)序性特征與人生命的蓬勃和衰竭具有異質(zhì)同構(gòu)性。據(jù)統(tǒng)計(jì),“春”在《詞鈔》中出現(xiàn)了四十三次。《詞鈔》中未表露憂國(guó)傷時(shí)之懷和懷才不遇之慨之詞,詞人垂垂老矣,對(duì)外物的敏感度不如從前。他隱逸于山水田野之間,于時(shí)事了解無(wú)甚多。同治九年(1870),曾國(guó)藩致信李元度,其言:“局中諸君,南屏翁近稍衰退,研、筠兩處并有失子之戚,左右能綜攬全綱否?”[7]談到吳氏衰老一事。吳氏遲暮之年,身體久病不愈,骨肉偏又相繼離開人世,就連好友亦接連去世。因此,憂生懼死成為人們生命意識(shí)最基本的表現(xiàn)。吳敏樹為兒子寫的悼念詞:“及第做官俱不得,甚剛風(fēng),吹得玉樓春老。”(《痛三郎·追悼三郎式甫》)和追念女兒時(shí)寫道:“今日塵埋纖指盡,那境兒,暗慘無(wú)春。”[2](《度金針》)“春”在詞人眼里是美好生命的象征、是生命的主體。然而事與愿違,年輕的生命悄然逝去。“春”與冷色調(diào)詞匯搭配,觸發(fā)詞人哀婉失落心態(tài)。
又如“錯(cuò)上江船,一度偷來(lái),怨苦兒春”[2](《同舟度·錯(cuò)憶》)更是流露對(duì)春的怨恨和悲愁情緒。在《無(wú)腔笛·自題鶴茗詞卷》:“茶煙花塢,惱甚闌珊風(fēng)雨。短笛無(wú)腔,牧牛兒,那管春將去。山齋路,紅藥闌干,我儂吟處,是一樣斷腸情緒。但不解,敲頭點(diǎn)句。”[2]詞人的“斷腸情緒”因“春將去”而起,激起無(wú)限郁結(jié)愁悶。孔子將人生比作流水,發(fā)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慨,蘇軾也有“哀吾生之須臾,羨長(zhǎng)江之無(wú)窮”的喟嘆。詞人生活的清王朝,亦同詞人一樣“垂垂老矣”,國(guó)運(yùn)日益衰微,危亡日益加深。吳敏樹借助“傷春”詞表達(dá)內(nèi)心的不平和哀怨,直率激切地表達(dá)了自己真實(shí)而又強(qiáng)烈的生命體驗(yàn)。
面對(duì)時(shí)光流逝和空間物換星移,詞人既慨嘆生命的易逝又沉浸于無(wú)垠的宇宙。“春”在詞人筆下亦具備積極的生命價(jià)值,試讀“矮屋低頭,高樓閣手,可有春情柔治。”(《寒香雪·寄彭雪琴宮保》)“快足歸來(lái)春日斜,不結(jié)絇頭待禁,猶然踏破江莎。”(《東坡屐·詠紅鞋》)[2]詞人將熱愛生活、珍視友情融進(jìn)詞作,這是對(duì)生命意識(shí)的自我肯定,亦是詞人頑強(qiáng)獨(dú)立的生命品格的形成及生命意識(shí)表達(dá)方式。
3 老來(lái)作詞之特色
在朱漢民總主編、王興國(guó)主編的《湖湘文化通史》(第4 冊(cè))中提及吳敏樹的詞:“吳敏樹晚年才學(xué)填詞,其詞作保留在《鶴茗堂百二詞鈔》中。但與其詩(shī)文相比,吳敏樹的詞大多是游戲之作,語(yǔ)言通俗易懂,俚語(yǔ)、戲謔語(yǔ)夾雜其間,在晚清詞壇中別具一格。”[11]吳敏樹老來(lái)作詞,此時(shí)他年過(guò)花甲,與壯年時(shí)所作的詩(shī)文相較,沒(méi)有了針砭時(shí)弊、體現(xiàn)民生疾苦的內(nèi)容,他開始頻繁感嘆生命短暫、時(shí)光匆匆,亦時(shí)時(shí)對(duì)生命的意義進(jìn)行思索。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理想的破滅,他通過(guò)作詞來(lái)抒發(fā)暮年時(shí)的復(fù)雜心境。
3.1 沉郁清冷之風(fēng)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言:“作詞之法,首貴沉郁,沉則不浮,郁則不薄。……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fā)之,而發(fā)之又若隱若現(xiàn),欲露不露,反復(fù)纏綿。終不許一語(yǔ)道破”[12]試讀《詞鈔》:“香草還生,楚王何在。”(《短簿來(lái)》)“香草無(wú)魂,杜鵑有血,啼斷青楓古道。”[2](《屈潭浪·追悼彭女四姑》)吳氏詩(shī)歌,常用香草意象表達(dá)悲傷憂郁情結(jié)。在詞創(chuàng)作中,亦延續(xù)這一寫法,借以抒發(fā)內(nèi)心悲苦凄冷之感。屈原吟“紛吾既有此內(nèi)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贊美香草的美好品質(zhì)。香草指香花善草,亦比喻高潔的人格。《離騷》中所出現(xiàn)的香草種類多達(dá)二十馀種,在屈原作品中,詩(shī)人與香草已然合二為一。“‘香草’在詩(shī)人眼里并不是毫無(wú)生機(jī)的物體,而是一個(gè)充滿著生命意識(shí)和情感理性的替代物,它是詩(shī)人藝術(shù)表達(dá)與情感發(fā)泄的媒介。”[13]再讀“山鬼奉文,湘君結(jié)珮,拌與騷家作使。”(《土地神·過(guò)松源村重吊西原子》)“重遇,有一輩騷人,九霄天女。幾陣靈風(fēng),掃盡淫虹酸雨。”[2](《青鸞復(fù)·擬題北渚新亭》)“山鬼”“湘君”“天女”等形象,皆出自屈原作品《九歌》,與洞庭湖鬼神信仰有所關(guān)聯(lián),這些意象神秘莫測(cè),屈原賦予其生命力。吳氏所居住的鹿角鎮(zhèn),與屈原流寓的沅湘一帶,皆處于洞庭湖濕地區(qū)域。湖湘文化深層的憂患意識(shí)及悲情的審美觀,奠定了湖湘文化憂國(guó)憂民的悲情傳統(tǒng)。吳敏樹自然繼承發(fā)揚(yáng)屈騷精神,將其意象融入詩(shī)詞中,凝結(jié)成沉郁清冷之詞風(fēng)。
此外,詞人對(duì)色彩的運(yùn)用相當(dāng)頻繁。色彩是巧妙地刺激視覺、敏銳地接收情感的語(yǔ)言,亦是傳達(dá)信息的有效指示。他選用冷色或暖色調(diào)色彩,卻故意在色彩詞前面或后面加上凄冷或幽清的字詞,如“冷”“寒”“恨”“愁”“暗”等,使他的詩(shī)歌籠罩在凄涼清冷的氣氛之中。如“卅七年聽雨樓頭,一場(chǎng)灰冷。”(《三生石·聽雨舊樓題壁》)“夜色向深宮,春將人影紅。華燈萬(wàn)盞日曈曈,暗淡當(dāng)中。”(《正面紅·詠宮燈》)[2]將個(gè)人的痛苦揭露無(wú)疑,詞作亦因此呈現(xiàn)更深層次、更耐人尋味的美,蘊(yùn)含了雙重美感。
3.2 俚語(yǔ)俗事入詞
清代是詞發(fā)展的中興時(shí)期,清代詞學(xué)創(chuàng)作是繼宋朝以后的又一個(gè)高峰。創(chuàng)作實(shí)踐和詞學(xué)建構(gòu)都有前人豐富的填詞經(jīng)驗(yàn)和詞學(xué)批評(píng)為基礎(chǔ)。吳敏樹的詞創(chuàng)作始于同治年間,清王朝剛剛經(jīng)歷中英鴉片戰(zhàn)爭(zhēng)、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封建帝國(guó)統(tǒng)治即將分崩離析。他沒(méi)有順應(yīng)時(shí)代發(fā)展“以詞寫史”,反而只關(guān)注眼前一方天地。一直生活于鄉(xiāng)村田野的吳氏,對(duì)農(nóng)村生活相當(dāng)熟悉。他崇尚黃山谷,亦學(xué)其以俗為雅的特色,以俗事俗物入詩(shī),語(yǔ)言上趨于通俗化,運(yùn)用俗語(yǔ)方言。除黃山谷外,還有秦觀亦喜將俚語(yǔ)入詞。陳廷焯評(píng)“少游名作甚多,俚詞亦不少。”[12]吳氏將俚語(yǔ)俗事入詞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與上述二位如出一轍。試讀《團(tuán)圓福·拜年》:“大門關(guān)了,索錢人去,大家樂(lè)飲銜杯。鄉(xiāng)俗從來(lái)多禁忌,不要沖開燈籠過(guò)好,妨聲息,莫是人來(lái)。團(tuán)圓今昔無(wú)猜,辭年了,分咐安排。老人雙健,孫兒又乖,又是小姑來(lái)嫁,新婦初來(lái)。先生醉,分些爆竹,鑼鼓同催。”[2]將湖湘地區(qū)拜年時(shí)的民俗與禁忌及其樂(lè)融融的熱鬧情形描摹得生動(dòng)有趣,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如同對(duì)鄉(xiāng)村生活臨摹的描寫方式,使詞更貼近生活,充滿人情味。又如“廚前磨豆腐,房中忙老鼠。”(《年故事·詠小年》)“只得耐煩守住,千金一刻,放爆聲鑼。”(《金尾蛇·除夕》)“看天門跌蕩,一年保佑無(wú)災(zāi)。吾家早,他家驚起,也放春雷。”[2](《開天門·出天行也》)這一類方言俗語(yǔ),乃至諺語(yǔ)、俚語(yǔ)一經(jīng)他手就別開生面。對(duì)節(jié)日氛圍烘托大有裨益,別有一番鄉(xiāng)村野趣。《白石道人詩(shī)說(shuō)》有言:“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14]吳敏樹從鄉(xiāng)村生活中汲取那些俏皮活潑、淳樸率真的口頭語(yǔ)言為文學(xué)注入新活力。
晚清詞壇以王鵬運(yùn)、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為主導(dǎo),行其道以詞體推尊為目的。吳敏樹反其道而行之,沒(méi)有局限在填詞,自創(chuàng)詞調(diào)。《詞鈔》中一百二十馀首詞,無(wú)一沿用前人詞調(diào),皆為自創(chuàng)。例如“江南樂(lè)”“姑蘇臺(tái)”“大名歸”“巴東野”“仙亭夢(mèng)”“烏有生”“寒香雪”“臥盧春”等詞牌,為吳氏新創(chuàng)。筆者依據(jù)清代萬(wàn)樹《詞律》對(duì)照《詞鈔》,亦只有五篇詞律對(duì)應(yīng),是晚清詞壇一創(chuàng)舉。
4 結(jié)束語(yǔ)
吳敏樹的《鶴茗堂百二詞鈔》具有鮮明的湖湘地方色彩,而至今無(wú)人對(duì)其詞進(jìn)行研究考察。綜上可見,吳敏樹獨(dú)創(chuàng)詞調(diào),樹一家之幟,這在晚清湖南文壇是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就清代詞史而言,清代是詞學(xué)的中興期,詞人詞作大量出
現(xiàn),清代詞人凡乎人人有詞集。文人廣泛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對(duì)清詞風(fēng)格的多彩及變化皆有很深的影響。《鶴茗堂百二詞鈔》中,大部分詞均自創(chuàng)詞牌名,語(yǔ)言通俗易懂,俚語(yǔ)、戲謔的詞參雜其中。然而吳敏樹在給曾國(guó)藩作挽詞《臺(tái)城路·長(zhǎng)沙迎曾太傅喪》時(shí),遵守了作詞的常規(guī),可見他作《鶴茗堂百二詞鈔》并非不懂詞律,而是刻意為之。詞的創(chuàng)作是文人個(gè)體創(chuàng)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對(duì)詞人的詞風(fēng)做出全面評(píng)價(jià)。《鶴茗堂百二詞鈔》展現(xiàn)了晚清湖湘儒士的概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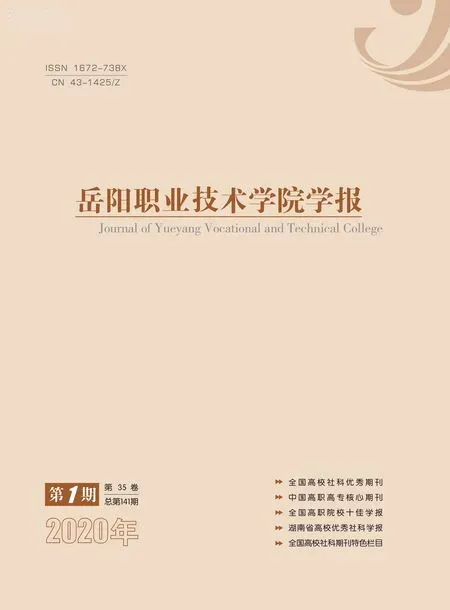 岳陽(yáng)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0年1期
岳陽(yáng)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0年1期
- 岳陽(yáng)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廣東省蔬菜出口競(jìng)爭(zhēng)力研究
- 湖南城市旅游形象認(rèn)知研究
——以岳陽(yáng)、長(zhǎng)沙、衡陽(yáng)三地為研究對(duì)象 - 中職學(xué)校學(xué)業(yè)水平考試背景下的微課教學(xué)實(shí)踐與思考
——以“計(jì)算機(jī)應(yīng)用基礎(chǔ)”課程為例 - 高職“電子產(chǎn)品開發(fā)”課程創(chuàng)客式教育教學(xué)的實(shí)踐與思考
- 英文原版電影在高職英語(yǔ)翻轉(zhuǎn)課堂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
- 學(xué)生標(biāo)準(zhǔn)化病人教學(xué)法在“基礎(chǔ)護(hù)理技術(shù)”課程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