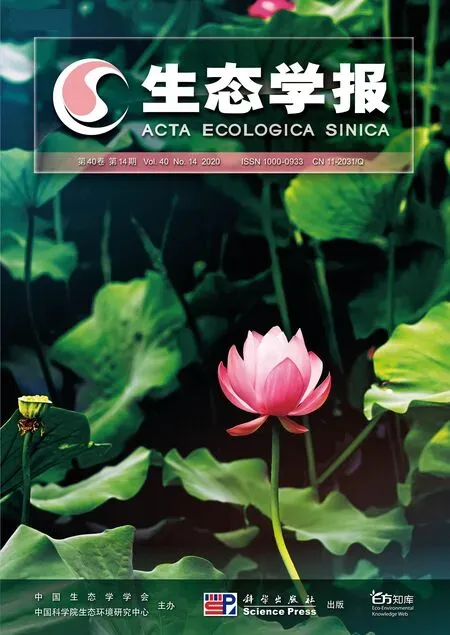中國森林生態系統凈初級生產力時空分布及其對氣候變化的響應研究綜述
徐雨晴,肖風勁,於 琍
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 北京 100081
森林生態系統是地球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具有很高的生物生產力、生物量以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其碳儲量占整個陸地植被碳儲量的80%以上,每年碳固定量約占整個陸地生物碳固定量的2/3[1],因此它對于維護全球碳平衡具有重大作用。森林與氣候之間關系密切,大氣中CO2平均每7年通過光合作用與陸地生物圈交換一次,其中70%是由森林進行的[2]。氣候變化特別是降水和溫度的變化,對森林植被的生長具有重要的影響,而由氣候變化引起的森林分布、林地土壤呼吸和生產力諸方面的變化反過來也可對地球氣候產生重大的反饋作用。
森林植被凈初級生產力(NPP)是通過植被光合作用在單位時間和單位面積所產生的有機物質總量與自養呼吸之差。NPP作為表征植被活力的關鍵變量,能直接反映出植物群落在自然環境條件下的生產能力[3],也是衡量植被固碳能力的最主要指標,關系到生態系統對CO2引起的溫室效應緩解作用的強弱[4]。森林生態系統NPP的微小變化都會引起大氣中CO2濃度較大幅度的改變,從而導致氣候的變化[5],因而它也是地表碳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判定碳匯/源和調節生態過程的主要因子[6]。另一方面,近百年來全球氣候發生了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變化,極端天氣氣候事件趨多趨強,這對陸地生態系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表現之一就是植被生產力的變化[7],且陸地植被生產力對氣候的變化十分敏感。
鑒于自然環境下的森林植被生產力能夠反映陸地生態系統的質量狀態、對碳平衡和全球氣候變化均具有一定的反饋作用,因而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開展森林生態系統NPP的評估,直接關系到地球的承載能力及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助于認識氣候變化與森林生態系統的相互作用機制,對于深刻理解和研究陸地碳循環和全球變化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對于區域地表植被估產、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利用也都有著一定的指導作用。
綜合國內外目前的NPP研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在時間序列上的波動情況;2)空間分布特征,包括經緯向變化規律,區域之間以及氣候帶之間的變化與差異;3)驅動因子;4)估算方法。由于森林生態系統本身的復雜性、野外測定困難,同時也受人類活動影響等原因,目前國際上對森林生態系統NPP的時空格局分異及生物地理學機制的認識還不能達到精確評估的需要。
中國不僅具有從溫帶到熱帶、從濕潤到干旱的不同氣候帶,也具有從北方針葉林帶到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和熱帶雨林的多樣性自然植被[8]。我國已有大量針對近幾十年尤其是20世紀80年來以來國家和區域尺度上植被NPP時空分布的研究,其中專門針對森林生態系統NPP的研究也有不少。研究尺度多為全國范圍或者片段式區域,以行政區或流域尺度最為多見。然而,這些研究總體比較分散,其中部分研究的結果、結論并不一致,甚至相悖,尚缺乏異同性分析與比較,也缺乏系統性和綜合性。這并不利于全面掌握我國相關研究的整體情況、了解清晰明確的研究結論以及進行更深層次的規律及原因探究,也非常影響對森林NPP的精確評估及機理認識,因而,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整合和總結非常有必要。鑒于此,本文收集了近幾十年我國植被NPP研究的主要相關文獻,依據其研究結果,系統地綜述了全國及區域尺度森林生態系統NPP的時空分布規律及未來可能變化趨勢,揭示出NPP與氣候因子的關系及對氣候變化的響應情況,并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為以后進一步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索引和參考作用。
1 NPP估算方法
全球不同尺度下NPP估算大致經歷了站點實測和模型估算兩個階段。1960—1970年代,國際生物圈計劃對不同生態系統類型展開了大量的野外調查,第一次對生物圈尺度的生物量和生產力進行了分析。野外調查獲得的實測數據比較可靠,但很難進行大范圍比較均勻的實地調查取樣,因而難以進行大區域乃至全球尺度NPP估算,更無法就NPP對未來氣候變化的響應做出機理性預測。模型估算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因而成為研究大尺度空間范圍NPP分布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由于實測方法測定結果的準確性是模型估算方法無法企及的,因而很多模型估算結果往往需要利用實測結果進行驗證和訂正。目前,國內外關于估算NPP的模型有20多種,大體可分為統計模型、過程模型和參數模型三類,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氣候生產力模型。包括統計模型和半經驗半理論模型兩大類,它是利用年均溫度和年降水量等氣候因子與實際測量NPP之間的統計關系而建立的回歸模型,其優點是模型簡單、應用方便,缺點是不同的研究區域誤差可能較大。統計模型是較早期出現的經驗模型,半經驗半理論模型是統計模型的進一步發展,主要引進了植被凈輻射和輻射干燥度等因子,增強了模型的機理性。但是,由于半經驗半理論模型是在土壤水分供給充分、植物生長茂盛條件下的蒸發量來計算植物NPP的,對于世界大多數地區該條件并不滿足,因而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區應用時估算值偏高[9]。氣候生產力模型主要有Miami模型、Thornthwaite Memorial模型、Chikugo模型、朱志輝模型和周廣勝模型。
生物地球化學模型(又稱機理模型或生理生態過程模型)。是通過對植物的光合作用、有機物分解及營養元素的循環等生理過程的模擬而得到的,可以與大氣環流模式耦合,因此可以用這類模型進行NPP與全球氣候變化之間的響應和反饋研究。由于其較強的機理性和系統性,所以該類模型的可靠性比較高,在不同條件下均可以詳細地描述生物學過程[9]。該類模型主要包括BEPS模型、Century模型、Biome-BGC模型、CEVSA模型等。
光能利用率模型(遙感數據驅動模型)。是基于資源平衡觀點以植物光合作用過程和Monteith提出的以光能利用率為基礎建立的[9],模型簡單,可直接利用遙感數據。1990年代出現了估算NPP的遙感模型,近年來隨著遙感技術的興起和發展,以遙感數據驅動的植被NPP估算得到迅速發展和應用,成為一個主要發展方向。光能利用率模型使區域及全球尺度的NPP估算成為可能,但其生態學機理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國際上最流行的NPP遙感估算模型包括CASA和GLO-PEM。CASA模型是光能利用率模的典型代表,主要通過遙感的技術方法,以NDVI為驅動,借助于主要的驅動因子(氣溫、降水量、太陽輻射量等)計算植被NPP值。
生態遙感耦合模型是綜合了生理生態過程模型和光能利用率模型的優點,通過葉面積指數將二者整合起來,可以反映區域及全球尺度的NPP空間分布及動態,增強了陸地NPP估算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表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
除此之外,近年國內外不斷出現基于森林清查數據進行的NPP估算研究。我國森林資源清查體系已有40多年的歷史,在此期間積累了大量森林資源清查樣本數據,尤其是以省為單位的數據,這使得用清查數據估算森林生物量和生產力成為一種合理可行的方法,并成為生態學家們關注的焦點之一。例如,王玉輝等[10]曾成功探討利用森林資源清查資料的方法估算落葉松人工林和天然林生物量和生產力,并發展了估算公式。還有研究認為,基于樹輪資料重建區域植被的NPP是可行和有效的,然而,此方法有可能導致對陸地生態系統生物量的低估現象出現,相關研究仍處于初步階段[11]。
2 全球森林NPP總體分布
從對全球森林生態系統NPP的研究來看,其領域主要涉及全球緯度格局、不同區域及不同氣候類型區間的差異等幾個方面:緯度梯度控制著氣候的空間變異規律,直接影響著溫度和降水格局,這一方面影響植被的光合、呼吸等生理過程,另一方面影響土壤的形成和變化過程,從而對森林NPP具有一定的決定作用。其中,就緯向分布而言,全球森林生態系統NPP在赤道附近最大,隨緯度升高而顯著降低,緯度每升高1°NPP約減少11.05 gC m-2a-1,北半球及其區域NPP的這種緯向變化規律更明顯[12]。例如,北半球地區緯度每升高1°NPP約減少11.71 gC m-2a-1,而南半球地區NPP未呈現出顯著的緯向變化規律;在亞洲、歐洲和北美洲區域,緯度每升高1°NPP分別約減少17.10、23.689 gC m-2a-1和9.639 gC m-2a-1,而在南美洲區域NPP卻未呈現出緯向變化規律[12]。就區域差異而言,全球各大洲之間森林生態系統NPP整體上差異不顯著,只有南美洲顯著高于亞洲、歐洲和北美洲[12]。就不同氣候類型區而言,森林生態系統NPP分布差異性很大,然而,相關研究結果并不一致,甚至有些結論相悖。例如:有研究[13]表明,全球森林生態系統NPP呈現出從寒冷性氣候區域向溫暖性氣候區域逐漸增大的趨勢,熱帶區域顯著高于溫帶區域;但也有研究[14]指出,熱帶區域森林生態系統地上部分的NPP與其他氣候區域沒有顯著差異,甚至低于溫帶區域。
3 中國森林NPP分布格局及其變化
3.1 近幾十年中國及其區域森林NPP分布
我國森林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南交通不便的深山區和邊疆地區以及東南部山地,而廣大的西北地區森林資源貧乏。東北地區的森林資源主要集中在大興安嶺、小興安嶺和長白山等地區。東北林區是我國最大的天然林區,橫跨溫帶和寒溫帶兩個氣候帶,屬于針闊混交林與北方針葉林的過渡區域,形成溫帶落葉闊葉林、溫帶針闊混交林和寒溫帶針葉林3個基本林區。西南地區的森林資源主要分布在川西、滇西北、藏東南的高山峽谷地區,主要林區處在橫斷山脈,西南林區是我國第二大天然林區。南方地區森林資源分布比較均勻,人工林占很高比重。武夷山系和南嶺山系較為集中,有林地面積占南方地區總面積的45%。
中國植被NPP年均值在空間上的分布格局的研究結果總體差異不大,其中最為具體和定量化的結果如下:沿經度方向,水分由西北向東南逐漸增加,潛在自然植被NPP與水分的分配格局總體保持一致,且NPP隨著經度的增加而增大,具體為NPP在經度73°—98°之間較小(小于200.0 gC m-2a-1),隨后隨經度的增加而增大,到128°時最大(498.1 gC m-2a-1);沿緯度方向,NPP與熱量由南向北逐漸遞減的分配格局大體保持一致,總體呈現出“U”型遞減模式,具體為NPP在18°時最大(722.8 gC m-2a-1),隨后遞增至39°時最低(為79.8 gC m-2a-1),遞增至51°時又達到高值(499.5 gC m-2a-1)[15]。關于近幾十年來中國植被NPP年際變化趨勢方面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有研究[15]認為,中國潛在自然植被NPP總體保持上升趨勢,也有研究[16]表明,中國植被的NPP在經歷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長期后陷入停滯。
中國不同氣候帶森林NPP變化范圍為261.9—724.959 gC m-2a-1[17],這一范圍值后來已得到絕大部分實測和模擬結果的驗證。例如:利用遙感估算模型得到中國典型落葉針葉林NPP實測平均值為490 gC m-2a-1[18]及477.74 gC m-2a-1[19]。區域上,采用集成生物圈模型模擬大小興安嶺森林植被NPP年均值為494.79 gC m-2a-1[20],采用CASA 模型得出1992—2012年東北落葉針葉林NPP年均值為358.7 gC m-2a-1、落葉闊葉林NPP年均值為424.99 gC m-2a-1[21]。運用Biome-BGC模型模擬的1980—2013年長白落葉松林NPP變化范圍為286.60—566.27 gC m-2a-1,均值為477.74 gC m-2a-1[19];模擬的1960—2011年長白山闊葉紅松林NPP變化范圍為473.28—703.44 gC m-2a-1,均值為611.71 gC m-2a-1,近似于基于樣地實測的NPP均值594.66 gC m-2a-1[22];模擬的長白落葉松人工林NPP變化范圍為272.79—844.80 gC m-2a-1,與基于樣地實測的NPP具有很好的一致性[23];模擬的北京山區華北落葉松林NPP為225.49—519.38 gC m-2a-1[24]。然而,也有少數模型模擬的長白山闊葉紅松林NPP值接近或超過了這一范圍上限,且不同模型的模擬結果差異較大,例如,通過EPPML過程模型的模擬值為1084 gC m-2a-1[25],通過回歸模型的模擬值為769.3 gC m-2a-1[26],通過GLOPEM-CEVSA模型的模擬值為722 gC m-2a-1[27]。
中國森林NPP年總量的估算值差別較大,有的研究[28]中為400×1012—640×1012gC/a(0.4—0.64 PgC/a)。也有研究表明[29],當氣溫平均升高1.5 ℃、降水平均增加5%時,中國植被NPP年總量由2.645×1015gC/a增加到2.80910×15gC/a,平均增加6.2%。
從研究的空間尺度來看,已有研究[30]表明,國內的NPP研究集中在全國以及東北、華北等區域。從本文的文獻搜集情況來看,目前對我國森林NPP時空演變以及對氣候變化的響應研究中,以東北、東南林區較為多見,以西南林區最為少見。
3.1.1東北林區
從地形分布看,東北林區山地植被NPP最高,平原植被區次之,高原區最低[31]。分析東北不同森林地區的NPP發現,貢獻率最大的是落葉闊葉林,以溫帶軟闊葉林最大,NPP平均水平為577.2 gC m-2a-1;溫帶針闊混交林NPP年總量最高(17.001×1012gC/a),占NPP總量的27.16%[32]。完達山系和長白山脈地區主要以落葉闊葉林和溫帶常綠針葉林植被為主,受海洋氣候影響,水熱條件充分,植被NPP值相對較高,在700 gC m-2a-1以上;大興安嶺東麓、小興安嶺地區植被主要以溫帶針闊混交林和落葉針葉林為主,受溫度條件限制,NPP值在600—800 gC m-2a-1[31]。1992—2012年落葉針葉林及落葉闊葉林NPP整體上均呈現出從東南向西北遞增趨勢,分別集中分布在大小興安嶺山區,以及長白山地區與遼東半島;NPP值變化范圍大致相同,分別為235.51—439.11和237.94—435.38 gC m-2a-1[21]。
從時間動態來看,植被NPP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季節和年際變化兩方面。對于年際變化,總體而言近幾十年來東北地區森林生態系統NPP在不同氣候情景下的模擬結果基本一致,且模擬結果一般高于或近似于NPP實測值,均表現出波動上升趨勢。東北地區植被NPP的這種提高,很可能是受氣候變化的系列影響,如:地區氣溫升高、多年凍土退化、凍土凍融時間縮短,植被發芽期提前、落葉期推后導致植被生長期延長[33]。
3.1.2東南林區
中國東南部植被年均NPP總體上呈現出從南到北、由東至西逐漸減少的態勢,不同植被類型間差異明顯,以常綠闊葉林最高,落葉針葉林最低[34]。從變化趨勢來看,近10年(2001—2010年)來我國東南植被NPP整體上略有減少,其中南部地區明顯減少,北部地區明顯增加[34]。關于東南林區NPP的研究相對有限,目前主要是以省市為單位或更小空間范圍的零散報道。例如,采用Biome-BGC生態過程模型模擬結果[35]表明,1991—2005年福建省森林NPP總量年均值為2.04×108gC/a,單位面積NPP年均值為759.63 gC m-2a-1,從區域分布來看,NPP高值區主要分布在閩中、閩西兩大山帶海拔高受人類活動影響小的森林分布區;另有研究[36]指出,福建省常綠闊葉林的NPP為1800 gC m-2a-1。采用周廣勝模型模擬出1954—2009年浙江天童地區常綠闊葉林NPP升高趨勢極為顯著(50—60年代呈下降趨勢,60年代之后呈振蕩上升趨勢),年均值為1219.6 gC m-2a-1[37];天童地區木荷米櫧林NPP年均值為2116—2555 gC m-2a-1[38]。江蘇省南京市森林NPP由北向南呈現逐漸增加的特征,最南部地區NPP大于1300 gC m-2a-1[39]。
3.1.3西南林區
對我國西南林區NPP的研究更為有限,相關報道也更為少見且比較零散,基本上是以地區植被NPP的研究為主。例如,對西南地區的研究表明,2001—2011年西南地區植被NPP均值為540.33 gC m-2a-1[40];橫斷山區 2004—2014 年植被 NPP 在整體上呈波動增加趨勢,全區NPP年總量變化范圍為183.768×1012—223.239×1012gC/a,多年均值為208.498×1012gC/a;NPP年均值變化范圍為408—496 gC m-2a-1,多年均值為463 gC m-2a-1[41]。
3.2 未來中國森林NPP分布
目前,對未來我國植被NPP的預估研究也還非常有限,已有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氣候情景各異,結論也千差萬別。對于未來我國植被NPP的變化而言,有研究[42]表明,33°N以南NPP將顯著增加;33°N以北,NPP增加較少,局部地區生產力甚至下降。這與區域研究中氣候變化將導致未來我國北方地區森林NPP明顯增加的結論不一致:在未來溫度增加2.5℃、降水增加12%、CO2濃度加倍的情景下,長白山闊葉樹和紅松林的NPP增幅分別為27.87%和23.96%[22];未來氣候變化將導致我國東北地區森林NPP明顯增加[43-44];未來氣候情景下中國新疆天山云杉NPP也將會增加26.4%—37.2%[45]。也有研究模擬出未來氣候變化引起的森林NPP在不同空間上的增加,如:到2030年我國森林NPP將由東南向西北遞增1%—10%不等的幅度[46]。還有模擬預估結果表明,21世紀末(2090—2099年)A2、A1B、B1情景下我國植被NPP平均值依次由高降到低。其中,3情景下NPP最低值均在本溪,分別為895、953、886 gC m-2a-1;最高值在A1B、A2情景下均在瓊海,B1情景下在桂平,分別為2927、2719、2826 gC m-2a-1[47],也均表現為不同程度的增加。
未來植被NPP對氣候變化的響應情況比較復雜,不同森林植被類型間差異性很大。一般而言,NPP對降水變化將為正響應;對溫度變化正負響應均有,但對溫度的響應強于對降水的響應;對CO2濃度變化為正響應或無響應。例如:有研究表明,在未來A2和B2情景下植被NPP與降水量增加呈正相關,與溫度升高呈負相關,其中溫度升高對NPP的負效應要大于降水量增加對NPP的正效應[19]。在未來CO2濃度、溫度及降水同時增加的情景下,長白落葉松林NPP明顯增加;單獨增加溫度會減小長白落葉松林的NPP,而降水及CO2濃度增加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NPP的增加,但降水增加的正效應明顯弱于溫度升高的負效應[23]。也有研究表明,未來單獨升高溫度或增加降水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闊葉紅松林NPP的增加,但降水明顯弱于溫度的作用;CO2濃度加倍與溫度、降水同時增加的情景下闊葉紅松林NPP也將明顯增加,然而,單獨升高CO2濃度對闊葉紅松林NPP沒有明顯的影響,但能促進長白落葉松林和華北地區典型油松林生態系統NPP的增加[15]。
綜上,由于生態系統本身及外界環境影響的復雜性、測定標志不統一、數據處理方法不同等各種原因,導致目前的研究中對NPP的定量描述結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NPP長期動態變化特征也可能存在差異。然而,NPP的這種整合研究能夠有助于全面掌握全國大范圍以及特定區域特定生態環境條件下NPP的時空分布特征及動態變化規律,充分反映出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響應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對NPP研究數據的積累和有效整合,對于大數據時代基礎數據庫的創新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為生態系統的脆弱性評估以及自然植被資源適度利用和科學管理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
4 氣候因素對中國森林NPP的影響
植被與氣候因子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耦合關系。氣候通過改變環境條件在植被的生理結構、過程等方面控制植被NPP的形成,因而NPP的變化能直接反映植被生態系統對環境氣候條件的響應。在千年尺度上,氣候變化是區域植被變化的主要原因,而非氣候因子僅處于次要地位。近幾十年氣候因子的變化已經引起森林生態系統植被分布和生產力等多方面的變化[48]。其中,溫度、降水、大氣CO2濃度、太陽輻射和地表蒸散的空間格局是影響植被NPP分布和碳收支的重要控制因素。目前大量研究分析了植被NPP與這些氣候因子之間的關系,尤其以前三個因子的研究居多。
4.1 單因子的影響
4.1.1溫度的影響
溫度對森林NPP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研究區域、時段差異以及與其他因素的協同作用其結論不盡相同。升溫同時控制著植被光合和呼吸兩個過程,對這兩個過程的影響決定著生態系統NPP的升高或降低[49],即存在正負兩方面的效應:
一方面,單獨溫度升高對森林生態系統NPP產生抑制作用,因為升溫可增大植被呼吸速率,加速植被的干物質消耗,不利于森林植被對營養物質的累積。同時,升溫會加劇土壤水分蒸發,導致森林植被水分脅迫增強,植物為了避免體內水分的大量流失,氣孔關閉,降低光合作用速率,從而限制植被生長。目前的研究中,升溫對NPP抑制作用的研究結果相對較少,主要有對長白落葉松林[19]、北京主要森林[24]等的研究。
另一方面,升溫也可以加快森林生態系統內部物質循環進程,加快植被光合作用速率,延長植被生長季,從而提高植被的NPP[50]。升溫在一定程度上還可加速土壤凋落物的分解,促進土壤養分的礦化,加快養分的釋放以及增加養分對植物生長的有效性[51]。許多中高緯度森林的生長均在一定程度上受氮素供給的限制,而升溫能導致土壤氮素有效性的升高也可能間接地促進森林植被生產力的增加[52]。升溫對NPP促進作用的研究結果比較多見,例如:中國東北地區氣溫較往年偏高1—2 ℃時,落葉針葉林年均NPP大幅增加[27];溫度上升2 ℃時,興安落葉松林的生物量和生產力均增加[53]。
升溫對NPP增長的促進作用,存在升溫閾值。模擬結果表明,溫度升高1.5℃和2℃時,東北大部分綠色植被(常綠針葉林和雜木林除外)NPP增加,增幅為0.58%—10.34%,均以針闊混交林波動最大;但溫度升高超過3℃時,所有植被類型的NPP均降低,降幅最高達10.48%,以常綠針葉林降幅最大[49];江西省在氣溫低于17 ℃的區域,溫度越高 NPP 也較高,而在溫度高于17 ℃的區域,NPP則隨溫度增加而降低[54]。
溫度對NPP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時間差異性。例如,有研究[19]表明,1980—2013年長白落葉松林NPP與年均溫度無明顯相關關系,而與上年11月至當年4月份溫度呈顯著負相關關系。此外,秦嶺火地塘林區油松林喬木層NPP與上年及當年7月份溫度均正相關,其動態變化主要受1—7月份平均溫度影響,華山松林喬木層NPP只與上年7月溫度顯著正相關,其動態變化主要受 5—7月份平均溫度影響[55]。
4.1.2降水的影響
中國森林生產力的分布格局主要取決于氣候環境中的水熱條件,而其中的水分條件在決定中國大部分地區森林生產力水平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46]。水分需求、水分平衡影響著植物光合作用,從而對NPP產生影響。水分脅迫能導致氣孔導度降低甚至關閉,植物蒸騰和光合作用都顯著下降,植物在防止葉子失水的同時也減少了干物質的積累。
降水量對NPP的影響與植被所處的干濕環境息息相關,總體來說,降水量增加對NPP的增加具有促進作用,尤其在較干旱地區,降水量增加能夠緩解水分脅迫,增加土壤濕度,利于植被干物質的積累。然而,這種促進作用也存在一定的閾值,并不是降水量越高NPP就越大。例如,江西省在降水低于1900 mm的地區,隨降水量增加NPP略有增加,但幅度較小且波動較為劇烈;在降水量為1900—1950 mm的地區,降水越多NPP也越高,且增加顯著;但在降水量高于1950 mm的地區,NPP則隨著降水的增加而降低[54]。此外,不同植被類型對降水量變化的敏感程度也不同,且相比降水量增加和減少的情況,NPP對降水量減少更為敏感,尤其對降雨量減少5%反應最為敏感,以針闊混交林最甚[49]。
一般而言,任何兩個變量間的相互關系總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在現實情況下植被NPP變化通常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降水量的變化通常與溫度等因素息息相關,可能還存在相互作用,故單獨分析降水量單因子變化對森林NPP影響的意義并不大,因而相關研究也并不多見。
4.1.3CO2的影響
CO2作為原料參與光合作用,同時還通過對溫度、植物水分及營養物質需求等作用來影響NPP。一般而言,當CO2濃度升高時,植物能通過降低自身的氣孔導度來降低冠層蒸散,從而提高土壤水分的利用效率,同時還能夠提高土壤氮的利用率,進而提高森林植被的光合作用效率,促進干物質的累積[56]。然而,關于CO2濃度升高對森林NPP的影響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的分歧。
絕大部分研究認為,CO2濃度升高對森林NPP增加具有促進作用。例如,CO2濃度升高促進長白落葉松林NPP的積累,CO2濃度每升高1 mg/L, NPP增加2.6—3.5 gC m-2a-1,且CO2濃度越高,NPP增加的幅度越大[23],其他一些研究[19,57-59]也得出了相一致的結果。關于大氣CO2的施肥效應一直以來都受到了廣泛關注。多數研究認為,CO2濃度升高有利于促進植物個體生長發育,加速生物量積累,即CO2具有施肥效應。對熱帶地區150多個地塊的本底調查表明,近幾十年來一些原始熱帶森林的生物量和生長速度均有所增加[60],這在55個溫帶森林地區也得到了證實,CO2施肥效應被認為是最為可能的貢獻[61]。然而,由于生物群區、光合作用方式和生長形式的不同,不同植物對CO2濃度增加的反應差異很大。一般而言,生長速率快的物種比生長速率慢的物種(例如,落葉樹比常綠樹)對CO2濃度升高的響應更敏感[62]。對樹木進行高濃度CO2熏蒸,一般也具有施肥效應,其短期直接效應表現為光合速率增強、光呼吸和暗呼吸均有所減弱、氣孔導度降低、水分利用效率提高,生產力提高,從而促進樹木的生長。但長期處于高CO2濃度下,樹木對CO2濃度升高適應后,光合速率可能會逐漸恢復到原有水平,CO2的施肥效應會消失[63]。
然而,有部分研究[64]表明,即使在高水平營養供給下,也還有一些物種對CO2濃度的升高并沒有反應。例如,單獨增加溫度(2℃)或單獨增加降水(12%)都能促進闊葉紅松林NPP增加,而單獨CO2濃度倍增對闊葉紅松林的NPP沒有明顯的影響[22];單獨增加大氣CO2濃度對新疆雪嶺云杉NPP沒起明顯作用[45];單獨CO2濃度變化對栓皮櫟林NPP影響較小[24]。也有模擬研究[65]發現,CO2濃度增加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遠小于對小單木生長的影響,在競爭環境中生長的樹木常常表現出比單個生長的樹木的反應要小,在特定情況下對生態系統沒有任何影響或影響很小。例如,Melillo等[66]通過TEM模型模擬發現,僅大氣CO2濃度倍增并沒有改變北方森林的NPP。甚至有基于樹木年輪的研究[67]指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的樹木生長并沒有隨著氣候和CO2的變化而增加。
目前,只有極少數研究認為,在CO2濃度加倍、氣候不變的情況下,NPP降低,但降低幅度很小,例如,對北京山區栓皮櫟林的研究[24]。
據分析,研究結果的差異性可能與植物、環境條件以及CO2作用時間長短等均有很大的關系。例如,雖然很多FACE試驗表明在CO2濃度加倍的情況下植物NPP顯著增加[68],但野外森林生長觀測研究發現CO2的施肥效應很弱[68-69]。究其原因,一方面,目前多數FACE試驗研究是短期的,而且試驗中CO2濃度是突然增加的,然而在自然界中CO2濃度的增加是一種緩慢長期的過程。另一個方面,森林生產力對CO2的響應還受其他環境條件的限制,如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由于低溫及其導致的可利用氮的限制,樹木難以利用升高的CO2濃度提高生產力[66,69]。
4.2 多因子的協同作用
4.2.1降水與溫度的協同作用
一般而言,單獨降水增加有利于森林NPP積累,升溫對森林NPP的影響可正可負,升溫和降水的協同作用主要取決于這種正、負面影響的相互抵消或疊加結果。例如,單獨溫度升高2.6℃刺槐林NPP降低了14.58%,單獨降水增加10%刺槐林NPP增加8.82%,當溫度升高2.6℃同時降水增加10%時,NPP降低了7.48%[70]。相同升溫情況下,降水量的變化情況對于NPP的變化具有決定作用,如對浙江天童地區常綠闊葉林預估研究[37]表明,同在溫度升高2℃時,降水量增加20%時NPP將升高15.9%,降水量減少20%時NPP將降低4.9%。而且,溫度升高比溫度不變時,降水增減對NPP的影響更明顯,而溫度不變、降水增減對NPP影響均相對很小。例如,關于東北森林生態系統NPP的研究中,氣溫升高3℃、降雨量不變時NPP年總量增加0.032×1015gC/a,增加了9.37%;氣溫升高3℃同時降雨量增加20%時,年NPP增加0.037×1015gC/a,增加了10.99%;而當氣溫不變、降雨增加20%或減少20%時,年NPP總量也相應增加或降低,但幅度都很小,只有5.72%和3.14%[71]。
就全國范圍而言,溫度和降水變化對NPP影響的重要性因不同的環境條件,其結論不一。有研究[16]認為,中國大部分地區植被NPP的變化主要受氣溫變化的影響,而干旱半干旱區域植被NPP主要受到降水的影響。也有研究[64]認為,中國溫度變化對NPP的影響總體低于降水變化的影響,植被NPP的響應情況更接近于單獨降水變化時對植被NPP產生的影響。就區域分析發現,規律性也并不明顯。一種研究結果表明,有些區域溫度比降水對植被NPP的影響更顯著,如:東北森林NPP對溫度比對降雨變化的反應更為敏感,溫度升高和降雨增減的情況下NPP變化的幅度較大,而溫度不變、降水增減的情況下NPP變化均很小[71]。另一種研究結果表明,有些區域的森林NPP受降水比受溫度的影響更顯著,如:華北落葉松林(相關系數0.75)[72]、北京山區刺槐林(相關系數0.83)[73]、北京山區栓皮櫟林(相關系數0.89)[24],它們的NPP年際變化與年降水量均呈顯著正相關,而與溫度的相關性不顯著。還有一種研究結果則表明,溫度、降水均能對NPP產生極顯著的影響,如:長白山闊葉樹NPP與溫度、降水都呈顯著正相關關系[22]。
然而,自然界中氣溫與降水變化對森林NPP的影響非常復雜,可能具有交互性或消長性,例如,生長季前的升溫能導致紅松林NPP增加,但這種增加也可能被夏季降水減少所抵消[74]。這種影響也表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例如,在中國東南部的北部地區植被NPP與降水關系密切,而在南部地區由于氣溫較高而且降水充沛植被NPP隨溫度和降水的變化沒有北方明顯[34]。此外,不同森林類型對溫度和降水的響應也差異顯著,例如,即使同在三峽庫區,常綠闊葉林、落葉闊葉林及針闊混交林對溫度和降水變化表現出正響應:在溫度增加2℃、降水增加20%的情況下,其生產力均增加,增幅分別達到24.34%、22.50%和15.98%;而常綠針葉林卻相反,在相同的溫度與降水變化條件下,生產力降低,減幅達5.55%[75]。
4.2.2CO2濃度與溫度、降水的協同作用
CO2對森林生態系統NPP的影響與溫度和降水的協同作用息息相關,但其作用效果不盡相同,依不同森林類型而異,結論甚至相反。
一方面,CO2濃度升高與降水量增加,兩者協同作用對森林NPP具有正效應,但溫度升高卻表現出負效應。其中,有一類研究認為,CO2與降水量的協同正效應大于溫度的負效應,但單獨降水量的正效應不敵溫度的負效應,如對長白落葉松人工林及北京山區刺槐林的研究[23, 73]。然而,也有研究表明,CO2與降水量的協同正效應卻小于溫度升高的負效應,例如,對SRES A2和B2排放情景下長白落葉松林的研究[19]。此外,還有研究表明,CO2濃度加倍、降水增加和溫度增加協同作用降低了NPP,各因子之間表現出較強的交互作用,例如,對油松林的研究[76]。
另一方面,CO2濃度升高與降水、溫度增加均有利于NPP積累,且協同增加作用比單個因子對NPP的積累作用更明顯。例如,有研究認為,在未來CO2濃度加倍及溫度、降水同時增加時,長白山闊葉紅松林NPP將顯著增加[22];CO2濃度加倍,氣候不變或變化的情景下刺槐林NPP均增加,且氣候因子間均為正交互作用[70]。
4.3 氣候因子影響的區域差異性
氣候因子是植被NPP分布的重要控制因素,但不同環境下不同氣候因子的相對重要性明顯不同。
針對全球較濕潤的森林生態系統,年均溫(r2約為0.50)較年降水(r2約為0.40)與NPP具有更強的相關性[12]。但也有研究[13]表明,年降水較年均溫與NPP的相關性更強。對于干旱的陸地生態系統,在旱季,NPP對干旱強度尤其敏感,降水量及水資源利用率的變化對植被NPP影響顯著;而在雨季,降水量的變化則對NPP的影響較小[77]。
就中國而言,絕大部分研究認為,不同森林生態系統NPP不同程度地受到氣候因子的影響,總體而言,各氣候因子對NPP的影響程度由區域植被生長的首要限制因素決定,如在高寒地區,低溫是制約植物生長的主要因素,因此溫度與NPP表現為較高的正相關;而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區,降水是影響植物生長的首要因素,所以降水量與NPP的正相關表現的更為突出,相反,溫度升高可能會導致蒸發加劇,從而加重干旱的程度,因而有時與NPP呈現負相關[78]。例如:青藏高原西北部降水量小于400 mm的區域內植被 NPP 的主導因子是降水,東南部降水量大于 400 mm的區域內植被 NPP的主導因子是溫度。而且,對NPP的首要控制因素因局地環境差異性大而差別很大,例如:同樣在東北地區,大小興安嶺森林植被NPP整體呈現出了上升趨勢,據原因分析,植被生長所需水分(降水、積雪融水、凍土融水、蒸散等)和熱量條件均朝著更加適宜植被生長的方向發展,且該區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小[31]。同時,東北也有部分地區森林植被NPP主要與地表蒸散呈顯著負相關,部分地區主要與溫度和太陽輻射呈正相關[31,79]。在我國三北防護林項目區,降雨供應對NPP變率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干旱對NPP變化的貢獻約高達74%[80]。
然而,也有少數研究[81]認為,我國大部分森林生態系統NPP不易受氣候變化影響,其中常綠闊葉林和針葉林NPP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很低,特別是常綠闊葉林的高大喬木受降雨和溫度變化影響小,抗旱抗澇,自我修復能力強,但亞熱帶常綠闊葉林NPP的脆弱性在增加。然而,除了氣候因素,非氣候因素對NPP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非氣候因素中,植被類型、植被的環境條件包括地形、地貌等,以及人類活動均能對植被NPP產生一定的影響。其中,NPP時空格局與土地利用類型密切相關,土地利用變化導致了植被類型變化進而影響植被NPP[82-83]。一般而言,落葉闊葉林和常綠針葉林NPP最高,落葉針葉林和針闊混交林次之。森林物種組成的長期變化也能間接地影響森林生產力[84]。植被的環境條件,包括地形條件如海拔、坡度和坡向,以及石漠化等,均能影響自然植被NPP。已有研究[85]表明,NPP在我國喀斯特地區比在非喀斯特區域反應敏感度高,離散程度大;NPP隨石漠化等級的遞增而減小,重度石漠化地區NPP明顯小于其他地區,且石漠化等級越高NPP波動越劇烈。此外,其他一些自然因素包括自然災害事件(如颶風[86]、火災[79])、營養元素(如氮[87]、磷[88])也都會對NPP產生一定影響。而且,人類生產、生活或其他改造活動也能對森林NPP時空分布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如:城市化[89]、森林濫砍亂伐、退耕還林等[90]。總而言之,NPP的變化是氣候條件、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以及其中耦合的人類活動綜合作用的結果。
氣候變化對森林生產力的影響是生態學研究的熱點領域之一。綜上可見,目前的研究已充分展示了植被NPP對氣候因素及其變化的響應特征,其中尤其是定量響應研究能為植被監測、資源利用和生態保育工作提供理論依據。然而,這些研究中尚少涉及氣候因素所引起的NPP變化過程中一系列植被生理反應,而這對深入理解氣候變化與植被生產力的相互作用機制至關重要,這還有待于在日后研究中進一步考慮。
5 目前研究存在的問題
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對中國森林生態系統NPP的研究取得了頗豐的成果,然而所開展的相關研究工作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5.1 重復性工作及研究結果差異性大
從目前已發表的NPP相關文獻來看,我國對某些地區的研究重復性工作較多,特別是對重要林區如東北林區的研究尤其明顯,這與學者之間研究信息交流和數據共享缺乏無不相關。同時,相關評估結果相差甚遠,數據系統性差,導致即使是對相同區域的NPP估算值之間有的都無法進行比較。
無論是通過站點實測還是模型模擬,NPP估算值差異性來源都非常廣泛。對于實測結果而言,即使同樣都來自于野外站點調查,但結果仍然可能差異較大,可能的原因有:NPP包括地上、地下部分,有的研究只測定了地上部分,而有的研究則包括地上、地下兩部分,即使均測定了地上、地下部分,對地下部分NPP的測定誤差較大;野外調查經常面臨很多困難,空間分布不均,樣方選取的主觀性強使得測定結果差異大;當將野外調查得的點尺度的NPP推算到更大空間尺度時,很可能會帶來誤差。對于模型模擬而言,由于不同模型的機理、運算方法和數據源等存在差異,導致對同一區域的NPP模擬值也很可能存在很大差異。即使使用同一個模型,參數設置、數據源不同也可能造成模擬結果的差異性。其中,所使用的氣象數據一般都是用氣候學方法計算并插值得到的,在這個由點到面以及不同分辨率之間轉換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引起誤差,從而影響NPP估算結果。
5.2 現有結論的不確定性
模型為NPP估算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模型模擬能力、對相關參數獲取限制以及參數化方法的誤差等諸多方面,均會給研究結果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NPP的估算精度上。對于生態系統模型而言,模型模擬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假設基礎上,對生態系統復雜機理進行一些簡化處理,忽略掉一些非決定性或者無法進行評估的細節過程,這必將增加預估結果的不確定性。例如,極端氣候事件會對森林的分布、結構產生極大影響(如颶風和熱帶風暴對于熱帶雨林的破壞力巨大,對生態系統結構的改變往往起著重要作用),然而,在對氣候變化背景下NPP的變化模擬過程中卻很難對這些極端事件作出評估,從而未加以考慮,這也會對NPP模擬結果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此外,以Biome-BGC模型模擬為例,由于試驗條件限制,一些研究只能針對部分敏感參數進行實地測量,其他很多參數都是參照相關文獻以及模型本身自帶的參數,也忽略了一些系數(如水分脅迫系數),這對模擬結果均能產生一定的影響。
5.3 研究的局限性
目前對NPP的估算存在諸多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基礎數據不足、建模過程中存在不確定性和模型驗證困難3個方面:對于模型估算,由于受一些基礎數據及模型參數獲取限制,建模工作往往受限。而且,由于受試驗條件、野外工作環境所限,觀測數據相對較少且較難獲得,故而影響模擬結果與實測數據的全面擬合與校驗,使得模型準確性驗證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研究區范圍較小,地形(海拔、坡向、坡度)、土壤等的微小變化都可能對NPP有較大的影響[91],而模型模擬時輸入的參數無法細致地反映出這些細微變化,使得模擬值與實測值之間存在偏差。
6 未來重點研究方向
(1)模型精度和適用性提高仍是重點。模型是NPP估算不可或缺的手段。模型參數和數據來源是決定模型精度最重要的因素。國內對NPP 的模擬多是對國外有關模型的改進。模型運行所需的很多參數在國內尚未研究,因而參考前人的成果。因此,以后的研究中應考慮根據中國實際特別是根據區域及研究數據的特點將參數更合理和實踐化,以確定適用性更強的參數。此外,由于國內還存在觀測不太完善的問題,如測定標準不統一、觀測指標連續性不夠等,造成很多數據的可用性較差,因而建立長期定位觀測網絡體系、強調觀測資料的標準化和可比性,也將有助于模型參數的校正和改進,從而提高模型精度。
(2)建立精度高綜合性強的耦合模型是重點也是難點。雖然已有模型都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但它們也均有各自的優點,應該發揮各自優勢。基于多種算法的集合模擬通常產生顯著優于單個算法的模擬結果[92]。各模型的相互結合、相互滲透將是準確預測研究的發展趨勢[93]。因而揚長避短、融合各模型的優點,建立精度高、綜合性強的耦合模型將是今后研究的重點和難點,也是今后NPP評估的一個必然發展方向。
(3)發展綜合評估指標體系研究。目前植被NPP的影響研究中,所采用的氣候指標基本上是年平均的變化,很少或沒有考慮其季節變化和極端氣候事件。而在氣候變暖大背景下極端氣候事件趨多趨強,氣候的季節波動將更為明顯,這對很多物種來說可能是致命的,因而在未來的研究中不容忽視。此外,如前文所述,林地生長環境(如海拔、地形、地貌等)、自然災害(如風害、病蟲害、火災等)、營養元素(如氮、磷等)限制、人類活動等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著NPP,但由于數據收集困難、人為因素難以定量化等各種原因,NPP的評估過程中很少對這些因素進行全面考慮。故此,今后的研究中,應更加注重各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發展更加完善的綜合評估指標體系。
(4)進一步加強機理性研究。目前陸地生態系統與關鍵氣候因子之間的關系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其耦合關系仍缺乏機理性分析,以后的研究中應予以加強。一般認為,溫室效應和氣候因子通過影響植物生長發育過程和水分循環過程,對植被生產力的形成產生影響[4,71]。然而,各因子隨植物生長的變化情況以及各因子間的交互作用往往并沒有太多考慮。此外,陸地生態系統與氣候變化之間相互作用機理有待進一步清晰化,可能尚需從植物生理學角度去加以解釋[15]。
(5)針對性選擇合適的研究尺度。NPP評估的不確定性很大,且在不同地域尺度上差異明顯,因而針對性選擇合適的研究尺度非常重要。全球變化加劇了氣候在地域間的不平衡性,使得NPP在區域尺度上的響應更加明顯。就模型模擬而言,大尺度模型無法考慮地面柵格單元內植被、地形以及氣候條件等的異質性,而區域尺度上的主導控制因素比較明確,空間異質性相對較低,因此也更能引起研究者的興趣[94],因而目前以及未來的研究更多地還是集中在區域尺度上。對于我國而言,模擬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的北部生產力比南部具有較大的變化和不確定范圍,因此,從最大程度減少和降低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響應的不確定程度出發,我國未來NPP研究的重點區域很可能在北方[42]。
(6)加強研究信息交流和建設網絡化數據共享平臺。由于研究信息交流仍較缺乏,不同學者采集的樣地不同,利用不同的估算方法、不同的參數得到不同的估算結果,從而使得數據系統性較差、評估結果相差甚遠,也容易出現重復性工作的情況。因而,在加強研究信息交流的基礎上,采用先進的研究技術手段,圍繞森林資源和環境保護等熱點問題研究森林生產力,同時實現數據共享和網絡化是生產力研究發展的必然趨勢[95]。
綜上,在選定合適的研究區域基礎上,建立精度高、綜合性強的耦合模型,發展綜合評估指標體系,同時進一步加強氣候變化與生產力的相互作用機理研究,同時在加強研究信息交流的基礎上,建設網絡化數據共享平臺,有效減少重復性工作以及降低評估結果的差異性,這些都是未來NPP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