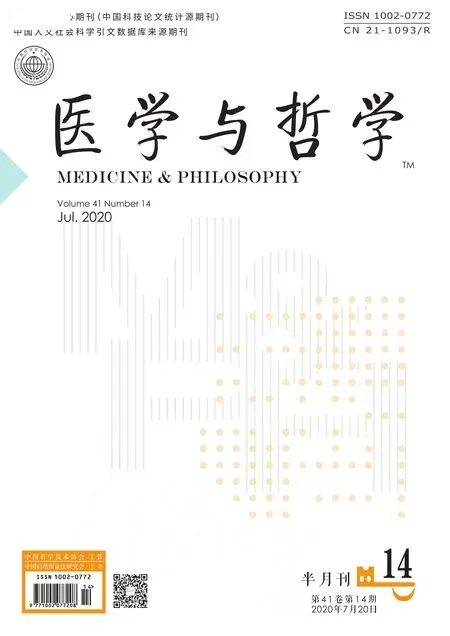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事件可供性管理模式研究*
魏東力 劉子琦 陳麗霖 朱啟卓 王新妍 徐 前 伍思涵 趙 群
1 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事件的基本概念
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事件(events of global public heath systematization,EGPHS),是一個前瞻性統合創新性的學術概念。其核心與人類以往的歷史理解和現實的社會認知十分不同,且具有科學技術哲學價值和醫學經濟倫理學的操作性意義,更加具有可以輻射和覆蓋自然、生物、人類、經濟、社會的,歷史、現代、未來的哲學統合性和社會科學前瞻性。同時,也可以明確克服20世紀前后人類慣性思維的地緣化倫理、城市化道德的公共安全支撐性漏洞和醫學預防實現性差距。
首先,EGPHS區別于以往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定性的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PHEIC是指通過疾病的國際傳播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風險,并有可能需要采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的不同尋常的事件[1]。因此,EGPHS與全球公共衛生地區化事件互補,第一次在概念上全面構成一組可供性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理論模式的人類認知基礎。
其次,EGPHS的基本概念可以將21世紀后WHO宣布的PHEIC統一定義為EGPHS的前置性階段表現(以下簡稱“前事件”)。以不斷研究和解釋前事件與EGPHS之間已知的和未知的可供性社會預測和政策科學的人類待知基礎。
最后,EGPHS的基本概念也可以將21世紀前至今依然存在的所有病毒所致的疫疾病和亞健康事件一律定義為EGPHS的歷史性階段表現(以下簡稱“歷事件”)。以全面回顧和追溯歷事件與EGPHS之間歷史的和現實的可供性社會預測和政策科學的人類可知基礎。
依此分類,人類可以在均衡地共享太陽系的地月運動關系的同時,深刻地探索全球看不見的存在,即透明化的客觀所賦予自然、生物、人類、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可供性健康和疾病的關系譜。假設人類已經發現EGPHS確實具有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在、無往而不在的客觀公共性,即人物共享性,那么可供性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理論的自然—生物價值、生物—人類價值、人類—經濟價值、經濟—社會價值,以及涉及人性健康與疾病關系的微生物學和零生物學價值就已經開始浮現或屏蔽在環境共同體遺傳和變異的生態趨勢之中。
2 EGPHS的可供性反思
2.1 可供性存在的基本反思
可供性(affordance)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首創的一個生態心理學的核心概念,吉布森將可供性概念定義為意味著動物和環境之間的協調性(complementarity)[2]。
由此可見,動物和環境之間至少存在有無限可能的或有限不可能的可協調性與不可協調性的生物可供性變化和自由性轉化。其中,在全球、公共、衛生等系統層次上的動物和環境之間可以協調均衡的可供性變化可能就是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常態值的本體論基礎;與此同時,在全球、公共、衛生等系統層次內的動物和環境之間可以不協調均衡的或不可以協調均衡的可供性變化可能就意味著EGPHS的潛在性傾向,以及不同部分與不同程度的生物之間發生密集性或規律性的大規模變化值的本體論基礎。就像是一場可以持續百年的戰爭、可以隨時爆發的火山、可以燒毀半壁的林火、可以毀滅家園的地震、可以淹沒一切的洪水、可以吞噬萬畝的蝗蟲、可以肥胖全民的生活方式均能導致無數生物、無數人物面臨其不同時間、不同世間和不同實踐所涉及到的系統化公共衛生災難事件的可供性存在。
但是,可供性的原始概念在認知上是將動物和環境進行了類似于對立統一法的學術性處理,并且主張可供性主要就是動態系統行為運動的物理環境內在傾向屬性的本體論解釋;以及可供性雖然獨立于知覺存在,但也是可被信息知覺便利的生物行為技術能力屬性的功效論互補,即可供性的動力系統概念[2]。很明顯,這是動物和環境之間關系的一種20世紀發展心理學傳統所需要的理論范式。實際上,動物和動物之間、植物和植物之間、環境和環境之間、動態和動態之間、靜態和靜態之間,以及它們歷史性的相互復合與復現之間均是處于一個一元化的全球物理化系統和全球生理化系統復雜一體化的雙圈體系之中,即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概念的物化和生化自由以及自律的生態化互動之中。因此明確地說,EGPHS至少存在一個非常的(物化和生化之間互為系統化過程和互為部分化格局的協調沖突性的)可供性存在的驅動機制。
概括地解釋,動物包括人類顯然都是具有各種不同物化和生化協調一致性基準的生物存在形式。同樣,環境是具有各種不同物化和生化一致性協調基準的生物存在形式以及生物能否存在的相關本體論基礎。因此,反思生物和環境之間的可供性存在實質可以進一步理解為是一個多元化互為系統和互為部分的協調性本體論、功效性認識論和系統性方法論的科學技術哲學共同體。現在,人類面臨的可供性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尚不能知道這一客觀系統的基本規律和變化真相。為此,可以假設這就是可供性存在研究的基本反思起點。
2.2 可供性社會的預測反思
有關可供性的預測反思的文獻案例可以回顧到天花病毒、流感病毒、乙肝病毒、艾滋病病毒等一系列歷事件發生至今的人類公共衛生過程變化的見識和實踐。公元前1046年~771年在《周易·乾象》中就出現了最早的“健”概念,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3]3。超前奠定了人類公共衛生系統“天行健”的可供性和可共享的認知高度起點和君子自強不息的思維密碼。由此拉開了數千年來人類自力更生意識和全球公共衛生環境可協調性和不可協調性共同演繹的醫學精神序幕。
例如,史學界推論的人類歷史上已經找到的第一個天花病例。其中,聚焦的天花病毒主要也是經過呼吸道黏膜侵入人體,通過飛沫吸入或直接接觸而傳染,即具有可供性和可共享的系統化協調性基礎。直到現在,天花病毒依然是無法有效預測和無法有效治療的歷史病種之一,只能采取《史記·趙世家》所述的公元前655年大疫中的設坊隔范式[3]1,即最早的公共衛生預防政策,以及源自歷史上最早的人痘接種思想和最有效的牛痘接種范式,即全球化最早的公共衛生免疫政策。
其中,人類從中國古代人痘接種知行模式的歷史傳播到英國近代牛痘接種經典范式的現代歷程都比較客觀地突出了不同文化背景中可供性社會的差異化預測邏輯。例如,人痘接種法即最早的免疫預防的疫苗化模式,依然是既可降低天花危害,又可引發天花傳染的風險免疫范式。
1780年,愛德華·琴納(Edward Jenner,1749年~1823年)首次將可引起牛皰疹的物質稱為病毒,其在近20年的鄉村醫生實踐中進行源自于農牧業經驗可供性機遇的牛痘接種法人體試驗,并發表了論文《一次天花牛痘的因果調查》,但他卻被當地醫學會一直定性為“醫學騙子”并呼吁取消其會員資格,因此是在非議中預測和解決了天花的可視性病毒防治基本范式。在動物和人類生活環境之間的病毒可供性系統中奠定了人畜公共衛生理論、技術和工程可持續發展的光輝起點。并在19世紀至今不斷獲得全球化公認。1853年,即琴納逝去30年之后,英國國會通過《疫苗接種法》,標志著英國和全球歷史上第一次以公共衛生的名義強制全民接種疫苗的社會預防和政策科學的可供性文明起點[3]32。其中的關鍵機制可以概括為琴納發現了病毒感染者和病毒免疫者之間存在可供性社會的可預測差異的可驅動邏輯。
就在琴納首次使用病毒術語100年之后,1898年前后人類才通過細菌過濾器發現比細菌更小的能夠通過細菌過濾器的煙草花葉病的致病因子現象,而且即使將其稀釋100萬倍依然具有致病能力,但是在人類進入原子時代標志的顯微鏡下卻沒有發現任何非細菌的存在。為此,沒有研究過人類疾病的貝杰林克將這種煙草花葉病的超顯微鏡濾過性致病因子也命名為病毒(virus)術語,奠定其病毒學開創者的發展起點。其中,同樣也比較客觀地突出了可供性社會的可預測差異和可驅動邏輯的科學進步機制。
1931年,電子顯微鏡技術的出現開啟了生物學革命的現代化進步,人類第一次能夠直接觀察到微小至百萬分之一毫米的物質存在。其中也包括人類直視病毒個體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可供性社會的預測本體論路徑和認知論方法蜿蜒曲折、峰回路轉,并具有明確時代的不確定性概念、差異性判斷和假設性推理之間的相互錯位。
1980年,WHO宣布全球已經消滅天花[3]7。至此,病毒界以天花為文化標志,與人畜共同演繹了一場萬年青史留名的EGPHS的歷史性階段表現的第一場閉幕式。為之后一系列不同年代所發現的病毒,諸如流感病毒、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以及其他病毒合并性疾病引發的國際公共衛生束手無策事件奠定了可供性社會研究的預測反思基準。
2.3 可供性政策的科學反思
可供性政策的科學反思,不僅可以進一步反思可供性社會的歷事件預測歷史之中存在的各種有效的醫學基礎,也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思21世紀以來人類的可供性政策面臨的自然、生物、人類、經濟、社會的系統化安全和危機的思維性挑戰,以及驅動性機遇。
2000年~2020年,WHO依據其全球疫情預警和反應網絡統計了世界各地每年不斷發生疫情危害的可供性生物環境信息和數據,并依據《國際衛生條例》發布了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包括2009年H1N1流感病毒蔓延,2014年野生型脊髓灰質炎病毒蔓延,2014年埃博拉病毒蔓延西非,2016年寨卡病毒蔓延巴西,2018年~2020年埃博拉病毒蔓延剛果(金)等。
其中,首當其沖的依然是人類千百萬年呼吸性環境中始終難以回避和免疫的流感病毒疫情。1920年前后首發于美國的流感病毒,導致全球蔓延,感染數億人,致死5 000萬人,2010年前后的流感病毒僅美國就感染2 200萬人。WHO曾指出,目前流感大流行在發生疫情國家內進一步傳播以及蔓延到更多的國家是不可避免的,這一假設已得到了過去經驗的全面驗證。2009年流感大流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國際上傳播。過去發生流感大流行時,病毒的廣泛傳播需要6個多月,而新型H1N1病毒卻在不到6周的時間內就能廣泛傳播。
2014年,WHO發布兩次PHEIC。分別涉及病原體為野生型脊髓灰質炎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疫情。2014年~2020年,WHO呈現出每隔一年就宣布一次PHEIC的頻發性范式,包括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2020年埃博拉病毒的再度蔓延等。
由此可見,人類在一系列病毒可供性存在的世界環境之中,不僅面臨其可供性社會的預測盲點,同時也面臨其可供性政策的科學空白。迄今為止,人類一切的科學技術共同體在EGPHS不斷臨近之時,依然是存在檢驗政策、診斷政策、預防政策和治療政策上的普遍危機和全面無助。特別突出的是,這種現象竟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政策都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和地區更為明顯。除此之外,具備人類科學基準的全球政策載體——理論、人力、財力、試劑、疫苗、藥物、裝備等一系列衛生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防疫利用——均是處于一種將來進行時的不可預期狀態。綜上所述,這就是可供性政策研究中的科學反思焦點。
3 EGPHS的可供性管理
在EGPHS的可供性反思中,人類可以發現其只是原生態環境之中可以進入衛生態的生物物種之一。其公共性源于生物環境性變化,這些變化都是不以任何人和社會的意志為轉移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環境,即真實世界不變的基準。與此同時,其公共性和衛生性法則在人類生物的社會發展中在所有人與每個人的歸屬上始終都存在野生態和自生態、生物態和生化態、生存態和生長態、生活態和生產態的經濟學差異,這些差異性均是不以任何人和社會的意志為轉移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基礎,即自由世界不變的基準。
因此,EGPHS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始終具有不以任何人和社會的意志為轉移的變化性和差異性的共同本質。這里的公共衛生并不是某一個地緣化倫理和城市化道德規范的所屬品,也不是某一個國家化貨幣和國際化貨物價值的交易品,而是地球上所有可持續慣性規律的共存化和共生化循環,對于人類來說是一個客觀的公共衛生系統,而不是一個主觀的公共衛生系統。所以,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是一個不同于和相對于人類公共衛生歷史化的可供性環境認知的創新性學術概念。
由此可見,在涉及到EGPHS的可供性管理上,人類思維和行為在計劃(plan)-執行(do)-檢查(check)-改進措施(action)的PDCA理論和實踐中,首先應該明確的是人類只能看到的真實地球不足百分之一、只能知道的地球生物不足千分之一、只有不到萬分之一的人類可能在顯微鏡下見過不足十萬分之一種細菌、只有不到百萬分之一的人類可能會在電子顯微鏡下見過不足千萬分之一種病毒的社會預測局限性和政策科學片面性的真相。何況就是在看到者與知道者之間、在知道者與做到者之間的人類學習過程和社會賦能結構之間依然可能存在巨大的時空差距和質量漏洞。因此,在計劃和執行上均可能會存在一定的科學者思維難以自由和自信的現實。
為此,EGPHS的基本概念假設全球是一個無機化衍生有機化的自然相互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自由依次出現了微生物和生物化的生態相互變化的循環,這種自然和自由雙重的過程循環時空均遵循物理科學上的基本定律,因此,質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電荷守恒定律、信息守恒定律,特別是太陽與地球之間自發的能量與熵的轉換關系和動態平衡即地球維持一個相對與所有生態域共同穩定的可供性環境溫度變化,可能就是人類可以從不知走向可知,可以從無解走向破解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免疫的密碼所在。2020年4月15日,WHO緊急項目負責人也曾表示,目前不清楚溫濕度等氣候因素對病毒的影響,也許不得不學習如何與之共存,以及如何在高密度城市環境中控制病毒。
當然,物理學系統中的一切規律都是不以任何人和社會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但是,物理學確實是一切生態學和生理學現象的可供性基礎,可以為人類和社會理解生態學和生理學的信息化系統變化提供諸如正熵與負熵的不同參照系的不同概念基準。當年正是埃爾文·薛定諤所著《生命是什么》促進了眾多物理學人士轉向了生物學時代方向的啟動思潮。
現代科學認為,太陽之光是賦予地球所有生命負熵存在的本源,即所有生命均是以各自不同或共同的方式從外部獲得物質、能量和信息以維系其生命的負熵及其有序的價值存在,同時,也是在自組織的耗散結構中不斷地消除熵及其無序的影響增加。目前,可以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間普遍聯系最早的細胞寄生物就是病毒,其潛伏的語言哲學可能就是隱含“并其他為獨、并天下為獨”的自然生物規律。第一,這是全球范圍內數量最大層次最高的前微生物類,主要是以噬菌的方式寄生于細菌細胞實現其負熵并以溶菌、溶原、溶器、溶體等未知的多種形式擴增簡稱噬類、巫類或電鏡微生物類。第二,是傳統認知中全球范圍內數量最多的微生物細菌,幾乎是作為噬類首選的細胞載體存在于所有的生物之中,發揮難以計數的生化和生理正反兩個方面的生命價值影響,簡稱菌類或顯微鏡微生物類。第三,是水、土、氣等多相之中的所有動植物及其微生物統稱生物類。第四,是人類以及與其生活生產密切相關的人畜類和與其生成生理密切相關的線粒體類。
其中,EGPHS的可供性管理焦點主要是聚焦于噬類,其不僅提供了地球上半數以上空氣環境中的氧氣,為天下生物的生存創造了僅次于太陽負熵之源的天然價值,同時,作為壟斷全球生命存在的頂級微生物系統通過噬菌等多樣化多層次不同的寄生細胞化擴增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可以引發一系列包括不同規模疫情在內的各種生物進化或退化的細胞因子風暴。
其次,EGPHS的可供性管理路徑主要是聚焦于菌類,因為其不僅是噬類獵殺的主要微生物,同時也是百倍于所有生物體自身內在基因組之外最主要的內部基因組所在,特別是細菌磁性特征可能就是破解菌類上下游微生物與生物相互鏈接與傳感物理的密碼所在。
最后,EGPHS的可供性管理范式主要是聚焦于生物類特別是人畜類源于知覺的和知道的經驗差異性,而不是迷信于圖像化和統計化的所謂科學抽象和專家依據。只有琴納式的醫生才可能奠定人類需要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基層創新的社會基礎。
綜上所述,以上關于EGPHS的可供性模式研究的三大假說性分析和各種假設性諸多推論可能會存在很多需要討論的問題和爭議。尚有待于學術界進一步研究的補充和完善。以利于人類能在EGPHS的前置性階段表現和知覺基礎上不斷地取得可供性管理創新。
4 EGPHS防御的科學倫理建議
醫學是一元化多層次系統的道德理論和實踐服務。EGPHS的出現第一次全面地鏡化了人類醫學逾萬年曲折的社會依賴性服務能力,前所未有地檢驗了全球公共衛生系統普遍存在的社會倫理空白和科學道德漏洞。與此同時,也暴露了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研究實驗室化和無數科學技術進步的理性在生態預測環境和健康政策環境中依然缺乏工具性終極價值和有效方法的現實無奈。
為此,本文建議全社會均應以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科學理論為醫學教育的核心基礎、為醫學管理的核心職能、為醫學研究的核心方向、為醫學服務的核心能力、為醫學合作的核心領域,在此基礎上積極拓展醫學系、護理系、技術系、藥學系和專科系均衡服務配置的醫學基準化教育和醫學服務基層化職業。有效地克服全社會和醫學系統日益缺乏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防御的科學基礎和服務能力的熵化局面和各種退化趨勢。在21世紀可供性存在[4-5]、可供性社會和可供性政策的三大客觀世界的真實生活中發現差異化的預測邏輯和前瞻性的科學基準,繼承和推進源于醫生化和基層化相結合的實踐,創新實現人類可以知道和護理可以做到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防御戰略的全民健康服務的范圍、規范和目標。在醫學政策和醫患關系上科學地自律生態關系、生物關系、生死關系的自然決定因素和社會決定因素的可供性管理模式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化界限。為延遲至今一直未能實現的《阿拉木圖宣言》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全球醫學基準補齊人性和經濟的歷史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