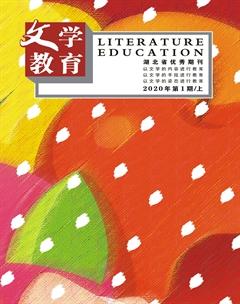后現代的游戲人生和反諷藝術:評方方《花滿月》
陸璐 李奇志
內容摘要:方方的小說雖常書寫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卻能用“刀鋒”般的筆力探索和挖掘筆下人性的隱秘、幽暗和欲望,花滿月正是這類人物的典型。《花滿月》通過“花滿月”式后現代游戲人生的敘事,以及“岳滿花”迥乎常人的人生故事,給讀者呈現了生命的另一種存在,表明了方方對某種普世人生態度的反思和人性種種可能性的全力探索。
關鍵詞:花滿月 游戲人生 反諷
在當代女作家中,方方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她的內心一直保留著文學創作的本真沖動,她的小說雖常常書寫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卻能用“刀鋒”般的筆力探索和挖掘筆下人物所隱藏著的人性的隱秘、幽暗和欲望。而這些隱秘、幽暗和欲望的人性,與現實人生的安穩價值追求相去甚遠,因此這些人物的人生在旁觀者看來,是叛經離道的,甚至是毫無意義的,花滿月正是這類人物的典型。但正是對這些人物的塑造表明了方方對某種普世人生態度的反思和人性種種可能性的全力探索。
小說《花滿月》發表在《北京文學》2017年第1期上。主人公花滿月原是地主富豪家的千金,家境優渥,養尊處優,卻因為沉溺于打麻將,錯過了花家在戰亂中的逃難機會;于是在時代的沉浮下,成為了下人王四的妻子,在工廠做一名腌菜工以維持生計。到了晚年,親生兒子還想跟她爭奪房子的賠償金,命運對她從來不懷好意,但當她的生活出現了轉機,正當一切都在向一個圓滿的結局發展的時候,作者卻筆鋒一轉,將結局往完全相反的方向驟然推進——花滿月意料之外地暴斃在了麻將桌上。花滿月跌宕起伏的一生,似乎充滿了戲劇性和悲劇性。迥乎常規的結尾從客觀上來看,似乎是偶然的,然而這卻又是必然的——沒有再能比完成“打滿一百圈麻將”這個愿望后死去更適合花滿月的結局了。常人所對幸福定義中的家庭圓滿、社會安定、生活富足,花滿月全都沒有,她有的只是揣在懷里的一副麻將,在昏暗的小閣樓里,創造了屬于自己的一番天地,那是花滿月的生命之光。
花滿月從來不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悲戚,麻將就是她全部的精神世界,打夠一百圈麻將,這是她人生的終極夢想;哪怕是屈身在小閣樓上,由麻將構成的自足精神世界,也足以溫暖她的一生。花滿月的牌癮與生俱來:自從睜眼能看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牌桌,小小年紀就能將母親老練的牌友打得落花流水;淪落為工廠的腌菜工時,她用撿來的麻將在幽深的閣樓給自己造了一個牌館,假想著與另外的三個牌友一起打牌,打得天翻地覆,風生水起;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中她也不諳世事,任牌樓外的世界更迭變換,牌桌上的她只覺得烈火灼心,終日沉溺在打麻將的快感中;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也是在麻將桌上含笑而去,她也覺得“相比起她在花家華麗噴香的閨房,這個逼仄的閣樓,更讓她覺得人生活成這樣,才叫值得。”①這個世上的任何人任何事不過都是花滿月人生中的過眼云煙,真正能夠讓花滿月夢牽魂繞的只有麻將而已。
從幼兒時就能在牌桌上打麻將打得風生水起到臨終前打滿一百圈麻將后闔然與世長辭,花滿月的人生都帶著一種怪異荒誕的感覺。然而這卻與后現代游戲說相契合,后現代游戲說揭示了人自由的本質,人可以拋開利害的考慮,擺脫倫理的羈絆,以游戲的態度對待人生。花滿月的人生也就是游戲人生,她跳脫出了普世價值觀的約束,我們難以看到生活對這個女子的摧殘,同樣的,她對于生活也從不報以溫情。甚至在進行“打麻將”這個讓她如癡如醉游戲的時候,她也不按常理出牌,這個游戲的規則制定者是她,滿足了自我的快感就足夠了,于是在小閣樓獨屬于她的小天地,她一人充當四人角色,她嚴格要求自己公正,不對自己偏心,努力把想象中對手的賭資贏過來。后現代游戲說中的“關懷你自己”,強調個體的差異,重視個體的日常體驗,在花滿月這里都不經意間充分呈現了:花滿月關心的從來不是世事的變遷、人生的無常,而是現實生活中具體的、實踐中的、不可替代的、活生生的“自我”。道德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約定,而不是真理,人生最重要的是確立個體的生存風格。后現代的自由感強調人們對于游戲的愉悅感受,花滿月沉浸在打麻將的快樂中時,她也感受到了無比的自由和快感,因此她寧愿在幽暗的閣樓上守著殘破的麻將度過一生,也不愿意在閨房里忍受不能打麻將的高貴、富足和寂寥。
維特跟斯坦提出:“不要想而要看。”②認為游戲歸根結底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人類生活現象,因而游戲具有實踐性的特征。由此,他強調進入游戲,參與游戲,回歸生活的世界。花滿月的游戲人生亦是如此,麻將對于花滿月來說不僅僅只是一種單純的精神追求,它更是自我生命體的當下參與,如此,花滿月便擺脫了精神與物質,心靈與身體,本質與現象的等依存關系的束縛,在麻將的世界中發揮自我的想象、創造性以及個性。方方運用反諷的藝術手法,通過花滿月的游戲人生將客觀存在的“外在的束縛”與花滿月“本我的欲望”構成一對激烈的沖突,解構了普世人生價值定義的框架,于是,花滿月自認為自己“足夠耀眼”的一生浮現在讀者面前。
《花滿月》敘事的時代背景,是現代史上最具變構性和沖突性的歷史時期,然而花滿月的靈魂卻是一個游離于時代之外的存在,命運的沖刷在她的精神世界沒有留下一絲痕跡。富貴人家的花滿月日日瘋魔般沉溺在麻將桌上,不知時變,看不到牌館外金戈鐵馬的現狀,花家人為了躲避戰亂倉皇逃走,花滿月卻因為舍不得離開牌桌而錯失逃走的機會。巨大的社會變革轉換了舊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一夜之間,花滿月變成了岳滿花,淪為了下人王四的妻子。新時代的到來必然伴隨著新的變革,一系列政策的實施給花滿月帶來了不同的身份,然而無論是成為套著肥大破舊衣服里的家庭主婦,還是工廠里的技術嫻熟腌菜工,外在的風云變幻絲毫影響不到她的內心世界,她像與生俱來帶著中國傳統式的“隨圓就方,無處不自在”的氣質,歷史的更迭變換對她來說只不過是一場場戲碼。于是在社會洪流的改造與沖擊之下,看到的不是一個被改造了“本心”的花滿月,她更像是一個旁觀者,世事的沉浮與人生的無常對她來說不過是細水流長人生中的一件件外在于“她自身”的瑣事,她的內心世界超脫于社會環境、道德規范、生存狀況等的羈絆,沉溺于麻將游戲人生。
花滿月帶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樂觀對待生活,她從來沒有試著和命運作對,并且接受了生活對她的種種刁難;在她的身上,我們能感受到一種超脫常理之外的淡漠。在花滿月的生命中,世人普遍的情感對她來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在小說構建的人際關系網中,丈夫王四、兒子王富華、廚子阿貴等等都不過是她人生中的配角,花滿月與這些人物從來沒有過刻骨銘心的愛恨糾葛。即使成為一名母親,花滿月也沒有因為孩子的存在而成為普遍意義上的賢妻良母,對于兒子的親熱,花滿月從來都置之不理。在小說中出現的眾多人物關系之中,無論是花滿月式富貴麻將游戲的“叛經離道”,還是岳滿花式貧窮麻將游戲的“躲進小樓”,兩種生活方式都與當下傳統世俗規范的準則,構成了巨大的反差,通讀全篇,這對矛盾貫穿了全文,使得故事曲徑通幽又柳暗花明。花滿月的人生與名利無關、與愛情、親情、友情關系淡漠,她一生的羈絆跟一個看似荒誕的意象緊緊相連——麻將。若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來關照花滿月的人生,我們最直接的感受是“怒其不爭,哀其不幸”,時代更迭變換讓花滿月淪落至此,然而她對命運的捉弄坦然受之,不知反抗。哪怕她的生活歷經歷史的轉換,歲月的洗禮,生活的磨難,至親的離去,她內心深處的“本我”未曾一日消失,只要實現“打滿一百圈麻將”這個愿望,她愿意傾其所有。
花滿月死了,她的一生無人提及也無人記起,而作者卻總結道:“她覺得自己的一生很輝煌,而實際上,這輝煌只要她自己覺得照耀了,就已足夠。”花滿月為麻將生,為麻將活,為麻將死;她的人生也因麻將而“輝煌照耀”。方方的反諷帶給我們深刻的思考:普世人生價值是每個人都認同的嗎?如果不認同,個體價值該如何實現?個體欲望該如何表達?個體生命該如何為自己而活?……方方摒棄了以往創作中女性形象大都以是以悲劇來結尾的設定,而讓花滿月“圓滿”了她的這一人生。方方的反諷將不和諧、矛盾的事物組合在一起,把故事的結局推向一種看似荒謬滑稽的境地之中,也使得小說更具有張力。人生價值的怪異追求與游戲命運劇本的疊加,使得花滿月這一形象更加鮮活。在《花滿月》中,我們看到方方對于命運的偶然與人生抉擇必然的哲學思考,花滿月這一形象的塑造,跳脫出了世俗人生價值觀念的框架,為我們提供了人生定義的另一種可能性并警醒著我們對自我、對人生價值的思考。
注 釋
①方方:《花滿月》,《北京文學》2017年第1期。本文后面所引的原文全出自本作品。
②[奧地利]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李步樓譯,商務印書館2000版,第47頁。
(作者介紹:陸璐,武漢輕工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漢語言文學16級學生;李奇志,本文通訊作者,武漢輕工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