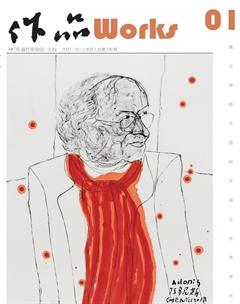虛構之美
塞 壬
2004年我開始寫作。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成為一個作家,寫,只是表達或者傾訴,誠然,這樣的寫作跟自己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很少有虛構的成分。我把文章貼到網絡論壇上,人家說,我寫的文章叫作散文。
于是,我成了一個寫散文的人,一寫就是十幾年。
實際上,在我的意識里,我沒有文本的概念。我并沒有事先預定要去寫一篇散文,或者去寫一篇小說。我不知道這兩者的區別,也不想知道。但是,有那么兩三次,我像往常那樣把所謂的“散文”投給雜志,編輯說,我把它當成小說發,你有意見嗎?
這能有什么意見?又不是說我寫得不好。
之所以屢屢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我的散文有相對完整的敘事結構。所以,讀的人覺得這是小說。這么多年,我一直在寫“我”,并且,我已經“我”寫了好幾十萬字了。很多人問我,這種以個體經驗得以維系的寫作,真的不會枯竭嗎?我笑了,他們不知道,我,除了可以泛“我”之外,還可以虛構。
我說的“泛我”,是指,他者的故事用我向的、主格的視角去寫。我曾說,我即眾生。那么,這樣的“我”怎么會枯竭呢?用第三人稱的他者視角,會顯得隔,而且,情感方面,很難有代入感。
然而,在寫作過程中,這個把戲并沒有給我帶來多大的愉悅。寫作,真正的快樂來自虛構。
虛構,不是虛假。我虛構一個鬼怪,描摹出來,它還是個人的樣子。
一個瓢,即使你描得跟真的一模一樣,那也只是一個匠人的手藝。所以,在我看來,寫個人經歷的散文,即使打動了你,但從寫作上來講,其實它并沒有多高明。有人把一個“真”字奉為寫作的高標準,可是,丑陋,低俗,平庸,它們也一樣很真,真,跟好壞沒有關系。
我理解的虛構是,它沖破了既定事實的母本以犯規之姿達成了想象之馬的意形。最終它定格于滿足表達想要的效果。寫作,如果只是畫瓢,抄襲現實,復述經歷,那可以休矣。
寫作,如果不是由我來擬定每一個字的使命,不是由我來勾畫敘事的走向和人物的命運,不是重新虛構另一個我,不是由不可控的想象之翼帶著激情游走于字里行間,那么,寫作只是在搬運文字的尸體。
我得舉個例子。
現在我了解了一件真事。東莞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的負責人從大涼山帶回來一個14歲的女孩,因工廠風聲緊,暫時不收童工,所以,這個人就把女孩安排住進了自己的家,這引起了左鄰右舍的猜疑,有人想舉報他拐騙幼女。這個故事拿到手,虛構的激情足以讓人發瘋,它可以發展的方向太多了,好了,第一時間就想到不倫戀的人可以滾了,雖然它可以寫成一篇很好的小說。
我相信,很多人會從男女感情的方向著手,它的確是一個常規的切入口。可是,我拿到手,卻希望這個人不要把女孩送進工廠,而是要把她送進學校。但最終他的種種努力失敗了,這個城市的學校,都沒能接收這個文盲女孩。為了避免女孩進工廠淪為童工,這個人和他的妻子決定自己親自教她學習認字。
我之所以要寫這樣的故事,是因為,我真的希望這個愿景可以成真。我覺得我理解的文學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的另一個朋友聽到這個故事,他笑著說,這還用講,這個黑心的工頭很快把女孩轉給了東莞夜總會的媽媽桑,賺了一大筆錢。我聽了追上前踢了他一腳,雖然我知道,他說的恰恰是最有可能發生的。
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就虛構什么樣的故事。你心里有光,就不會虛構絕望。
那么,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朝著想要的方向。
一個寫散文的人,開了寫小說的眼,在一個現成的事件里,用虛構之筆寫著自己,寫著“我”,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犯規?
可是,寫了這么些年,發現有一些題材的確屬于純粹的小說,小說之于我,那是別人的故事,即使有我,也是躲在幕后。當我正要進入的時候,這個“我”就會跳出來理論一番,或者是,跟里面的主人公打架。寫作,對我來說,讓“我”憋住,或者是穿上別人的衣裳,用別人的嘴去說話,這都讓我難受極了,寫作也難以為繼。
那么,我在想,我能不能寫這樣的小說,“我”可以經常跳出來發一通議論,然后跨上想象之馬,去虛構一個又一個的我?
好像,也沒什么不可以的。
責編: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