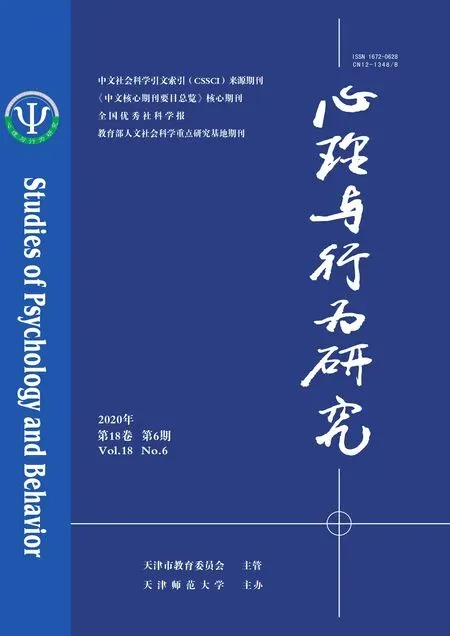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初中生閱讀成就的影響:閱讀動機和閱讀活動的中介作用 *
王曉誠 賈麗娜 金元英
(1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無錫 214122) (2 韓國高麗大學教育學院,首爾 02841)
1 引言
閱讀是個體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和了解外部世界的必要手段。閱讀能力構成了學習活動的重要前提,閱讀能力的不足會對其他必要技能的習得產生重大影響(Kirsch et al., 2002)。尤其對于初中生來說,他們正處于“透過閱讀學習新知”的階段,良好的閱讀能力能夠幫助初中生迅速獲取知識并掌握所需信息。諸多國際評估項目,如國際學生學業成就評估項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均把閱讀素養看作知識信息時代學生需具備的核心素養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及影響學生閱讀成就的因素有哪些,已成為世界各國教育研究者及相關工作者所關注的問題。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指個人或某一群體在社會中,依據其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源而被界定的社會位置,通常以父母職業、父母受教育水平及家庭經濟收入作為客觀度量的指標,反映了個體獲取現實或潛在資源的差異(Bradley & Corwyn,2002)。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顯著預測學生的學業成就: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學生的學業成就也越低 (任春榮, 辛濤, 2012; 舒華等, 2002)。Kieffer(2010)發現,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群體中,有80%的低年級學生不能熟練地閱讀,中高年級學生也面臨更多的閱讀障礙風險;PISA 和PIRLS 的相關研究結果則進一步揭示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家庭資源(如藏書量、父母讀寫支援)對學生閱讀成就的影響(Mullis, Martin,Foy, & Hopper, 2017; OECD, 2010)。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閱讀成就的影響往往通過一系列中介變量起作用,如親子閱讀(Leseman &de Jong, 1998;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父母教育期望(Bradley & Corwyn, 2002)、父母鼓勵(顧紅磊, 劉君, 夏天生, 2017; Baker, Scher, & Mackler,1997; Morrow, 1983)、父母對子女的讀寫指導(Evans, Shaw, & Bell, 2000; Sénéchal & LeFevre,2002)等。家庭投資理論認為,在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中,父母擁有更多的資本可用于投資子女的發展,包括物質投資(如豐富的學習資源、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情感投資(如鼓勵子女學習或表揚努力行為、開展更多的親子活動和交流),從而對子女的學業成就產生積極的影響(Davis-Kean, 2005; Sohr-Preston et al., 2013)。
近年來,研究者關注的家庭經濟地位與學生閱讀表現之間的中介變量,不再僅局限于父母特征,也開始轉向學生個體特征,如閱讀動機(顧紅磊等, 2017)、閱讀投入和閱讀興趣(溫紅博, 梁凱麗, 劉先偉, 2016)、自我效能感(石雷山, 陳英敏, 侯秀, 高峰強, 2013)等。其中,閱讀動機作為重要的個體特征,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閱讀成就關系之間起重要作用。首先,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學生具有更高水平的閱讀動機(劉玉娟,2012),閱讀動機又直接影響閱讀能力的各項指標,如文本理解、字詞識別、閱讀技能等(Baker &Wigfield, 1999; Guthrie, Wigfield, Metsala, & Cox,1999)。此外,閱讀動機還通過閱讀活動(如閱讀量、閱讀頻率)的中介作用對閱讀成就產生間接影響(Becker, McElvany, & Kortenbruck, 2010;Schiefele, Schaffner, M?ller, & Wigfield, 2012):學生的閱讀動機越高,就越傾向于選擇閱讀活動并在閱讀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而越容易成為一名熟練的閱讀者。
一方面,閱讀動機顯著正向預測閱讀活動。研究表明,閱讀動機水平較高的學生的閱讀量是閱讀動機水平較低的學生的三倍(Wigfield &Guthrie, 1997)。與外部動機相比,內部動機與興趣閱讀活動之間有著更大的相關(Baker & Wigfield,1999; Becker et al., 2010; Lau, 2004)。Lau 發現,將諸多變量同時納入回歸分析時,中學生的內部動機與閱讀活動的關系強度最大。可以說,在中學生的閱讀活動中,內部動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進行閱讀不僅是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同,或者為獲得某種獎賞,更重要的是為了滿足求知欲、興趣、好奇心以及意識到閱讀的重要性而進行主動、自覺地閱讀”(宋鳳寧, 宋歌, 余賢君, 張必隱, 2000, p.87)。
另一方面,閱讀活動顯著正向預測閱讀成就(宋鳳寧等, 2000; 張文靜, 辛濤, 2012; Anderson,Wilson, & Fielding, 1988; Cunningham & Stanovich,1997)。Cunningham 和Stanovich 發現,閱讀活動對學生在五至十年級之間閱讀理解進步的解釋力可達23%。PISA 的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每天閱讀時間大于30 分鐘及以上的學生,其閱讀成就顯著高于“不會為了樂趣而閱讀”的學生(張文靜,辛濤, 2012);這種閱讀投入行為被證實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所帶來的不利影響(Guthrie & Wigfield, 2000; Kirsch et al., 2002)。
基于已有文獻,本研究以閱讀動機和閱讀活動為中介變量,探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初中生閱讀成就的影響機制(見圖1)。研究假設包括,假設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直接影響閱讀成就;假設2: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影響閱讀動機,進而影響閱讀成就;假設3: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影響閱讀活動,進而影響閱讀成就;假設4: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影響閱讀動機,進而影響閱讀活動,最終影響閱讀成就,即閱讀動機和閱讀活動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閱讀成就的關系中起鏈式中介作用。

圖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閱讀動機、閱讀活動與閱讀成就關系的理論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法,選取中國東部某省3 所學校共499 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獲得有效問卷468 份。被試的年齡范圍為12~17 歲(M=13.3 歲,SD=0.97 歲)。其中,男生230 名(49.1%),女生238 名(50.9%);7 年級176 名(37.6%),8 年級145 名(31.0%),9 年級147 名(31.4%);城市、鄉鎮、農村學校的學生分別為2 5 5 名(54.5%)、189 名(40.4%)、24 名(5.1%)。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以父母職業、父母受教育水平及家庭經濟收入為主要指標(任春榮,2010)。具體包括5 個維度:父親職業、母親職業、父親受教育水平、母親受教育水平、家庭經濟收入。家庭經濟收入維度有17 道題,其余均為1 道題,共計21 道題。對于父母職業的測量,本研究按照師保國和申繼亮(2007)的標準,將職業分為5個等級,分別賦予1~5 的分值;父母受教育水平則包括“文盲”“小學或小學以下”“初中”“高中或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7 個類別,分別賦予1~7 的分值;家庭經濟收入采取被試報告家庭擁有物數量的形式進行測量,以避免學生因不了解家庭實際收入而拒答或亂填的情況(任春榮,2010)。參考PISA 背景問卷所提供的方式,要求學生報告家中有無互聯網、教育軟件等17 項設施,“有”計1 分,“無”計0 分,總分在0~17 分之間。參照有關研究(顧紅磊等, 2017; 石雷山等,2013),本研究分別將父母職業和受教育水平的得分轉化為標準分進行統計分析,并和家庭擁有物得分共同構成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指標。
2.2.2 閱讀動機量表
閱讀動機的測量參考了Baker 和Wigfield(1999)編制的閱讀動機量表(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MRQ)。研究指出,內部動機和外部動機對閱讀成就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內部動機顯著正向預測閱讀成就,而外部動機則顯著負向預測閱讀成就(Becker et al., 2010;Schiefele et al., 2012; Wang & Guthrie, 2004)。若將兩者同時納入閱讀動機的測量指標,很可能帶來結果相互抵消的效果(Schiefele et al., 2012)。因此,基于中文版MRQ 的修訂結果,本研究選取“挑戰”“好奇心”“參與度”3 個維度來測量學生的內部閱讀動機。每個維度有5 道題目,共計15 道題目。采用李克特4 點計分,分數越高,表明閱讀動機水平越高。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表明,該量表具有理想的結構效度:χ2/df=3.25,p<0.001,CFI=0.94,TLI=0.93,SRMR=0.05,RMSEA=0.07,所有觀測變量在對應的潛在變量上的標準化因子載荷為0.51~0.78。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
2.2.3 閱讀活動量表
閱讀活動的測量參考了Guthrie,McGough 和Wigfield(1994)的閱讀活動量表(Reading Activity Inventory, RAI)及Schaffner,Schiefele 和Ulferts(2013)的閱讀量量表。量表共3 道題目,分別測量學生“出于個人興趣的”閱讀量、閱讀頻率及每次的閱讀時長。采用李克特4 點計分,分數越高,表明閱讀投入水平越高。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表明,該量表具有理想的結構效度:χ2/df=2.26,p=0.13,CFI=0.99,TLI=0.97,SRMR=0.02,RMSEA=0.05。閱讀量、閱讀頻率和閱讀時長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分別為0.58、0.59 和0.51。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7,與先前研究結果類似(Stutz,Schaffner, & Schiefele, 2016; Wang & Guthrie, 2004)。
2.2.4 閱讀成就
將在本次施測前一周發布的語文期中考試成績作為學生閱讀成就的評估指標,該成績由學校教導處提供。參照有關研究(石雷山等, 2013; 武麗麗, 張大均, 程剛, 王鑫強, 2018),所有成績都以同一學校同一年級為單位轉換成標準分進行統計分析。
2.3 數據分析
采用SPSS 軟件的“期望值最大化”法對缺失數據進行處理,對變量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使用Amos 軟件的“最大似然估計”法對測量模型及結構模型進行檢驗。由于本研究包含兩個中介變量,參考Preacher和Selig(2012)的建議,采用Monte Carlo 法分別檢驗各變量中介效應的顯著性。如果中介效應平均估計的95%置信區間不包括0,說明此中介效應在0.05 的水平上顯著,反之則說明不顯著。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對數據進行Harman 單因子檢驗的結果,第一個公因子的解釋率為27.6%,低于臨界值40%(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同時,單因子模型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較差:χ2/df=17.44,p<0.001,CFI=0.51,TLI=0.39,SRMR=0.16,RMSEA=0.19。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2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對所有的觀測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變量之間呈顯著正相關(見表1)。對潛在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可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閱讀動機(r=0.21,p<0.0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閱讀活動(r=0.14,p<0.0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閱讀成就(r=0.12,p<0.01)、閱讀動機與閱讀活動(r=0.37,p<0.01)、閱讀動機與閱讀成就(r=0.20,p<0.01)以及閱讀活動與閱讀成就(r=0.21,p<0.01)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

表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矩陣
3.3 測量模型的評估
本研究采用了Kline(2011)提出的結構方程模型檢驗的“兩步驟法”(two-step approach)。即結構方程模型的檢驗需經過兩個步驟:一是測量模型的檢驗,該測量模型包括所有的潛在變量并假設變量之間是相互關聯的;二是在模型中添加有向路徑(directed path),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檢驗。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法對測量模型進行評估可知,該模型擬合較好:χ2/d f=3.3 6,p<0.001,CFI=0.94,TLI=0.91,SRMR=0.05,RMSEA=0.07。所有的觀測變量在對應潛在變量上的標準化因子載荷為0.50~0.86,表明所有的觀測變量都有效測量了所表征的潛在變量,可以進一步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評估。
3.4 結構方程模型的評估
結構方程模型的評估結果表明,模型的各項指標達到了良好擬合的標準:χ2/df=3.01,p<0.001,CFI=0.94,TLI=0.91,SRMR=0.05,RMSEA=0.07。由圖2 可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閱讀成就的直接效應不顯著,假設1 不成立。此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顯著正向影響閱讀動機,閱讀動機顯著正向影響閱讀活動,閱讀活動顯著正向影響閱讀成就。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閱讀成就的總效應顯著(β=0.13,p<0.01)。使用Monte Carlo 法對中介效應進行顯著性檢驗可知,閱讀動機(95%CI[-0.016, 0.084])與閱讀活動(95%CI[-0.045, 0.046])的獨特中介效應均不顯著,假設2 和3 不成立;閱讀動機和閱讀活動的鏈式中介效應顯著(95%CI[0.006, 0.081],β=0.023),假設4 成立。
4 討論
4.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閱讀成就的作用機制
本研究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閱讀成就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通過閱讀動機和閱讀活動的鏈式中介作用間接發揮影響。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學生更傾向于將出于個人的好奇心、對有挑戰性的文本的偏好、享受閱讀本身的樂趣等內在因素投入到閱讀活動中,而這種大量的、廣泛的自發閱讀最終帶來提升閱讀成就的積極效果。可以說,由于經濟收入、父母職業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差異,不同家庭對子女的閱讀投資存在較大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子女閱讀動機、閱讀活動乃至閱讀成就之間的差距。該結果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行為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一系列中介變量起作用的觀點相一致(石雷山等, 2013; 溫紅博等, 2016; Bradley &Corwyn, 2002)。
一方面,家庭經濟資本為子女提供基本的物質條件,如安靜的閱讀環境、豐富的書籍和用品,為子女開展閱讀活動、發展閱讀興趣奠定基礎(李毅,譚婷, 2019);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具備更為積極的閱讀態度和更高水平的閱讀興趣(Myrberg & Rosén, 2009),在這種家庭文化氛圍中,子女可能會潛移默化地模仿和學習父母的閱讀行為,獲得較高的閱讀投入。另外,中上階層的家庭或高學歷的父母往往對閱讀持鼓勵的態度(顧紅磊等, 2017; Baker et al., 1997; Morrow, 1983),并通過親子閱讀、示范閱讀等形式,以榜樣的力量提升子女的閱讀動機,幫助他們形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最終正面影響子女的閱讀成就。綜上所述,在討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作用時,除了已有研究中提到的父母特征的中介效應之外,也不可忽視學生個體特征的影響及其主觀能動性。

圖2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閱讀動機、閱讀活動與閱讀成就關系的結構方程模型
4.2 閱讀活動的重要性
結構方程模型的評估結果表明,閱讀動機并不直接作用于閱讀成就,而是通過改變學生的閱讀投入(如增加閱讀量和閱讀時長)來影響閱讀成就。這與已有研究結果一致:閱讀動機水平較高的學生更傾向于選擇閱讀(Wigfield & Guthrie, 1997),而大量的閱讀活動又能帶來一系列積極效果,如豐富其詞匯量并提升閱讀過程的自動化水平(Schiefele et al.,2012; Stutz et al., 2016)、促進閱讀策略的使用(Guthrie et al., 1999; Wigfield et al., 2008)、幫助學生積累各類主題相關的背景知識(McNamara &Kintsch, 1996),進而正向預測閱讀成就。
由此可知,要想提升學生的閱讀成就,僅僅提升內部閱讀動機水平是不夠的,還需研究能夠激發學生具體閱讀行為的策略。例如,提供豐富的閱讀資源與高質量的閱讀暴露環境,鼓勵學生在時間、數量及廣度上增加對閱讀的投入。在校外環境中,家長也應盡可能地為子女創造良好的閱讀環境,如增加家庭藏書量、為子女購買或推薦適合的讀物、開展各種親子閱讀活動等,讓子女更多、更全面地接觸多樣化的閱讀資源,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張文靜, 辛濤, 2012)。
4.3 教育啟示
本研究驗證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能夠通過閱讀動機和閱讀活動的鏈式中介作用來間接影響閱讀成就。該結果提示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雖然個體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可能一時難以改變,但可以通過提高學生的閱讀動機、開展多樣化的閱讀活動,最終達到提升閱讀成就的效果。例如,通過引導學生自主設計和實施閱讀任務,提高自主閱讀能力(Perry, Hutchinson, & Thauberger,2007),讓其感受到更多的閱讀樂趣,進一步激發內部動機;家長可以運用自身的知識儲備,參與子女的閱讀活動,展示積極的閱讀態度,并用榜樣示范的作用激發子女的閱讀動機和興趣。
4.4 研究局限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第一,樣本取自我國東部地區的3所學校,研究結果的代表性有待提升。第二,大部分數據通過問卷法收集而成,盡管研究采用的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問卷法的社會贊許效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未來研究還應嘗試采用觀察法、訪談法等多種方法對數據進行三角互證。第三,本研究使用學生的語文期中考試成績作為閱讀成就的評估指標,未來的研究還可嘗試采取標準化閱讀測驗的方式進行評估。
5 結論
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閱讀動機、閱讀活動及閱讀成就之間呈顯著正相關;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閱讀成就的直接效應不顯著,但可以通過閱讀動機和閱讀活動的鏈式中介效應對閱讀成就產生間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