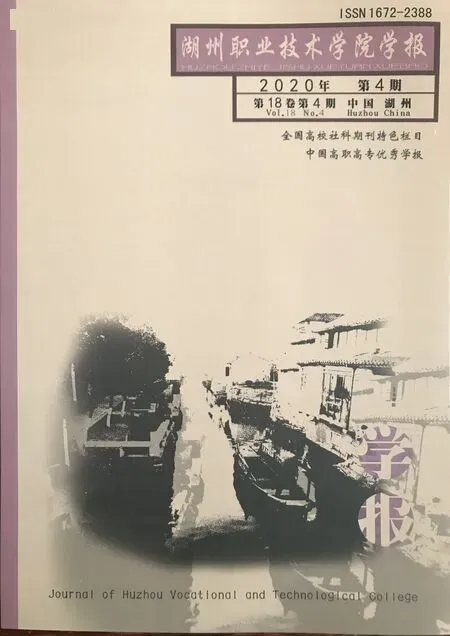存在主義哲學視閾下的《黑鐵時代》*
劉 皇 俊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存在主義既是一種哲學思潮,亦是一種文學思潮。存在主義的源頭可追溯至19世紀法國天主教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后經尼采、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推演,再到薩特、加繆等人的思考而蔚為大觀。“存在主義揭示人類存在的荒誕和困境,強調個人和自由。人通過自由選擇和行動實現自身存在的價值,強調經驗與思維、行動、態度和情感的結合。”[1]67-70顯然,存在主義推崇“人”和“個體”,倡導自我生存的積極性,揭示存在的荒誕,追求“個體”的自由。王小波的《黑鐵時代》充滿了對性、變形、異化的描寫,在隱喻和暗示中表現世界的荒誕。“個體”存在的孤獨,使得該作品呈現出鮮明的存在主義特征。《黑鐵時代》的敘述者“我”,在表哥經營的公寓中打工。表哥不到三十歲,頭頂就光禿禿的,有一小撮卓別林式的胡子。表哥雖是個文盲卻精于算計,稱他為小流氓也不為過。公寓的住客都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衣著考究,妝容精致,他們“都拖著沉重的腳鐐”[2]2。在“黑鐵時代”里,所有上過大學的人,都必須住在有營業執照的黑鐵公寓里。與其說這是公寓倒不如說是監獄。黑鐵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建筑內外的色調皆以黑色為主,“籠罩在一團黑暗的溫暖里”[2]9。公寓內,“窗子的大小剛夠區別白天和黑夜”[2]5。這里有一套嚴密的準則和制度,所有人都生活在規則之下。所有住進公寓的人,肘彎上都扣著一個鐵環,被一根鐵鏈串在一起,每天被關在暗無天日的公寓之中,但卻無人反抗、質疑黑鐵公寓的合法性。公寓房客如同奴隸一般,可以在中關村路口的“房客市場”進行買賣。在這里,所有人的一切都會受到嚴格監管,人們生活在黑鐵時代壓抑的制度之下,在荒誕的世界中迷失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正如敘述者“我”所說:“在黑鐵時代,人們總是等待著什么。”[2]21人們不知道自己在等待著什么?無論是公寓管理員還是被“囚禁”的房客,人們的生活似乎都沒有了意義。
一、黑鐵公寓的荒誕
“荒誕”或者說“荒謬”是存在主義的核心關鍵詞,是存在主義哲學解釋人與現實世界關系的落腳點,同時也是文學意味絕佳的生長點。它帶來的陌生化接受效果,辛辣絕妙的諷刺都是作家無法拒絕它的理由。在這里,哲學意義上的“荒誕”與文學創造上的“荒誕”達到了完美融合,它們互相豐富了彼此。
王小波筆下的荒誕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但又被世俗所遮蔽。在黑鐵時代,沒有人意識到荒誕的存在,人們更不會思考荒誕為何?黑鐵時代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所有人都必須按照“規則”辦事。受過教育的人必須住進黑鐵公寓,接受如同監獄般的管理。只有不識字又不會算數的人,才能當公寓管理員。管理員必須赤膊穿著皮衣。每個住客的肘彎都扣著一個鐵環,甚至住客上廁所都要接受管理員的監管。住客房間門口的紅燈連閃兩下,表示住客要去散步。住客必須由管理員牽著繩索才能離開公寓。《公寓管理手冊》上規定:“假如房客生了病,發燒在38 ℃以上,白血球在一萬以上,就可以免受鞭責。”[2]36
黑鐵時代荒誕為何?“荒誕”一詞意為“無意義”,而“無意義”又可細分為“不可理喻”和“無價值”。顯然,《黑鐵時代》所呈現的“荒誕”更傾向于“無價值”甚至是“虛無”之意。就如小說中401室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收到一紙通知,被判定為“專門人才”,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必須搬進公寓,接受權力的規訓。三十五歲獲圖林獎的計算機系校友,戴著鐫了“國之瑰寶”四字的24K黃金手銬。荒謬的是,手銬還需自己付費。在這里,知識分子的價值失去了意義,存在也幻化為虛無。難怪“我”要說:“人們說,所有的聰明人都住在公寓里,住在公寓外面的人都不夠聰明。聰明人被人像大蒜一樣拴成一串,這件事未必聰明。這世上最不幸的事就是吃了千辛萬苦,做成一件傻事情。”[2]4黑鐵時代之所以荒誕,就是因為它的“制度”,它的“規訓”,它的“監禁”。王小波曾經歷過中國文學史上較為荒誕的時代。他對于“規訓社會”有著深刻的感受。其“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呈現出諸多的荒誕書寫,透過符號化人物“王二”追問人何以存在?這使得哲學意義的“荒誕“與文學創造的“荒誕”在存在的本源性問題上達到了完美交融。王小波企圖通過對“個體”及“世界”荒誕甚至是虛無的書寫,來達到對邏各斯話語霸權的揭示和批判;在荒誕之中揭示文革背后的內在邏輯,反思、凝視被人們所遺忘的“黑夜”。在這一意義上,《黑鐵時代》從“個體”存在的話語表達上升到了“知識分子群體”存在的理性反思。在講師、女老師、音樂家、研究生、大學生等“個體”形象的背后,是對生活于“黑鐵時代”知識分子群體生存境遇的觀照。
王小波在《黑鐵時代》中構筑的“黑鐵公寓”似乎是一個荒誕的文學幻想,但又像是一個智者的預言,在荒誕滑稽、幽默揶揄中隱藏著對邏各斯話語霸權的批判與反思。王小波從生活在“黑鐵公寓”的“個體”入手,從他們的現實生存活動出發,去探尋存在的方式,追問“黑鐵時代”人們存在的意義。在這一意義上,達到了文本與讀者、理性與非理性、虛構與現實、作者與作者、個體與群體的對話。
二、孤獨個體的存在
孤獨是人類普遍的情感體驗。存在主義包含多種思想成分,但其最核心的一條是強調關注“人”本身,主張把人作為“個體”來看待。這有別于黑格爾式的整體歷史觀、傳統中國式的群體論。在談到“個體”時就不能回避“孤獨”,二者往往難分彼此。存在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曾提出了“孤獨個體”的概念。在他看來,“人”本來就是作為一個孤獨的個體而存在的,存在是個體的,亦是主觀的。因此,“理性不能解決人生問題, 只有孤獨、厭煩、絕望、恐懼等非理性情緒體驗和死亡、苦難、罪過、斗爭等‘邊緣處境’,才能使人接近它的存在。它所描繪的是個人的孤獨,人與人之間不僅能夠相互理解甚至還會相互折磨的悲涼情景,這便是人類的生存狀態。”[3]52-55王小波在《黑鐵時代》中建構了一群“孤獨個體”符碼。他們的“孤獨”是與“荒誕”緊密相連的。他們對于孤獨抱著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接受孤獨,一如他們接受荒謬;另一方面,他們又拒斥孤獨,渴望得到慰藉,以求消解孤獨。
數學系的禿頭老校友、401室的鋼琴家、愛慕虛榮的銀行女職員、404室的女老師,甚至是“我”、表哥、綠頭發女管理員都是這類“孤獨個體”符碼。他們在百無聊賴的荒誕世界里,找不到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孤獨成為他們的一種普遍情感體驗。他們是被“異化”的個體,通過“性”甚至是各種各樣扭曲怪誕的方式言說著自己的存在。在“我”看來,“黑鐵時代的人有很多怪癖”[2]13:401室的女鋼琴家讓“我”到一號房間等她,并把她的手腳都拴住,背帶解開。表哥在對講機里讓“我”用酒精給她擦背。擦著擦著,表哥握著一根黑色藤條走了進來……“表哥和所有搞得到的女孩之間全都不干不凈,滿腦子都是下流主意。”[4]59王小波的小說中有著非常多的“性狂歡”書寫,甚至是違背倫理道德的性書寫。《黃金時代》中的王二和陳清揚“搞破鞋”,他在身體的歡愉中感覺到自己和外面的世界合為了一體。王二甚至說:“在我看來,這東西無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5]33《黑鐵時代》中的“我”問她可以嗎?因為她的回答,“我”冷淡又振奮,“就如一個小孩打開屬于自己的糖盒子,取出一顆糖,然后把盒子仔細蓋好。”[2]33她使“我”興奮不已……
在這些赤裸裸的性書寫的背后,是一個個“孤獨的個體”。他們正走在遠離人的命運的途中,即海德格爾所說的“離家”狀態。他們遠離了自己詩意的生存根基,忘記了自己存在的本真意義,墜入了無盡的黑夜與孤獨之中。在荒誕的世界里,他們如行尸走肉一般,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納現實預設的某種身份,可能是公寓管理者亦或是公寓房客;他們不得不忘記本真的自我,在強大的外部力量面前顯得如此渺小。個體存在的合法性、真實性、價值性被“制度”消解了,精神家園已經幻滅。極權政治和規訓社會讓人們感到孤獨、虛無、荒誕,他們不得不訴諸于“性”“虐戀”“異化”以獲得自贖。雖然,這可能并不能消解孤獨,甚至適得其反,但對這些處于孤獨困境的個體而言,這是他們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亦是他們凸顯生命權力意志的方式。于是,王小波筆下的人物企圖以此來拒斥孤獨,從“孤獨個體”的困境中獲得解脫;作家本人也將性書寫作為一種有力的話語方式,以此來向讀者“說話”。
三、自由意志的追尋
如果說“荒誕”“個體”“存在”是存在主義的前三個關鍵詞,那么“自由”便是第四個關鍵詞。在此,有必要對“自由”的內涵作一下解釋。盡管存在主義對自由的解釋各有千秋,但他們共同指向“個體”。存在主義的人生是悲觀痛苦的,但存在方式的選擇權把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因此,薩特高呼人生而自由。正因為如此,存在主義才被稱為真正的人道主義。“自由”之于存在主義大概有兩層含義:一方面,自由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永恒的向往;另一方面,自由是人對抗荒誕現實、擺脫生存困境的方式。王小波曾自稱“自由主義者”,大聲疾呼“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6]1。他辭去穩定的教職,只愿做個自由撰稿人。王小波是愛自由的,可我們翻遍《黑鐵時代》也難以找到自由的氣息。《黑鐵時代》通篇皆是“禁錮”“規制”“服從”的陰影。住客也好管理員也罷,都沒有自由可言,更別談基本的尊嚴。恰恰正是這種“黑夜”式或者說“深淵”式的描寫,才愈發表現出作者對自由的渴望與呼喚。
“所有住進公寓的人肘彎都扣著一根鐵環,被一根鐵鏈串在一起,只有‘我’和表哥例外。”[4]57沒有人覺得有什么不對,人們變身成了服從的機器。“每個房客規規矩矩坐在自己的床上”[4]61,大家都懂規矩了,才省我表哥的事。黑鐵公寓不僅管理嚴苛,還施行懲罰制度。401室的女孩因為違反規則,被反綁雙手,鉆進了鳥籠。而“能夠離開這座小籠子還不是激動人心的原因----離開了小籠子還要走進大籠子----激動人心的是她總算是等到了什么。”[2]24或許,在黑鐵公寓的管理之下自由意志已經湮滅了,它僅存在于遙遠的過去。可怕的不是沒有自由,而是意識不到自由應該存在。黑鐵時代中“規制”“極權”“禁錮”的力量越嚴酷,邏各斯話語霸權越強大,這能說明人們對于自由民主的強烈呼喚。王小波在小說中不僅僅描繪了個體存在的孤獨與虛無,在更深的意義上,他的眼睛凝視了極權泛濫、人性異變的社會現實。“王小波之所以不惜筆墨刻畫現實環境對人的嚴酷壓制, 關鍵就在于呼喚‘人的自由’依舊是東方文學的表現主題之一。”[7]76-83
四、結 語
黑鐵時代的荒誕不僅僅是一種存在感受,它已經演變為一種時代“癥候群”。人在荒誕之中被異化、被扭曲、被消解,在強大的邏各斯話語霸權面前一切都顯得那么蒼白無力。住在黑鐵公寓里的“孤獨個體”,選擇用“性”“虐戀”“幻想”來面對“孤獨的困境”以及“存在的荒謬”。這是他們為了擺脫“孤獨”與“荒謬”所做的努力,也是他們東方式的“詩意的棲息”。他們似乎忘記了自由本應與生俱來,人的存在本來就是自由的。在“黑鐵時代”,自由被遮蔽了,人們忘記了“自由”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沒有人會質疑這個世界的荒誕,也沒有人會思考自由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