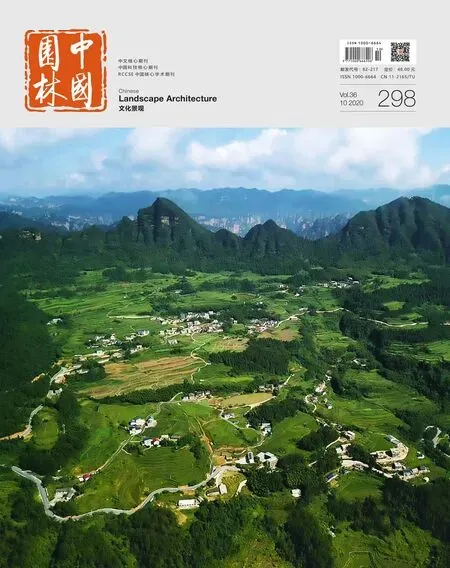“連接自然與文化”①:西方哲學背景下的全球議題
(澳)史蒂文·布朗 撰文
韓 鋒 程安祺 譯
我住在一個叫“格京塔”(Gozinta)的鄉村農場,占地60hm2,距離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80km。農場位于低至中等陡峭的山坡上,主要植被群落為開闊的脆性橡膠林。那里有東部灰袋鼠、紅頸袋鼠、沼澤袋鼠、普通袋熊和短喙針鼴鼠等多種鄉土動物,以及超過90種被記錄的鳥類。該地區擁有超過20 000年的原住民歷史,位于恩古納瓦(Ngunawal)、貢貢古拉(Gungungurra)和尤因(Yuin)3種語言文化族群聚居地的邊緣地區,在19世紀20年代曾被殖民入侵者(主要是英國)占領②。博羅溪(Boro Creek)是一條狹窄的間歇溪流,流入肖爾哈文(Shoalhaven)河。大約在19世紀90年代,博羅溪附近出現了第一座農舍及其附屬建筑。我的農場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種植橄欖樹,邊緣處用作綿羊、牛牧業養殖以及農作物的種植,是一處自然環境和文化歷史深刻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期的人文地理領域。該學科加上風景園林學、園藝學、建筑學、人類學、人種學、地理學、考古學、生態學、藝術史等學科領域的概念,引領了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21世紀的文化景觀保護實踐的發展。如今,隨著遺產內涵的拓展、技術的進步、氣候變化及可持續等環境挑戰的影響,以及對于更好地理解和闡釋人與場所、景觀、非人類物種之間聯系的迫切需求,文化景觀的實踐已變得越來越復雜。
在遺產保護領域,文化景觀的理念與遺產地的管理與安全保衛緊密相關。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遺產保護已經從關注建筑、城市中心以及考古遺址轉變為涵蓋越來越多樣化的遺產形式(如非物質遺產、工業遺產、20世紀遺產和外太空遺產),同時開始關注越來越大的地理區域。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設立“文化景觀”作為文化遺產的新類別[1]。委員會根據西方文化框架對文化景觀進行了分類:人類有意設計和創造的景觀(以歷史園林和公園為代表),遺址景觀和持續演進的景觀或活態景觀(包括鄉村或城市),以及關聯性景觀(象征或精神)[2]。
正如澳大利亞人文地理學家萊斯利·海德(Lesley Head)指出的那樣,文化景觀概念不是凝固的,而是“隨時間發生變化,并在世界不同地區、不同學科和不同政府背景下有著一系列不同理解”[3]。根據大量的相關文獻,文化景觀可以總結為三大類意義[4]。
1)文化景觀作為物質實體。從物質或有形的意義上講,文化景觀是地球上部分被選定的、經過人類-生態互動(或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區域。
2)文化景觀作為概念和過程。在此,文化景觀不僅是有形的場所(或物質實體),而且其內涵更加廣泛,可以包含關聯性和象征性景觀、虛擬空間以及城市歷史性景觀等。
3)文化景觀作為方法和工具。雖然文化景觀方法論可能不像城市歷史景觀(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5]方法那樣明晰,但文化景觀研究中有大量的實踐方法:例如景觀特性描述、景觀考古學、傳記和生物水文學方法、文學表現、世界遺產方法[6]、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的《遺產提升工具包》(Enhancing Our Heritage Toolkit)[7],以及各種保護區管理方法。
世界遺產保護中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西方(即歐洲和北美)思想的普遍影響:自然環境和文化歷史是相互分離的領域。也就是說,“自然”與“文化”是二元的、對立的,彼此分離的。考古學家和遺產學者丹尼斯·伯恩(Denis Byrne)指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文化-自然二元論是西方現代性的基礎,因此討論文化-自然議題對于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相遇具有開創性意義。[8]”
世界遺產就是將“自然”與“文化”分離的系統之一。舉例來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提名程序和實踐就是基于這樣的分離[9-10]。這種分離在“突出與普遍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的評估標準中很明顯,6項標準適用于文化遺產,4項適用于自然遺產。即使是“混合遺產”類別(即滿足一項或多項文化和自然標準的世界遺產),仍然保持自然和文化之間的區別,而不是將它們視為相互聯系的。雖然《世界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已經實施了48年,但是《公約》[9]仍然將這2個領域視為分離。盡管在1992年設立了“文化景觀”遺產類別,并于2005年建立了符合世界遺產標準的文化景觀獨立名單,這種分離狀況仍然存在[11-12]。
在本文中,我將重點介紹2 個全球性非政府組織,IUCN 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的工作,以及二者為“架構”自然與文化之間的橋梁所做的合作努力。IUCN和ICOMOS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咨詢機構,2個機構都認識到有必要對混合世界遺產或文化景觀世界遺產的提名地進行聯合評估。直到最近,這類評估還是各自分開進行的。我重點介紹這2個全球性組織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和推廣他們在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為更好地連接自然與文化遺產的治理和管理實踐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和引領作用。
1 IUCN:向文化轉向
IUCN于1948年10月5日在法國楓丹白露成立。
作為第一個全球環境聯盟,IUCN將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召集在一起,其共同目標是保護自然,它的目的是鼓勵國際合作,并提供科學知識和工具用以指導保護行動。如今,IUCN擁有1 300多名成員(包括國家、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原住民組織),以及15 000多名國際專家。IUCN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多樣化的環境保護網絡,持續領導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將其作為實施巴黎氣候變化協議(Paris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等國際協議的關鍵手段[13]。
IUCN自成立以來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拒絕將景觀的文化性與自然性平等看待。早在成立初期,IUCN就倡導“荒野”(wilderness)和“堡壘”(fortress conservation)概念和保護模式,兩者均導致了原住民和其他公民從保護區內被(通常是他們的社區家園)驅趕出來。
這種狀況直到1998年IUCN“保護地非物質價值”(Non-Material Values of Protected Areas)工作組成立,才發生顯著的變化。2003年,工作組將其名稱更改為“保護地文化和精神價值”(Cultu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of Protected Areas,CSVPA)③,該名稱的更改與在南非德班(Durban)舉行的IUCN第五屆世界公園大會有關。此次大會上,原住民譴責IUCN以往的自然保護實踐,對IUCN在承認和尊重原住民的權利、責任以及保護方面提出了挑戰[14]。
為了使保護區包括半自然、農業和城市景觀這些類別,IUCN在1994年提出了6類保護地分類體系[15]。2008年,IUCN對此分類體系進行了修訂,其中的2個類別強調了人類創造力的作用。
第V類 陸地/海洋景觀保護區:這類保護區經過人與自然之間的長期相互作用,產生具有顯著而重要的審美、生態、文化和科學價值,安全保衛此類相互作用關系的完整性對于保護和持續地區發展以及相關的自然保護和其他價值至關重要。
第VI類 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保護區:第VI類保護地的目的是保護生態系統、棲息地和關聯的文化價值、傳統自然資源管理系統[16]。
2012年,在韓國濟州島舉行的IUCN世界保護大會上,提出了一份關于IUCN和ICOMOS協同合作的提案,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將自然與文化融入世界遺產體系[17]。
2 ICOMOS:向自然轉向
ICOMOS成立于1965年。在成立之初,ICOMOS通過了《威尼斯歷史遺址保護和修復憲章》(Venice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以下簡稱《憲章》)。《憲章》是一部于1964年由一群遺產保護專家(主要是建筑師)在威尼斯制定的保護導則。《憲章》為歷史建筑的保護和修復提供了框架,但未提及“自然”或“自然遺產”。ICOMOS從最初對歷史建筑的聚焦,經過55年的發展,其關注點已包含多種類別的文化遺產,這在其29個國際科學委員會的工作成果中可見一斑[18]。
ICOMOS的任務是保護文化遺產。它是一個全球性的非政府組織,致力于促進將理論、方法和科學技術應用于文化遺產保護。該組織擁有約11 000名個人成員、300名機構成員、110個國家委員會成員以及29個國際科學委員會。
在總的歷程中,ICOMOS并未有效參與到自然遺產的保護,而是延續了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分離的傳統西方觀點。不過,一些ICOMOS的官方文件也承認自然和文化存在某種交疊關系。例如,澳大利亞ICOMOS的《巴拉憲章》(Burra Charter)指出[19]:
1)憲章可以“適用于所有具有文化價值的場所類型,包括具有文化價值的自然、原住民和歷史場所”(序言;在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2中也有提及[20]) ;
2)“場所具有廣義的范疇,包括自然和文化特性”(第1.1條;解釋性說明);
3)在“某些文化中,自然和文化價值不可分割”(第5.1條;解釋性說明)。
《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指出[21]:
1)遺產地包括其自然環境(第2條;注釋);
2)某些類別的遺產,例如文化景觀,可以具有重要的自然價值(第3條);
3)遺產的保存狀況與其自然和文化特性有關(第17條;注釋)。
3 IUCN-ICOMOS在自然-文化融合上的合作
自2013年以來,IUCN與ICOMOS開始探索更緊密的合作方式。開展這項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學習和創造新方法,集中認知和支持重要陸地與海洋景觀的自然、文化和社會價值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聯特征”[22]。這項工作正在進行的2個關鍵項目是“連接實踐項目”(Connecting Practice Project)和“自然-文化/文化-自然之旅”(Nature-Culture/Culture-Nature Journey),這2個項目我都參與了[23]。
2013年10月啟動的“連接實踐項目”是一個合作項目,旨在定義新的方法和策略,在世界遺產體系中進一步融合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迄今為止,該項目共經歷了3個階段④,每個階段都基于與特定世界遺產地的管理者和社區的合作[24-29]。3個階段的研究目標和遺產地分別如下。
第一階段(2013—2015年):此階段采用“邊做邊學”的方法,在“考量自然和文化價值時制定更內在關聯的策略”,同時對“IUCN和ICOMOS的實踐和制度文化”進行批判性評論[29]。核心成果是在IUCN和ICOMOS之間建立了合作的工作程序。第一階段的世界遺產研究案例是蒙古阿爾泰山脈的石刻群(Petroglyphic Complexes),埃塞俄比亞的孔素(Kongso)文化景觀,以及墨西哥的圣卡安(Sian Ka'an)生態保護區。
第二階段(2016—2017年):該階段總結第一階段的經驗教訓,“加強世界遺產地治理和管理的實踐性措施”[29]。《遺產提升工具箱》這一原來被用以評價自然遺產管理有效性的工具,被應用于文化遺產地[7,30]。該階段的世界遺產研究案例是匈牙利的霍爾托巴吉(Hortobágy)國家公園、南非和萊索托的馬洛蒂-德拉根斯堡(Maloti-Drakensberg)跨國國家公園。
第三階段(2019年至今):此階段的重點是生物文化實踐、農業景觀及世界遺產對于遺產地變化的管理。預期成果是相關概念和術語草案[25]。這一階段的世界遺產研究案例包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艾恩文化遺址(Cultural Sites of Al Ain)、塞內加爾的薩盧姆河三角洲(Saloum Delta)和中國的紅河哈尼水稻梯田(Honghe Hani Rice Terraces)文化景觀。
從“連接實踐項目”發現,IUCN 和ICOMOS如要更好地融合自然和文化遺產合作,需要在工作中進一步考慮3個問題。首先,需解決IUCN和ICOMOS內部以及2個機構之間的體制與實踐分歧;第二,提升專家和機構的能力,促進對遺產自然和其價值的整體認知;第三,修訂世界遺產治理和管理政策框架和指南[29]。其中一個突出的關鍵,是要具備制訂真正融合自然和文化遺產的管理規劃的能力。
與“連接實踐項目”并行運行的另一個項目是“自然-文化/文化-自然之旅”(以下簡稱“自然文化之旅”)⑤。該項目包括IUCN和ICOMOS領導層的一系列對話和會議。第一次“自然文化之旅”于2016年在美國夏威夷舉辦的IUCN世界保護大會上舉行,第二次則在2017年在印度德里舉辦的ICOMOS大會和科學研討會上舉行[30],2次會議的成果文件均總結了工作、討論和思想成果[32-33]。隨后,在全球各地的會議上舉行了許多這類“旅行風格”的活動。這些自然與文化的對話,從全球層面到國家和地方各級,不斷細化、具體化[34]。
2020年10月1 —10日,擬在悉尼舉行的第20屆ICOMOS大會和科學研討會(GA2020)將是“自然文化之旅”項目的里程碑。在這次會議中,IUCN和ICOMOS將簽署一項協議(或備忘錄),認可2個組織之間有必要繼續合作,在地區、國家和國際各級的工作中更好地融合自然與文化。但是,由于全球COVID-19大流行,澳大利亞和世界范圍內的社會經濟生活和國際航線受到限制,何時恢復正常無法確定,這一重要的全球會議已推遲至2023年9月。
4 為什么IUCN和ICOMOS關于自然-文化的合作工作是重要的?
我認為有2個主要的原因(雖然還有其他原因)。
首先,西方思想與哲學中自然與文化的分離,對包括原住民在內的非西方的國家和社區具有破壞性的負面影響。中國學者韓鋒提供了很好的案例。韓鋒描述了文化景觀概念在中國的世界遺產理論和實踐領域所遭遇的困境,特別列舉了廬山和五臺山2個世界遺產例子[10,35]。從本質上講,兩者都是文化景觀(世界遺產體系中的“文化遺產”的一種形式),反映的是“景觀中的自然與宇宙信仰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35],而不是中國最初申報的“混合遺產”。換言之,將這些世界遺產地提名為(自然與文化分離的)“混合遺產”,其價值核心有悖于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這項合作工作強調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的分離式管理會導致立法、管理和實踐無法在遺產地奏效。以世界遺產地塔斯馬尼亞荒野地(Tasmanian Wilderness,澳大利亞)為例,它符合3項文化遺產和4項自然遺產標準,是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混合世界遺產[36]。同時,它受到國家或地區級別多種自然和文化立法保護(包括將原住民與“歷史”或非原住民文化遺產聚居地的分離式保護),其中包括《聯邦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1999)》(Commonwealt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塔斯馬尼亞州的法律如《自然保護法(2002)》(Nature Conservation Act)、《國家公園和保護區管理法(2002)》(National Parks and Reserves Management Act)、《歷史文化遺產法(1995)》(Historic Cultural Heritage Act)和《原住民遺產法(1995)》(Aboriginal Heritage Act)。理想情況下,《塔斯馬尼亞荒野地世界遺產管理規劃》(the Tasmanian Wilderness World Heritage Area Management Plan)應將其文化和自然價值進行整合性規劃[37]。但是,跟許多此類規劃一樣,即便規劃將此遺產地稱為“杰出的土著文化景觀”,規劃中的文化與自然價值管理仍是分離的[37]。規劃在某種程度上呼吁抵制“荒野”一詞,“荒野”一詞的意思是“空無一物”(empty),歪曲詆毀了塔斯馬尼亞超過40 000年的土著居住史[38]。因此,在當前的立法和管理上,自然價值和文化價值的保護仍然是分離的。對于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緊密相互關系的認知,無論在管理分類上,還是在西方文化與土著宇宙觀之間的重大差異認知上,我們都知之甚少[39]。
5 現在往哪里走?
自2013年以來,IUCN和ICOMOS合作開展的融合自然與文化工作取得了超預期的成果,并且影響越來越廣泛。但是,包括世界遺產和大多數保護區系統在內的西方體系,制定真正能融合自然和文化的管理規劃和治理體系的能力仍然不足。對自然-文化遺產價值進行整體性評估并以此作為管理行動的基礎意味著什么?全面融合自然與文化的管理規劃有哪些模式?現有的管理文件是否真正地融合了自然和文化,而不是僅將它們集結起來歸置于一個文件之中?此類工作對西方國家始終是一個挑戰。在我看來,這項工作的領導者來自那些自然與文化未被或至少沒有被嚴重分離的地區。我建議原住民社區、地方社區,以及他們的知識、經驗、語言和世界觀,應該在進一步推進“自然文化之旅”工作中占有核心地位。
最后,回到我的澳大利亞鄉村住所,我熱衷于從事這樣的工作——為我的鄉村制定管理規劃,將文化和自然的屬性、價值以及保護行動相互關聯起來。
注:本文是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最初幾個月寫作的。疫情有著一個顯著的“積極”方面,那就是全球空氣質量的改善、碳排放的減少,以及為這些世界遺產,無論是文化、文化景觀、自然還是混合遺產提供了“喘息空間”,這些遺產地通常都有大量的游客。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CROM)準備了題為《COVID-19——ICCROM關于保護遺產的呼吁》的宣言(COVID-19:Call of ICCROM for Protecting Heritage)[40]。該宣言呼吁遺產工作者齊心協力,尋找利用遺產作為后COVID-19時代恢復社會與增強韌性的方法。對我而言,這包括運用文化景觀方法,整體保護文化和自然價值。
注釋:
① 在本文中,筆者使用“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這一復合詞來定義人類、非人類、超越人類(例如精神、創世祖先)的要素和景觀是緊密關聯的(即一體或相互作用的);而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一詞的含義是自然和文化是對立與分割的2個領域。
② 譯者注:Ngunawal、Gungungurra和Yuin語言群體為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土著聚落。
③ 此工作小組于2009年成為IUCN 永久“專家小組”(Specialist Group)。
④ 第四階段正在計劃中。
⑤ “自然-文化之旅”(Nature-Culture Journey,NCJ)常用于IUCN作為該項目領導組織時,而“文化-自然之旅”(Culture-Nature Journey,CNJ)用于ICOMOS作為該項目領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