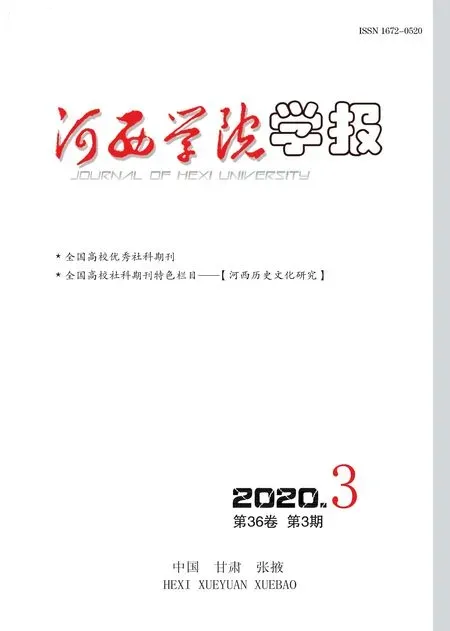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新興學術領域的構建實踐
——評《教育人類學視野中的裕固族教育研究》
后慧宏
(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北京 100081)
一、邏輯質詢: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的構建三重疑問
民族教育研究對象主要是民族教育實踐中的某種現象、潛在問題或客觀規律,并且出于對民族教育的人文關懷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大批學者已投身民族教育研究領域。那么何謂“裕固族教育研究”?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來看,裕固族教育研究固然是以探究裕固族及其聚居區的教育活動及其文化價值為要旨的學術領域。[1]9既然裕固族教育研究被部分學者認定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來加以構建,也吸引了大批包括鐘進文、巴戰龍、安維武等本土中青年學者在內的研究者參與。那么作為一名民族教育研究者,筆者對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被構建持有三點疑問:其一,何以需要,即裕固族教育研究為何需要作為學術領域被加以構建?其二,何以可能,即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如何才能成為可能?其三,何以實現,即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目標如何實現?帶著以上問題,筆者關注了裕固族青年學者巴戰龍博士及他的系列著作。
二、價值選擇: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何以需要?
基于對三重疑問的質詢,筆者通過閱讀任職于北京師范大學的巴戰龍老師所著述的并于2017年4月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人類學視野中的裕固族教育研究》來推進思考。首先筆者想通過閱讀著作來消解第一個問題,即尋找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何以需要?在作為本族學者的巴戰龍博士看來,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其一,裕固族研究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領域,其中歷史研究、語言研究和民俗研究的成果最多,尤其是西部裕固族語研究最為國際化、學術水平逼近國際一流水平。裕固族教育研究是裕固組研究的一個薄弱領域,也是一個蘊含無限潛力的領域。[2]2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得以建構,能更好地為發展裕固族教育和保持裕固族語言服務,如通過推行雙語教育來培養“民漢兼通”型雙語人才。在人類學中,往往把語言看作是“文化資源”和“文化實踐”。人類學視域下,雙語教育具有培育人類共同文化、尊重人類差異、傳承與保護各民族優秀文化的價值意義。[3]其二,早期記述“錫喇回鶻兒”現代學校教育活動的《祁連山北麓調查報告》[4]和傳記《顧嘉堪布傳——祁連山藏民教育之創辦者》[5]以及后來的相關研究均涉及裕固族教育,隨著裕固族教育研究探索與實踐,“何謂裕固族教育研究”成為最基本卻又難以回答的問題。基于此,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需要主動作為知識整合和領域構建,從而來吸引更多學者涉足這一新興領域研究。
三、雙重依據: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何以可能?
(一)著作劃定了裕固族教育研究對象范圍
人類學視野中的教育研究講求以“他者的眼光”來審視現實問題,進而做到“推他及己”,這是教育人類學的基本范式。那么巴戰龍博士作為裕固族學者對本民族教育研究領域學術構建何以可能?這就需要我們從領域構建的學理分析入手來觀照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實現過程。一方面,從學科發展視角來看,隨著“裕固學”取代“裕固族研究”的逐漸興起,裕固族教育研究被整合為裕固學的一個核心的子領域是這一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2]2另一方面,從學術領域構建視角來看,任何學科中新興研究領域的構建實際是對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的劃定,即研究領域是研究對象的范疇化和特定化,這種過程實際也是研究領域被持續地刻畫、深化和拓展,并被突顯和承認的過程。因此,確定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對象成為該領域被加以構建的邏輯起點,裕固族教育研究對象與功能、性質與定位、學科基礎與理論淵源、方法與倫理等的論述則是領域得以構建的基礎研究工作。
(二)以“教育人類學諸學科”為基礎開展學術研究
凡是新興學術研究領域的開辟,皆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學理基礎、獨特的學術思維和豐盈的人道主義情懷,更需要親歷親為的行動能力和不拘一格的創新能力。首先,構建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需要專業型研究者作為先行者。巴戰龍先生作為裕固族教育理論與實踐并重的研究者,他將裕固族教育研究創設為一個新興學術領域并加以建構,實際上是作為局內人或行動者研究本民族教育可以規避“壁上觀”或書齋式偏見,還會使所開展的研究因使命感和責任感驅動、務實和切實的態度做法而更加深入且全面。其次,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新興學術領域的構建需要相關學科提供學理基礎。根據巴戰龍博士的觀點來看,裕固族教育研究尚處于發展中,需要更多的發掘和分析關于裕固族教育的生物事實、心理事實、社會事實和文化事實,[1]21所以他在領域構建中將“教育人類學諸學科”作為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學科基礎。最后,領域構建需要學術研究成果來佐證。巴戰龍先生作為專業型研究者以“教育人類學諸學科”作為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學科基礎,進而開展了系列裕固族教育研究活動并產出了大量研究成果,這也為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佐證。
四、實踐取徑: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何以實現?
(一)厘定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的本體論問題
巴戰龍博士的著作《教育人類學視野中的裕固族教育研究》,顧名思義,是從教育人類學的視角切入,通過對“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加以論述來嘗試為“領域構建”的奠定基礎。
首先,巴戰龍博士根據“活動說”和“關系說”兩種解說來把握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對象并指出,“從教育人類學的研究風格和學術理路出發,裕固族教育研究最核心的對象是教育活動,但是專家學者又常常不能止步于對教育活動的分析,而是需要更進一步通過對教育活動的分析來透視各種‘關系’,例如國家與社會、制度與行動的關系等等。”[1]5確定了裕固族研究所在的對象,我們還需要將裕固族教育研究置于特定情境中來界定其具有哪些功能?著作中將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亞(子)領域來賦予其兩種特定功能:其一,作為本體功能的學術功能;其二,作為附屬功能的咨詢功能。[1]6-7同樣,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質與定位也是其被構建為子領域的要素。
其次,巴戰龍博士從整體論視角切入對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質和定位做了思考與探索并指出,裕固族教育研究是多學科參與其中的學術領域,同時也是民族研究和教育研究的交叉學術領域。[1]13裕固族教育研究同其它民族教育研究工作一樣,需要關注語言學、教育學、心理學、歷史學、管理學等學科理論與實踐,這些學科為其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提供了方法論借鑒。至于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實際是介于確定與不確定之間的動態平衡的社會和文化過程,他在著作中結合社會學和人類學相關理論指出,“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種綜合性的學術領域,也是一種中觀性的學術領域。”[1]14定位形塑性質,性質規制定位,二者相互牽制,不可分可。
再次,基于對“惟學科主義”和“惟超(跨)學科主義”的批判而卻不反對從具體學科視角出發研究裕固族教育,巴戰龍博士將裕固族教育研究定位為綜合性學術領域,并指出把“教育人類學諸學科作為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學科基礎”是出于對領域建構和發展處于“初級階段”而做出的較優選擇。[1]22根據作者的陳述來看,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學術領域未來進一步擴張必將借鑒其他學科基本理論及研究方法。
最后,基于對裕固學和裕固族研究的整體觀照,巴戰龍博士發現裕固族教育研究處于薄弱領域,與裕固族各項這會事業發展不相稱,所以確定裕固族教育研究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并加以建構成為必要。同樣,這個新興領域也是一個多學科參與和互動的學術領域,這一學術領域借鑒了國際少數族群教育發展和研究經驗。
(二)站位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專門領域所開展研究
著作第二編和第三編在梳理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遵循“歷史—主題—政策”并置的邏輯,撰寫了系列關照學校教育、社區教育和家庭教育三種形態下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學術論文。第一類,裕固族教育研究進展述評類文章。主要有《成就與問題:中國裕固族教育研究六十年》《近五年來裕固族教育研究進展述評——以期刊報紙文獻為例》《近五年來裕固族教育研究進展述評——以學位論文為例》《裕固族教育研究新成果——〈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第一中學校志〉述評》。[1]37-76第二類,裕固族教育主題學術論文。諸如《簡論21世紀裕固族教育的文化使命》《裕固族學校教育功能的社會人類學分析》《人口較少民族地區縣域學前教育發展的教育人類學研究——以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為例》《裕固族學校舞蹈教育發展芻議——以鄉土教材〈裕固族舞蹈〉為中心》《裕固族兒童“剃頭儀式”的教育人類學研究》《學校教育與地方知識關系探究——基于一項裕固族鄉村社區民族志研究》《裕固族文化融入國家基礎教育課程體系問題的調查研究報告》《在學校教育中追求語言公平傳承的歷程——對三次裕固語教育試驗的本質性個案研究》《打造雙語家庭——裕固族語言文化遺產傳承的新思路》《如何打造雙語家庭——裕固族語言文化遺產傳承問題研究》。[1]77-201第三類,促進裕固族教育發展的政策研究。如《裕固族基礎教育發展:成就與政策》《加快民族文化課程建設促進人口較少民族發展》。[1]204-214事實上,這些成果都是裕固族教育研究被確立為新興學術領域的奠基性學術成果。
五、結語:裕固族教育研究新興學術領域已具雛形
巴戰龍博士的著作《教育人類學視野中的裕固族教育研究》回答了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構建“何以需要”、“何以可能”和“何以實現”的邏輯質詢。從著作的體例設計來看,從該領域確定通過歷時研究和共時研究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裕固族教育學術史,并站位于宏觀、中觀和微觀三維視域下對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學術領域加以“循序漸進、步步深入”的構建。從內容特點來看,著作選擇教育人類學視角來審視裕固族教育并嘗試初步構建裕固族教育研究新興學術領域。從學術文化來看,著作做到了“傳統”與“現代”并重。從學術理念來看,著作秉持了“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理念。最后,從研究邏輯來看,著作嚴格遵循理論與實踐并重的雙重邏輯來呈現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的構建過程,進而立足于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開展相關研究。因此,該著作就是“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新興學術領域構建的標志性學術成果。
總體而言,著作以構建“開放社會科學”為基本的價值取向,在闡釋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對象與功能、性質與定位和學科基礎之上,提出了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并加以構建,然后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遵循“領域—歷史—主題—政策”的邏輯,撰寫了系列關照學校教育、社區教育和家庭教育三種形態下的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學術論文來作為本領域主題研究,最終為構建出裕固族教育研究奠定基礎。事實上,巴戰龍博士將“裕固族教育研究”作為一個“新興學術領域”加以構建,將為有效防止近年來裕固族教育研究“井噴式”的發展所出現一些研究深度不夠、水平不高、理論薄弱等問題的發生提供學術治理的一劑解藥,為裕固族教育的規范化、科學化、系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6]至于裕固族教育研究領域能否成為民族教育研究者持續關注的學術領域,不僅需要以巴戰龍博士為代表的裕固族本族學者持續努力,也需要更多具有較高學術素養和實踐關懷的兄弟民族研究者涉足這一尚處于初創階段的新興學術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