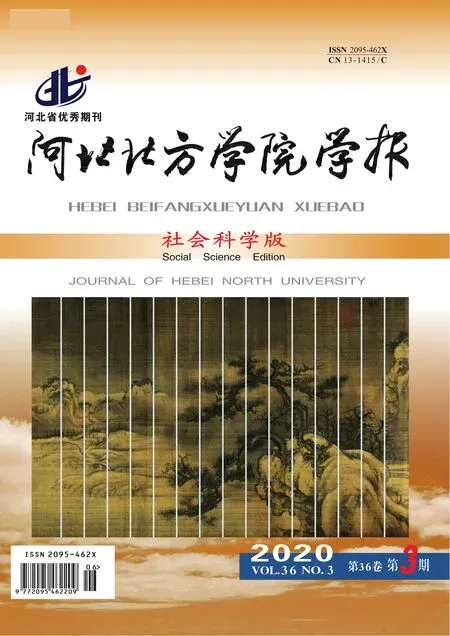青年群像佛系亞文化的認同危機研究
王 乙
(北京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44)
“佛系”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現象,蘊含鮮明時代特征,衍生出一系列如“佛系青年”“佛系父母”“佛系學習”及“佛系養生”等詞語,以輕松調侃的語氣和深入淺出的含義緊抓現代人內心喜好。英國學者默克羅比在《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一書中指出,青年群體中的亞文化現象是由工人階級中的部分青年代表創造,并在社會或同輩間引起廣泛輿論和傳播的某種文化現象。這種現象聚焦社會熱點問題,融合青年的成長探索經驗和對未來的想象力,展現和表達青年群體的共鳴與立場。它在本質上區別于傳統中產階級文化,甚至與前代人年輕時社會流傳的文化現象存在實質性差別[1]。青年佛系亞文化是當今社會眾多亞文化現象的一種,它由青年創造和豐富,展現當代青年對社會生活狀態的真實面貌和對社會問題的客觀認識,受到社會大眾傳媒和輿論的傳播與評論。
一、青年群像佛系亞文化的形態特征
2017年,互聯網上出現大量以“90后”和“佛系”為關鍵詞的話題文章,吸引大眾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這些文章包裹著當下普遍彌漫的社會焦慮和浮躁,形象生動地道明了當代青年的無奈現狀和尷尬困境,與社會期望的“陽光積極”與“健康向上”的青年群體精神面貌形成鮮明對比。
(一)理性與隨性并存的矛盾情緒
佛系文化之所以能夠引起青年的廣泛熱議,是因為這種文化現象迎合了部分青年獵奇的心理特點。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現高度契合了當前相當一部分青年的心理狀態和現實情況。透過“隨性”和“任性”的標簽反映出部分青年對當前社會發展存在問題的思考,同時折射出青年對自身發展的理性評判和對未來的美好期望。首先,“佛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面對選擇不急于作出回答,而是先審視自我,進行理性思考和選擇。其次,佛系文化折射出一種“隨性”和“放下”的生活方式,緩解了社會壓力爆炸式增長所帶來的獨屬于當代青年人的焦慮。他們用“佛系”標簽解決諸多無意義的爭端與矛盾,并攜著一份更好的心情面對生活,形成更加積極向上的人格。最后,在這個愈發突出團隊合作的時代,每個人性格中的包容與理解在團隊磨合中便顯得尤為重要。當代青年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其性格相對欠缺包容,而“佛系”標簽帶給當代青年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在其人格形成過程中放棄無謂爭執,從而更加順應時代發展方向。
(二)進取與焦慮共生的心理狀態
隨著大數據時代到來,社會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社會成員的焦慮感和迷茫感愈加強烈。“忙忙碌碌,看不到未來”“身體變差”“發際線后移”“容易崩潰”“莫名想哭”及“缺乏歸屬感”成為人們共同的感嘆。首先,青年正處于人生事業選擇的關鍵時期,個人理想的實現承載著國家、社會和家庭等多方期望,巨大的壓力使青年倍感壓抑。在社會現實選擇面前,學業焦慮、擇業焦慮、感情焦慮、健康焦慮和生存焦慮相互交織,令青年疲于應付。在這種情況下,擺脫焦慮和煩惱、追求平淡生活及關注內心真實感受似乎成為青年合情合理的訴求。其次,從本質上來講,佛系亞文化與前幾年盛行的“屌絲文化”類似,是青年群體自嘲與調侃的表達方式在自媒體時代的再一次呈現[2]。焦慮是社會大環境的產物,也是困擾所有人的共同病癥,只不過在“佛系亞文化”下被青年群體無限放大了。最后,青年群體的自嘲口吻與實際追求呈現反向狀態:越是看淡一切,越是看不淡一切;越是不爭不搶,越是錙銖必較;越是頹廢無力,越是暗地較勁。佛系文化的背后是青年渴望進取奮斗的價值追求和焦慮困惑的現實束縛間的矛盾映射。
(三)務實與逃避交織的價值取向
當代青年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浪潮逐漸成長。城市中長大的“90后”沒有經歷過經濟匱乏時期,對于物質的獲得與失去并不像前代人那樣敏感。他們渴望以自我奮斗方式打破社會對他們傳統刻板的定義,重視和追求內心真實的體驗。首先,佛系文化的存在建立在佛系青年對自身條件和社會認知的基礎上。佛系文化不僅是“90后”心理的真實寫照,也是社會問題的縮影。由于現代生活節奏加快,人們渴望逃離現代社會快節奏的壓力和普遍的功利風氣,希望尋找一種可以讓精神和身體放松的生活方式。其次,當青年真正走出象牙塔進入社會,經歷的是現實生活的四處碰壁。一時間他們感到奮斗無望,人生前途渺茫,從而想做一個無欲無求的人。實際上,“佛系”是應對快節奏浮躁風氣的一種反抗行為。他們讓自己慢下來去體會內心真實的需求,客觀考慮自身現實情況,適當降低物質要求,回歸生命本真,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二、青年佛系亞文化群像的認同危機
身份是個體的人在社交網絡中的位置,體現了人與其他個體或群體之間的組織交往形態。認同打通了主體與客體之間聯系和轉化的雙向通道,表現為從“我”到“我們”的認知過程,“認同的過程強調共同認識,弱化兩者間的差異,是主體的了解、接受和贊同的漸進過程”[3]。認同是個體對自己所屬群體的自我認知的確認,是伴隨著深入的情感體驗和行為模式發展的心理過程[4],是個人與社會互動的結果。當代青年群像佛系亞文化認同危機主要分為以下幾點。
(一)“認同”要素復雜多樣
身份的認同在個體和社會環境的互動過程中逐步完成。首先,認同的前提來自于個體對自身生理和心理狀態的直覺感知;其次,認同對象要具有高度解釋效力。如果一個概念不能有效建立與個體認知和經驗間的聯系,“認同”關系就難以產生。對個人而言,“我是誰”是一個關鍵命題,它直接決定個體的社會地位,同時決定個體與社會的對應關系。“如果缺乏周圍環境和人的參照,我們得到客觀描述的可能性將會十分渺茫。”為進一步定位“我是誰”,就需要基于周圍環境、社會空間和人際交往等不同外部關系得到全面客觀的認識及反饋。人的自我認知的實現需要在多重參照的基礎上完成,而文化認同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才有可能實現。當今,中國社會發展受到地理分布和經濟條件等多方因素影響,這也加速了青年群體內部分化現象。由于貧富分化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因素,與城市青年相比,農村青年的文化體驗和綜合視野相對貧乏。農村青年群體所面臨的發展形勢也愈發復雜和現實。現代與傳統、先進與落后、物質與精神以及新事物與舊事物的對立沖擊雖然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但也在無形中加大了他們獲得文化認同的難度。這種差異間接折射出當代青年群體的分層現象,所謂“佛系”生活正是在現實生活中農村青年等弱勢群體構筑的一種話語體系,他們以此得到歸宿感和身份認同。他們降低對事物的期待感,尋找借口麻木自我,愚化內心,在假笑的背后是空洞和無處安放的靈魂。
(二)“認同”問題層出不窮
認同,通常又被翻譯成“同一性”或“身份”。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自我認同危機是指“個體無法對自身行為形成積極評價”或“個體意識不能形成連貫、完整的自我概念”的現象[5]。由于外界環境的諸多不確定性,容易造成個體的焦慮和恐慌情緒蔓延。
隨著社會進步,多元的文化現象不斷充實和刷新著個體的認知,年輕一代文化觀和歷史觀呈現斷裂狀態。部分青年逐漸遠離主流文化,“自以為是”地脫離傳統道德環境,將自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混入主流價值體系,借此宣泄消極情緒,吸引他人注意力。這種行為令作為亞文化主體的青年一代不再認可父輩的價值觀和文化,不再依賴父母替他們選擇的“平坦大道”。可現實社會卻無法給予他們認同和共鳴,由此產生并激發出種種“代際沖突”。社會輿論對佛系文化評價各異,有人強烈抨擊,認為年輕人喪失奮斗動力甚至逃避奮斗,本質上是一種萎靡的文化現象;有人表示支持,認為新時代的青年對社會發展有深入理解和思考,只是每一代青年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特點,應包容青年種類豐富的訴求,尊重每個青年的選擇;有人表示中立,認為不必過分強調佛系的積極和消極影響,但適當調侃自嘲也無不可。社會對青年佛系文化的評判褒貶不一,青年在被否定的過程中充滿了迷惘和痛苦。
(三)“認同”身份模糊不清
英國社會學大師齊格蒙特·鮑曼認為,“進入流動的現代性階段,社會成員個體化是無法避免的終極命運。個體認知是逐漸脫離社會和他人標準和期望,走向個體獨立的過程”[6]。個體身份模糊不清帶來的困惑具體體現在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與人的疏離。由于閱歷和思維視角差異,人與人的關系看似緊密熱絡,實際上泛泛之交居多,進而導致個人越來越收緊自己的小圈子,個體間的信任關系不再穩固。另一方面,個人與社會的分離。首先,個人與社會的分離體現在個人與社會之間溝通渠道的堵塞,公共空間淪為暴露隱私的天地,各種八卦信息和負面新聞侵占社會公共資源,個體與社會溝通的積極作用逐漸減弱。其次,個體更加注重自身利益,而對社會事物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下降,導致社會共同利益和集體利益受損。此外,客觀存在的未知風險增加了人類交往和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加速了個體與個體以及個體與社會間的分離。個體失去了社會坐標的支點,對身份“認同”的追求更加模糊不清。
三、青年佛系亞文化群像認同危機的應對策略
青年佛系亞文化是互聯網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不能忽視其對年輕人價值觀的影響。培養青年健康的社會心態,必須從社會現實和青年群體的實際問題出發,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需,創造和凈化適合青年成長的客觀環境。
(一)重視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要場合都強調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青年工作不僅是日常工作,而且是與黨和國家事業有關的政治工作。要傾聽青年心聲,把握青年脈搏,采用青年喜聞樂見的方式開展青年工作。第一,注重青年身心健康的訴求。身心健康發展是青年成長成才的基礎和前提。只有充分保障青年身心健康,才能為他們的美好生活和事業前途打下堅實基礎。近年,青年心理健康問題頻發,焦慮、抑郁和失眠等成為阻礙青年健康發展的公共衛生問題,應重視青年心理咨詢與治療體系建設,加強對青年的心理疏導。第二,關注青年個人成長需求。應維護青年權益、改善青年福祉和擴大青年發展空間,加深其社會治理參與程度,完善相關法律、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政策。第三,注重青年事業發展的訴求。推進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事業穩步發展,必須將青年的事業擺在首要位置[7]。事業不僅是青年的人生追求,也是社會發展動力。政府、高校、企業和社會各方面力量應為青年提供支持,幫助他們擴大職業發展空間,打通社會上升通道。
(二)凈化青年成長的社會環境
目前,中國正處于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8]。社會轉型帶來的諸多問題使年輕人越來越焦慮,這也是“佛系”文化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社會上積聚的消極情緒壓倒積極情緒,就可能對年輕人的價值觀產生巨大沖擊,甚至被某些“別有用心”者蒙蔽和利用,激發煽動社會不滿情緒,進而演變成一系列惡性事件。在實踐基礎上,人和環境既相互影響又相互制約。正如馬克思提到,人在發展過程中創造了環境,相反,環境也造就了人的發展[9]。人能夠改造周圍環境,同時優美的環境可以影響和改變人,啟發人類更好地生活。青年處于人生關鍵期,他們的思想尚未成熟,價值判斷容易受到外界干擾。因此,有必要從源頭上凈化他們成長成才的社會環境,大力掃除文化垃圾,塑造健康的社會心態。一是要積極弘揚和宣傳社會正能量,發揚榜樣標桿和示范性作用。梳理和總結好榜樣的先進事跡,通過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和用心用情宣講,令青年向榜樣學習,將榜樣精神發揚光大。二是要加強國家和法律層面的有效監管,營造風清氣正適合青年人健康成長的社會生態環境。堅決抵制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對青年理想信念的侵蝕,打擊功利風氣,杜絕“唯成績論”和“唯績效論”,加強對青年人成長和就業的引導鼓勵,鼓勵青年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三)強化網絡空間的輿論治理
媒體在“佛系”文化的普及中起著重要作用。宣傳具有形式多樣、內容多元、速度快、互動性強、自發性強和成本低等特點。要在新時代的網絡陣地上占領新高地,應加緊建立并完善媒體管理制度,優化傳播內容信息的審核發布流程,防止不良信息傳播,引導正確的傳播理念,營造綠色和諧的互聯網傳播生態。近年,新媒體已成為文化傳播的主要載體,在輿論引導中發揮重要作用。當前,存在部分網絡短視頻平臺主體責任缺失和內容低級庸俗問題,甚至出現違法違規現象。進一步規范網絡媒體管理,引導和激勵網絡媒體自覺傳播正能量,放大正面效應十分必要。首先,新媒體應發揮自身優勢,堅守法律紅線和道德底線。網絡產品和信息傳播平臺要秉持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尊重事實,客觀理性,充滿正能量,不以低俗內容吸引眼球,不以片面推理掩蓋客觀真相,對“佛系”文化進行合理引導,挖掘文化現象背后的深層意味,幫助青年盡早走出焦慮和困惑。其次,新媒體必須堅持積極正面輿論導向,作好精準定位。媒體運營者要不忘初心,努力生產和創作出更好的內容,履行媒體人傳播社會正能量的責任,扎根特定領域,積極弘揚主流文化精神。
青年群像佛系亞文化認同危機源于社會發展和青年群體的認知觀念變化,是通過網絡媒體等渠道帶動產生的一種新語言方式和文化實踐。青年群像佛系亞文化認同危機需要跨越要素多樣、問題復雜和身份模糊等3類突出矛盾,從關注青年訴求、治理社會環境和強化網絡綜合治理建設3方面入手,幫助青年勇敢走出困惑,培育其健康積極的精神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