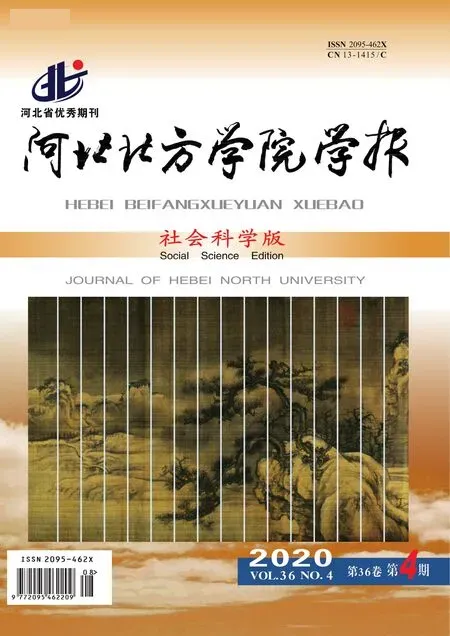順應論視域下《離騷》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研究
盧 欣,岳 峰
(1.福州工商學院 文法學院,福建 福州 350700;2.福建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離騷》是《楚辭》的開篇之作,是詩歌史上浪漫主義的奠基之作。《楚辭》在國外的譯介始于1852年,截至2017年,《楚辭》約有40個英譯本(含節譯本和全譯本)。20世紀以來,國內學者開始對《離騷》譯本進行多維研究,但在知網平臺就“離騷&翻譯/英譯”進行精確檢索只得到37篇文章(2000—2020年),發文量較少。可見,國內英譯研究發文量與國內外學者的譯介熱度不相符。從發文主題來看,《離騷》英譯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分析選詞技巧與翻譯策略,其中還包括譯者主體性和英譯質量等;二是剖析語言和語體,如副文本、注釋、隱喻、“兮/將”等詞、意象與文化負載詞;三是探究文化傳播與文學風格,如風格重構、美學特征、文學特質及文化走出去等。此外,在Web of Science檢索“Lisao/Li-sao”一詞,可得9條相關搜索結果,其中國外學者6篇,研究方向包括解析《離騷》譯本注釋、評述專著《離騷新解》、探討敘事風格和抒情主體等。
從國內外研究來看,《離騷》的譯本探討和學術研究還存在不足,有一定局限性,主要原因是其翻譯難度高、閱讀障礙廣以及研究難點多。下文以順應理論為基礎,選取《離騷》4個英譯本為語料,對詩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進行比較分析,主要探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何作出順應性語言選擇,采用何種翻譯原則與方法實現文化負載詞的語言和文化內涵的最優傳遞。
一、順應論在《離騷》英譯中的應用
比利時語言學家杰夫·維索爾倫首創了語言順應論,從全新的視角來闡釋語用學,提出語言的使用是選擇且與語境相互順應的動態過程,并進一步指出應從“綜觀”的視角來看待語言的使用[1]139。《離騷》既具有獨特的語言風格,又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譯者勢必以“綜觀”的角度推動語言和文化的順應,才能達到文學跨語言傳播和交流的效果。
(一)《離騷》英譯本簡介
《離騷》的英譯始于1879年,彼時英國漢學家莊延齡在英文雜志《中國評論》上發表“The Sadness of Seperation or Li Sao”一文。而后,國外一眾漢學家陸續發表了《離騷》的部分譯本或全譯本,代表譯本有理雅各版(1895)、霍克斯版(1959)(下稱霍譯)、宇文所安版(1996)、戴維·亨頓版(2008)和夏克胡版(2012)[2]。國內第一個譯本誕生于1929年,作者是華裔學者林文慶,其它著名譯本主要有楊憲益、戴乃迭版(1953)(下稱楊譯),許淵沖版(1988)(下稱許譯),孫大雨版(1996)和卓振英版(2006)(下稱卓譯)。
(二)順應理論與《離騷》翻譯難點的融合
1990年,中國學者錢冠連率先引入順應論。1999年,何自然和于國棟系統地介紹了順應論的內容和理論框架。2001年,陳喜華和戈玲玲首次用順應論來指導翻譯實踐,前者提出如何在翻譯中進行語言語境和交際語境的順應,后者分析語境關系順應對詞義選擇的制約[3]83。順應論認為,語言的使用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為達到不同的交際意圖,語言使用者需要根據語境選擇恰當的語言手段。
就翻譯而言,譯文的語言選擇是對原語語境和語言結構作出動態順應的過程[3]82-83。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典籍翻譯兼具跨語言和跨文化性,受到文本內外雙重因素的制約,語言順應性對典籍翻譯的過程具有很強的闡釋力[4]。除去《離騷》別具一格的語言特色,作者在詩中還融入大量的文化意象、歷史和神話故事等來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與愛國情懷。如何將語言形式和文化內涵、客觀意象和主觀情感準確地傳遞給譯入語讀者是全詩翻譯的難點。介于此,譯者可在順應論原則的指導下整合語言結構和語境,選擇并重構譯文語言。
二、《離騷》英譯原則
順應論為語言現象的語用描述和語用解釋提供了4個研究角度:語境關系順應、結構客體順應、順應的動態性以及順應過程的意識突顯程度[3]82。鑒于《離騷》獨特的語言風格和文化概念,譯者可遵循以下3個原則進行目的語的重構,即動態順應原文語言結構和語言語境、交際語境以及文化語境。
(一)順應原文的語言結構和語言語境
語言結構的順應是指譯者根據不同類型的語碼、語體和語段對譯文語言結構進行選擇調整,包括語音結構、詞素與詞匯、分句以及超句等。語言語境包括片內銜接、篇際制約和線性序列3個方面[5]。此外,譯者應仔細考究詞匯本身的含義,把握詞匯的語法和語境含義,在詞匯、結構和修辭等層面作出恰當的選擇和順應。
《離騷》的語句以七言為主,譯者必須順應詩歌的語言特點和語音習慣,并考慮上下文的銜接,適當調整詞序和語序,讓譯文最大程度地被譯語讀者所接受。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句,許淵沖將上句譯作“My way ahead’s a long,long one,oh! I’ll seek my beauty high and low”[6]38,其中“one”和“low”與上句“sun”和“go”構成“abab”的押韻模式;卓振英譯作“Long,long is the way,but nothing will my effort arrest;Up hill and down dale for the beauty I will quest”[7]18,其中“arrest”和“quest”與下句“thirst”和“burst”構成“aabb”的韻腳模式。此外,本詩多用語氣助詞“兮”字表明中頓,許淵沖忠實于原語語言結構,將其譯作“oh”,呈現出原文獨特的語言結構和風格。而其他譯者均未將“兮”譯出。
《離騷》中共出現18種香草意象詞,后世借此得以了解先秦楚國時期香的運用與發展。以“掔木根以結茝兮”為例,“茝”指“白芷”,古書上說是一種香草。許淵沖將其譯作“clover”(三葉草,苜蓿)[6]32;卓振英選用霍譯“valerian(纈草)[7]9”的變體詞“Valeria White[7]15”,從香味和形態而言,“Valerian”一詞相似度更高一些。再如“薜荔”一詞,卓振英譯作“Wisteria”,與前文語境保持一致,就是綜合考慮了雙語語境和讀者的接受能力。
(二)順應交際語境
順應交際語境指的是譯者應順應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注重譯文的言語行為規范和交際者的認知等[1]138。《離騷》中,作者廣泛運用了象征手法,引類譬喻,托物言志。此外,作者還大量運用古代神話和傳說,以神喻事,借典明理。譯者在處理時應有“綜觀”意識,除了語言語境外,應充分考慮譯入語讀者的社會環境、認知和接受能力等。
《離騷》中共出現28位歷史或神話人物,有夏禹、商湯、武文王、唐堯和虞舜等明君,也有夏桀和殷紂等暴君;有夏啟與寒浞等驕奢淫逸和不修政事的君王,亦有彭咸、伊尹、皋陶、傅說和呂望等良相賢臣;還有宓妃和蹇修等神話人物。以“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這一典故為例,許淵沖和楊憲益均將“說”和“武丁”譯作“a convict”[7]43和“his sovereign”[8]26,霍克斯將其譯作“Yue laboured as a builder”和“Wu Ding”[9]55,卓振英譯為“King Wuding”和“Fu Yue,a tamper”[7]26。許譯和楊譯考慮譯入語讀者的接受能力,采用了意譯法;霍譯和卓譯則采用音譯法,忠實地呈現了原語文化。此外,卓譯本還增添了注解,完美地呈現了譯語的交際功能。
(三)順應文化語境
文化語境是語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譯文語言的重構勢必要順應文化語境。《離騷》英譯也只有動態地順應不同的文化語境,才能盡可能地傳遞原語的傳統文化內涵,實現翻譯在譯入語中的語用等值,喚起譯入語讀者與原語讀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動態順應提倡譯者在特定時代的文化語境下順應不同的翻譯目的作出動態選擇,以動態的觀點研究翻譯過程中語境和結構的相互順應過程[10]。
以“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為例,禮記有云“幼名,冠字……”,意為“幼時取名,弱冠之年取字”,這一傳統習俗與現代不同。屈原,名平,字原,“正則”和“靈均”是對“平”和“原”二字的引申,含義分別是“正直、正派”和“聰穎、公平”。由于詩體限制和文化差異,譯者無法在譯入語中完全闡釋這一文化內涵。對此,許淵沖選用“my formal name was…I was also called…”[6]29這一結構來向譯入語讀者簡要介紹這一傳統習俗,卓譯“My personal name…,the other name…”[7]2結構與許譯相近,楊譯“Denoting that in me…”[8]7則是直接陳述名字內涵。此外,許淵沖動態地選用“Divine Right”和“Divine Flame”來解釋“正則”和“靈均”兩詞,一是和上句“bright”和“name”相呼應,二是傳遞“剛正不阿”和“熱情洋溢”之意,雖與原文略有出入,但卻是考慮到譯入語讀者認知、平衡交際語境和文化語境之佳作。
基于此,典籍英譯,尤其是詩歌英譯,可采用順應論翻譯原則來進行詞匯和語篇的處理。具體而言,譯文語言需基于原文語言結構、語言語境、交際語境和文化語境作出動態順應。下文從《離騷》中的文化負載詞出發,探析順應論原則在英譯過程中的具體運用。
三、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
美國翻譯家尤金·奈達將文化負載詞分為生態學、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宗教文化及語言文化負載詞[11]。在《離騷》一文中,負載詞出現的頻率依次為生態文化、物質文化、語言文化、宗教文化和社會文化。魏曉紅將語言翻譯中的文化語境分為表層文化語境和深層文化語境,前者體現文化共性,是物質文化的一部分;后者體現不同文化的個性,是精神文化的組成部分。譯者需要順應文化差異才能實現成功的交際[12]。介于此,下文試將生態文化和物質文化負載詞歸類為表層文化語境詞匯,將宗教文化和語言文化負載詞歸類為深層文化語境詞匯,并引用順應論探討其翻譯方法。
(一)表層文化語境詞匯
因為該類詞匯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原語和譯語在語言和文化上可能實現等值,譯者大多順應語言語境和交際語境,采用直譯法、音譯加注法和意譯法。
1.物質文化負載詞
《離騷》中不乏對楚地生活的描寫,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詩中與飲食、服飾、音樂、習俗和交通工具有關的詞匯都歸為此類。如“椒糈”一詞指的是以椒香拌精米制成的祭神的食物,3位譯者分別譯為“peppered rice[6]43(許譯)、Ash Flowers and ground fine rice[7]24(卓譯)和spiced rice[8]29(楊譯)”,許淵沖的直譯法既順應了語言結構和交際功能,也可以被譯入語讀者所理解和接受。又如“恐皇輿之敗績”中“皇輿”一詞指的是“皇家的馬車”,許淵沖和霍克斯采用直譯法,譯作“royal cab”[6]31和“chariot of my lord”[9]51;卓振英和楊憲益則采用意譯法,取其引申義,譯為“the Sovereign”[7]4和“my sovereign's sceptre”[8]9。筆者認為,直譯法既可以傳遞本味,也可以讓譯語讀者靠近原文,而霍譯“chariot”一詞相較許譯本“cab”則更添一分古味。
2.生態文化負載詞
生態文化負載詞指與生態文明相關的地形地貌、動植物物種和資源能源等,此處主要介紹《離騷》中最常見的兩類意象:地理類和植物類。
詩中大量的傳說和虛幻地名是翻譯的一大難點,如“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中的“蒼梧”和“縣圃”分別指古代區名和傳說地名。“蒼梧”約指湖南九嶷山以南區域,但考證不明,許淵沖意譯為“E’regreen State”[6]38,既傳遞出這是地理類專有名詞,又取“蒼”之韻味;卓振英直接音譯為“Cangwu”[7]16。“縣圃”,即“懸圃”,是傳說中的神仙居所,位于昆侖山頂,許淵沖譯為“the mountain’s crest”[6]38,卓振英譯為“the Garden of Xuanpu”[7]16。從譯語讀者的接受能力來看,許譯略勝一籌。卓振英對于地理類詞匯大多采用音譯法或音譯加注法,兼顧了文化和語言信息點,如“沅、湘”譯作“the Yuan and Xiang Rivers[7]15”,“咸池”譯作Pond Xianchi,the sun’s bath[7]19。但筆者認為一些虛擬的地名無需一一對應,否則會給譯入語讀者增添閱讀障礙。
《離騷》中“花草樹木”等意象累計有30余種,常見的“蘭和蕙”的出現頻率更是高達10余次,更有一些當下已經無法考證的僅存于古書中的香草詞匯。屈原選用“杜蘅、留夷、揭車”等香草意象和“菌桂”等香木意象來寓意“高潔、正直”;用“蕭艾、茅菉葹”等惡草代指“卑污、低俗”。如“江離和辟芷”均是香草名,分別被譯作“sweet grass by riverside”[6]29(許譯)、“Selinea and Angelica”[7]2(卓譯)和“Angelic herbs and sweet selineas”[8]4(楊譯)。其中,許淵沖采用釋義法來翻譯植物類詞匯,順應譯入語讀者的認知結構;卓振英和楊憲益則采用借譯法,讓譯語讀者在頭腦中形成類似的植物意象,但讀者認知能力存在差異,且英譯本中的植物意象與原文意象存在差異。又如,“扶桑”是古代傳說中的神樹,許譯為“a giant tree”[6]39,卓譯為“Fusang”[7]18,楊譯為“the brake”[8]25。若僅音譯為“Fusang”而不添加注釋,則容易使譯語讀者產生閱讀障礙。許淵沖的釋義法雖忽視了原語文化,但充分考慮到交際語境和讀者的接受能力。
(二)深層文化語境詞匯
該類詞匯體現文化的差異性,譯者應綜合考慮文本內和文本外因素,順應交際和文化語境,盡可能地引介原語文化。因此,在處理宗教文化詞和語言文化負載詞時,譯者大多采用意譯法、創譯法和增譯法。
1.宗教文化負載詞
楚地巫風盛行,《離騷》中有大量與意識、信仰、神話、佛教和巫文化有關的文化詞匯,它們展示了楚地的宗教文化個性,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有很大差異。
以“指九天以為正兮”中的“九天”為例,“九”是最大的數字,故“九天”指“天之極高處”。許淵沖將其增譯為“Ninth Heaven high”[6]31極為妥當;霍譯為“ninefold heaven”[9]62,給讀者“九重天”之感;卓譯為“providence(上天;天佑)”[7]6,容易使譯語讀者聯想到“God”;而楊憲益選用“celestial spheres(天界)”[8]9這一短語,也與原語內涵有出入。又如,“巫咸”為古代傳說人名,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許淵沖采用意譯法將其譯作“the wizard”[6]43;楊憲益將其譯作“the wizard great”[8]21;卓振英則采用音譯加注法譯為“Wu Xian the Diviner Great”[7]24。從詩歌意境和語言結構來講,許譯更佳。可見,譯者為順應交際和文化語境而綜合采用增譯、意譯或直譯等翻譯方法,以傳遞中國特色文化內涵。
2.語言文化負載詞
《離騷》中除了大量的楚地風俗文化詞匯以外,還有許多頗具中國特色的古語詞匯。
以“庚寅”為例,它是中國干支紀法中計算年份的一種說法,在古代頗為流行,但因漢語語言和文化的特殊性,故無法完全向西方讀者介紹這一信息。基于西方讀者對十二生肖有一定的認知度,“寅”又對應十二生肖中的“虎”,許淵沖順應譯語讀者的認知能力,將其簡譯作“Tiger’s Day”[6]29。霍克斯和卓振英主張保留譯語文化,采用音譯法,將其譯作“the day keng yin[9]39和“the day of gengyin”[7]2,但未加注釋,容易造成讀者的閱讀障礙。又如,“蛾眉”一詞原指像蠶蛾的觸須一樣好看的眉毛,后代指姣好的容貌和美女。許淵沖結合上下文語境,將其創譯作“my beauty”[7]34,方便讀者理解和接受,霍譯“my delicate beauty”[9]47亦是如此;卓譯和楊譯采用“brow”[7]8和“eyebrow”[8]10來翻譯該詞,與原語內涵相悖,亦不符合西方讀者的審美方式和理解能力。
典籍英譯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徑,肩負著重大的使命。《離騷》中極富特色的語言風格和文化內涵要求譯者進行動態順應,盡可能地傳達中國傳統文化內涵。順應理論尚在發展和完善過程中,但語用學與翻譯學的結合勢必對文學作品英譯起著很強的指導意義。表層文化語境詞匯具有文化共性,如物質和生態文化負載詞可以在譯入語文化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達,譯者可以使用直譯法、音譯加注法和意譯法來處理;相反,深層文化語境詞匯具有文化個性,如宗教和語言文化負載詞很難在譯入語文化中找到相似的表達,建議采用意譯法、創譯法和注釋法。綜上,作為“文化使者”,譯者應動態地順應語言結構、語言語境、交際語境和文化語境,綜合使用各種翻譯方法,以最大限度地傳遞《離騷》中的華麗語言、詩體結構、文化意蘊和詩人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