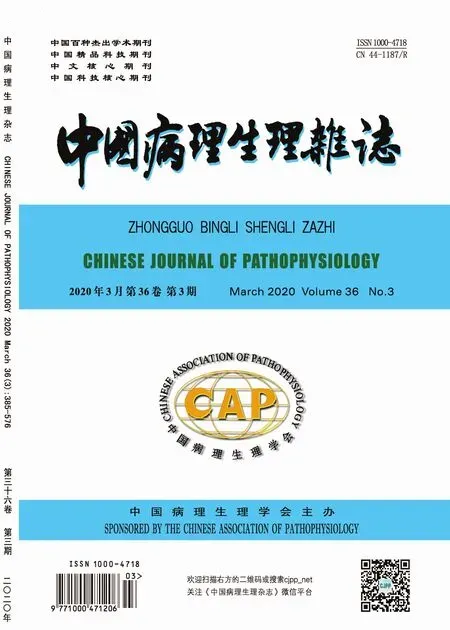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心肌損傷的病理生理機制探討
陳韻岱, 李玉珍, 劉秀華, 周 浩
(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心血管內科, 2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院研究生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 北京 100853)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自2019年12月爆發流行以來,截至2020年3月9日,已迅速蔓延至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99個國家和地區。全球累計確診111 044例,累計死亡3 876例[1],成為了全球性的公眾健康威脅。肺組織是新型冠狀病毒的主要攻擊靶器官,常見的臨床癥狀為發熱、干咳、乏力;少數伴有鼻塞、流涕、咽痛等。近期研究發現,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的患者中,16.7%的患者合并心律失常,7.2%的病人出現急性心肌損傷,而10.5%的患者最終死于心血管疾病[2]。因此,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的心肌損傷值得關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明確指出心肌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侵犯的重要臟器,表現為心肌細胞變性、壞死,心肌間質可見單核細胞、淋巴細胞和中性粒細胞浸潤,部分血管內皮脫落、內膜炎癥及血栓形成[3]。由于本病為新發傳染病,其誘發的心肌損傷尚缺乏深入的探討和基礎實驗數據支持,本文擬通過分析討論COVID-19相關心肌損傷的病理生理機制,為重癥患者心肌保護治療提供臨床參考。考慮到細胞因子風暴和血管緊張素轉換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表達失衡已經被眾多學者報道和分析[4-5],本文主要從新近心肌組織病理結果中的血管炎和低氧血癥2個方面進行探討。
1 血管炎
心臟收縮的能量物質和氧氣供應受到冠脈血流的調控。心肌是高耗氧器官,靜息狀態下冠脈血流中70%的氧氣被心肌攝取。因此,在心臟負荷加重、心肌收縮活動增強時,提高單位血液中心肌攝氧能力的潛力較小。此時,更多依靠冠脈及心肌微循環通過舒張血管、增加單位面積下的血流量來滿足心臟高負荷條件下對氧氣的需求[6]。調節冠狀動脈和心肌微循環舒張的主要方式為內皮依賴性的血管舒張活動:內皮通過自身特異性的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 NOS)將左旋精氨酸轉化生成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也被稱為內皮依賴性舒張因子)[7];隨后被平滑肌攝取并作用于鉀通道的開放,最終誘發血管平滑肌的舒張。不僅如此,單層內皮構成的心肌末梢微循環中,由于缺乏神經的分布,心肌組織代謝物質的交換更多依賴單個內皮細胞的舒張活動[8]。由此可知,內皮功能受損是冠脈血流儲備能力下降和舒張功能失衡的重要標志,而功能失調的冠脈及微血管舒張活動,將會限制心肌在高負荷條件下的血供,引發心肌缺血[7]。同時內皮細胞是血管的第一道屏障,可以感知血液中的各種應激條件的變化(例如缺氧、炎癥、高脂等),并通過自身旁分泌功能和形態學變化向心肌傳遞各種血液中的信息。例如受損的內皮可以通過表達細胞間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 ICAM1)來吸引炎癥細胞[9]。同時,受損的內皮表現為細胞通透性及細胞間屏障結構的破壞,由此加速炎癥細胞通過形變來穿透內皮層進入心肌組織中。因此,內皮功能異常可能是心肌炎癥的始動信號。最后,內皮細胞是天然的抗凝屏障,其細胞膜上含有肝素、前列腺素等精細調節局部抗凝活動的物質[10]。內皮脫落誘發的內膜下膠原暴露,是局部血栓形成的關鍵因素。綜上所述,冠脈及心肌微血管通過調節血流量來影響心肌能量供應,通過旁分泌和自身形變來擴大心肌炎癥反應,通過自身天然抗凝作用決定局部血栓風險的高低。
血管炎是指血管壁及血管周圍有炎癥細胞浸潤,并伴有纖維素沉積、膠原纖維變性、內皮細胞壞死等血管損傷。血管炎從廣義上分為原發性血管炎和繼發性血管炎。心臟幾乎是所有原發性血管炎的靶器官[11]。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3],心臟的病理活檢提示心肌血管表現為內皮脫落、內膜炎癥和血栓形成,說明SARS-CoV-2感染可能誘發內皮細胞功能下降甚至內皮細胞死亡脫落,同時伴隨著內皮及內皮下的炎癥細胞浸潤,以及機體較高的血栓風險。而上述變化,可以通過影響心肌的血液供應、誘導心肌炎癥反應以及增加冠脈血流負荷,導致患者出現急性心肌損傷。在治療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3]指出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療需給予循環支持。心肌微血管是決定心肌組織血液灌注量以及血液和心肌組織進行物質交換的基本結構和功能單位。由于微血管損傷發生在全身循環衰竭的早期,而心肌微血管障礙會更加隱蔽和難以捕捉,因此早期針對冠脈和心肌微血管的保護可能是減輕心肌損傷的重要策略。
ACE2是SARS-CoV-2的細胞內受體,該受體是SARS-CoV-2感染、入侵機體的關鍵分子[12]。它在肺、心臟和腎臟中高度表達,主要定位在這些器官的大動脈、小動脈和小靜脈內皮細胞上[13-14]。根據近期的尸檢結果以及臨床經驗,我們發現SARS-CoV-2主要受累器官為肺、心臟和腎臟。這3種不同臟器有相似的血管炎病理變化:肺組織內表現為單核、淋巴細胞浸潤以及血管內血栓形成;心肌血管表現為內皮脫落、內膜炎和血栓形成;腎臟表現為腎小球毛細血管網的蛋白質滲出和間質的微血栓形成。盡管目前血管中是否有SARS-CoV-2包涵體尚無確切報道,但是基于這3種器官都是血管豐富的組織且在內皮細胞均高度表達ACE2,我們推測SARS-CoV-2可能通過直接和間接作用誘發“泛血管炎”的病理生理變化。一方面,SARS-CoV-2通過攻擊血管(主要是內皮),導致內皮層的脫落和繼發血栓形成,破壞內皮依賴的組織血供,導致器官的能量代謝下降或中斷,引起血管炎癥從而擴大組織的炎癥反應。另一方面,SARS-CoV-2刺激全身炎癥因子風暴,炎癥因子通過啟動凋亡途徑,誘導內皮細胞損傷、死亡和脫落;同時,炎癥因子可以進一步激活內皮細胞,被激活的內皮細胞表達大量黏附分子,后者介導炎癥細胞黏附和侵入血管壁或血管周圍。上述泛血管炎的理論推測還需要在臨床實踐中和動物及細胞實驗中進一步證實和修正。
2 低氧血癥誘導的心肌損傷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3]中病理改變顯示:心肌細胞可見變性、壞死。SARS-CoV-2感染誘導的低氧血癥是引起心肌細胞變性壞死的重要病理生理學基礎。氧氣作為心肌的能源物質,被用來生成ATP供給心肌細胞的電生理收縮和舒張活動。氧氣含量的下降,首先表現為機體的ATP耗竭和能量物質的匱乏。心肌細胞為了滿足細胞代謝的需求,通過誘發線粒體自身分裂而在短時間內提高線粒體的數量,從而保障心肌細胞的氧化磷酸化。但是這種異常的線粒體分裂,將會誘發線粒體結構和功能的失衡[15-16],表現為線粒體基因組的不穩定、線粒體膜電位的降低及線粒體依賴的細胞凋亡途徑激活,從而導致心肌細胞死亡。不僅如此,難以糾正的低氧血癥,將會造成心肌細胞的酸中毒和氧化應激。由于長期的氧含量下降,線粒體有氧糖代謝被阻礙而無氧糖酵解過程將會被加強[17],由此造成了葡萄糖不完全分解并產生大量的乳酸,誘發胞質酸化。同時,由于有氧糖酵解的失衡,還原氫等抗氧化物質無法得到及時的彌補和再循環,由此造成心肌的氧化應激損傷[18]。過度的氧化應激、胞內酸中毒,共同作用于細胞內源性凋亡通路,由此誘發心肌細胞死亡。同時,新型冠狀病毒誘導的細胞因子風暴也可以通過提高腫瘤壞死因子α的含量,激活外源性凋亡通路,進一步加重心肌細胞的死亡。上述病理生理學過程可以解釋COVID-19患者病理結果中心肌細胞變性壞死的改變。
在臨床證據上,COVID-19患者中有16.7%出現心律失常[19],表現為早搏,提示SARS-CoV-2感染可提高心肌的自律性和興奮性[20]。相較于其他非收縮細胞,心肌細胞膜可通過細胞膜的去極化而誘發細胞膜上離子通道通透性的改變,隨后促進心肌細胞內外鈣離子、鈉離子的快速流動和交換,引發單個心肌細胞的收縮,并通過細胞間連接將這種興奮收縮進行傳導,最終誘發心肌的整體收縮。由于低氧造成的ATP不足,心肌細胞膜的鈉鉀泵無法正常工作,使得心肌膜電位輕度去極化,由此造成心肌細胞興奮性的上升和自律性的提高,但傳導性卻相對下降,這種病理生理學變化將會提高心肌細胞電生理異常的風險。除此之外,心肌細胞收縮和舒張過程,本質上是肌漿網介導的胞漿鈣離子振蕩。盡管鈣離子從肌漿網向胞質中釋放是一個順濃度梯度擴散過程,但舒張期鈣離子的回收卻是逆濃度梯度,極度依賴胞內ATP水平[21]。由此,低氧介導的能量匱乏,將會顯著干擾心肌細胞的舒張功能,造成心肌順應性的下降,影響靜脈血的回流。最后,為了應對低氧血癥,機體交感神經的異常興奮將會提高心肌電生理紊亂的風險[22],交感遞質的大量釋放也會加重心肌的氧耗和負荷。綜上所述,無法糾正的低氧血癥,會通過一系列心肌細胞內病理生理學反應,導致交感興奮介導的心肌氧耗和負荷加重、心肌收縮舒張功能失調、心肌電生理紊亂,以及部分心肌的壞死。
3 總結
盡管新型冠狀病毒的靶器官是肺組織,但是急性心肌損傷以及心血管死亡率卻是現階段治療中未解的難題。眾多學者提出ACE2介導的病毒直接攻擊心肌以及細胞因子風暴可能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多臟器損傷的潛在機制。本文依托近期的尸體解剖證據,從心臟冠脈血管炎及低氧血癥誘導心肌損傷的角度剖析了臨床上可能忽視的病理生理學改變,闡述了COVID-19相關的心肌損傷機制,希望為臨床治療提供潛在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