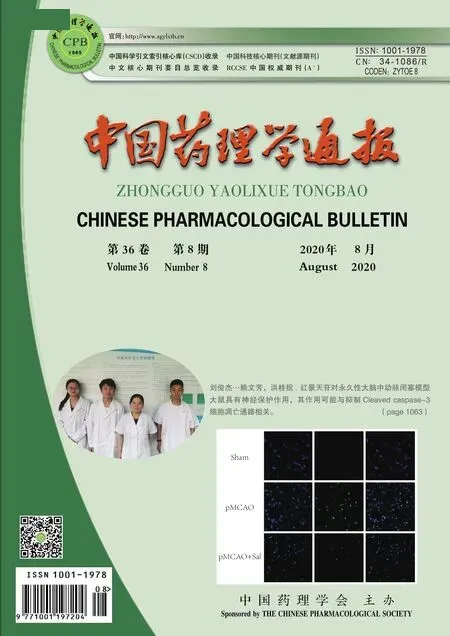肺動脈高壓動物模型研究進展
孫姝嬋,方蓮花,杜冠華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藥物研究所,北京市藥物靶點研究與新藥篩選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50)
肺動脈高壓(pulmonary hypertension,PH)是指肺動脈壓力異常升高的一種血流動力學和病理生理狀態。按臨床、治療和病理生理學特點,肺動脈高壓分為5類:動脈型PH、左心疾病導致的PH、肺病和/或缺氧導致的PH、肺動脈阻塞導致的PH、未知因素導致的PH[1]。盡管不同亞類PH的病因不同,但都表現出相似的病理變化,包括肺血管內側肥大、內膜增生和纖維化、外膜增厚伴隨中度血管周圍炎癥細胞浸潤、叢狀擴張性病變以及原位血栓形成,肺血管不斷增生、重構使血管部分閉塞,肺血管阻力增加,導致進行性右心衰竭和功能衰退,甚至死亡[2]。
REVEAL注冊研究的數據顯示,肺動脈高壓新診斷患者生存率為61.2%[3],PH可以是特發性也可以繼發于各種病癥,有證據表明,PH使各種常見疾病復雜化[1],因此迫切需要探究PH的發病機制和治療策略。動物模型是實驗研究的重要媒介,但目前PH動物模型仍不能全面模擬人體的發病特點,發病機制尚未明確界定,各種造模方法仍需優化和改進。本文對近年來國內外PH動物疾病模型制備方法進行總結,介紹不同模型的原理及制備方法,分析其優缺點以及對臨床PH的模擬性。
1 野百合堿誘導模型
野百合堿(monocrotaline,MCT)是從野百合種子中提取的一種吡咯烷生物堿,它能夠引起肝毒性和肺動脈高壓。
MCT引起PH的機制在于其被肝臟的混合功能氧化酶轉化為野百合吡咯,野百合吡咯可以在肺血管內皮細胞中形成DNA和蛋白加合物,從而導致細胞周期停滯,使內皮細胞凋亡,血管內膜剝脫,從而引起肺動脈平滑肌細胞進行性增殖和肺血管重塑[4]。MCT模型的特征在于內皮細胞凋亡和血管周圍炎癥,這與人肺動脈高壓發病的生理病理機制類似。MCT模型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了解肺血管重塑的過程以及炎癥反應在其發病機制的重要作用。大鼠是目前MCT模型的首選物種。
MCT模型主要經頸背部或腹部單次皮下注射1%MCT溶液,極少數采用腹腔注射。MCT誘導的肺動脈高壓程度取決于MCT的劑量[5],廣泛采用的劑量主要有50 mg·kg-1和60 mg·kg-1,一般2 周后造模成功。通過血流動力學指標判斷模型是否成功,主要指標有肺動脈平均壓力(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mPAP)、右心室收縮壓(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RVSP)、右心室肥厚指數(righ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dex,RVHI)。有研究表明這兩種劑量誘導的PH模型RVSP與死亡率相當,但50 mg·kg-1對肺中、小動脈中膜厚度改變更為明顯[6]。
MCT模型具有技術簡單、可重復、時間短、穩定性好、低成本等優點。MCT能引起內皮功能障礙,較好模擬臨床上炎性相關的PH,但對重度血管增生性PH的模擬有限。另外,MCT誘導的大鼠通常死于MCT誘導的肺毒性、靜脈阻塞性肝病和心肌炎,而不是死于肺動脈高壓[7]。由于MCT模型形態學變化發展得非常快并且不易通過治療干預來預防,所以作為臨床PH模型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 慢性低氧性模型
低氧性肺動脈高壓(hypox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HPH)是臨床常見的一類PH,常由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睡眠呼吸暫停、高原病等導致。慢性缺氧(chronic hypoxia,CHP)會引起內皮細胞損傷,以致相關舒縮因子失衡,增加肺血管收縮反應并促進血管重塑,最終發展為肺動脈高壓[8]。近年來缺氧性肺血管收縮和肺動脈重塑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內皮素-1、一氧化氮、環氧合酶和腺嘌呤核苷酸途徑。
CHP模型需將動物置于低氧艙內,通入N2和O2混合氣體,通過控制器將O2濃度控制在(10.0±0.5)%(體積分數),缺氧時長2~8周,喂養期間定期清掃并補充食物和水。大量研究證明,持續缺氧或間斷性缺氧(約8 h·d-1)均可發展為PH,并且低壓低氧艙或常壓低氧艙也均可成功制備模型。
慢性高碳酸血癥常見于缺氧性肺病患者,并且根據臨床觀察,除非同時存在高碳酸血癥,否則低氧性肺病很難發展為肺動脈高壓,可見二氧化碳分壓與肺動脈壓力密切相關。因此,吸入低氧伴高二氧化碳混合氣體制備PH動物模型更符合臨床患者情況。將動物置于常壓低氧高二氧化碳氧倉中,倉內氧濃度維持在9%~11%,二氧化碳濃度維持在5%~6%,每天8 h,每周6 d,飼養4周[9]。
通過慢性缺氧誘導肺動脈高壓,易于操作,并且牛、鼠、羊、豬都可以建立CHP模型。但慢性缺氧反應在物種間存在差異,即使是同一物種隨著年齡、性別的不同,反應也會受到顯著影響,最常用的動物是大鼠和小鼠[10]。由于缺氧誘導是可逆的,因此較難模擬臨床重癥PH,并且不能完全模擬PH的血管損傷情況。此外該方法對設備要求很高,很難同時進行大量動物實驗,盡管如此,這兩種模型都為體內研究PH發病機制提供重要的疾病模型。
3 栓塞性模型
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是由內源或外源性栓子阻塞肺動脈,引起肺循環和右心功能障礙的臨床綜合征[11]。慢性血栓栓塞型肺動脈高壓(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是PH的一種獨特形式,是急性肺栓塞或肺動脈原位血栓形成的長期后果,表現為肺動脈增大、內膜受損及周圍血管阻塞[12]。
從廣義上講,此模型分為2類:注射血栓或者異物。
血栓模型是從自體或供體(異源)動物獲得血液樣本在體外凝結成血栓,然后再將其注入實驗動物中。注射血栓可較好表現急性肺栓塞的病理生理情況,但是由于離體血凝塊的大小和體積均不規則,難以保證肺血管阻塞的程度和持續性,而且自體PE模型還需要進行2次手術,在大鼠、兔或豬中會產生循環休克,操作復雜。
與此相比,很多實驗室已采用將惰性材料注入頸靜脈的方法來模擬肺栓塞,包括大鼠、兔、狗、羊、貓、豬都可以建立CTEPH模型。其中大鼠模型較為常見,體質量(350~500) g,通過右頸靜脈注射聚苯乙烯微球(15~25 μm,130萬~195 萬個珠/100 g)。該方法可以控制進入肺部的微球數量,較準確地增加肺血管阻力,還避免發生免疫反應、大鼠纖維蛋白溶解率高等問題[13]。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微球是阻塞在肺部毛細血管前小動脈中,而不是臨床上通常觀察到的阻塞在近端肺動脈。
栓塞性PH模型引起的血流動力學變化與臨床一致[13],產生的促凝狀態、血栓前變化可作為臨床避免血栓栓塞及外科手術等干預機制的實驗對象[14]。
4 手術分流模型
肺動脈高壓是先天性心臟病的常見并發癥,高肺血流量引起的肺血管重構是其重要的病理過程。手術分流可以增加肺部血流量,其中體循環動脈-肺動脈之間的分流和動-靜脈之間的分流是較常用的左向右分流型肺動脈高壓建模方法。
4.1 體循環動脈-肺動脈之間的分流由于大、中動脈壓力高于肺動脈壓力,通過壓力階差在兩者間建立分流可使體循環血液分流至肺循環,使肺循環血液增多。該方法多采用犬、豬、羊等大型動物。包括誘導主動脈和肺動脈、左頸總動脈和肺動脈、左鎖骨下動脈和肺動脈分流等。盡管能更好的模擬臨床上慢性心臟病相關的PH,但由于開胸手術難度較大、創傷大、飼養大體積動物困難及成本等問題,因此較難推廣和應用。
4.2 動-靜脈(A-V)之間的分流利用動靜脈間較大的壓力差,分流后動脈血流入靜脈,使流回右心的血液增加,繼而使右心射入肺動脈的血液增多。該方法多采用兔、鼠等小型動物。大鼠多采用主動脈-腔靜脈分流;兔多采用頸總動脈-頸靜脈分流;有研究首創通過腹主動脈-下腔靜脈分流建立小鼠的PH模型[15],小鼠模型為研究PH的分子機制提供了更多機會。與大中動脈-肺動脈間的分流相比,A-V分流具有死亡率低、侵入性低、通暢性較高、成本低等優點。
常見的PH動物模型主要是慢性低氧模型和野百合堿誘導模型,盡管這些模型增加了對PH肺血管重塑機制的理解,但與臨床的發病機制和疾病表型不同。隨著PH機制研究從單純的血管收縮轉變為血管增生,血液分流的作用被認為在PH的發展中至關重要。
5 遺傳修飾模型
由遺傳因素導致的肺動脈高壓稱為遺傳性肺動脈高壓(heritable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HPAH),主要有家族性肺動脈高壓(familial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FPAH)和伴基因突變的特發性肺動脈高壓(idiopathic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IPAH)[16]。在過去的世界肺動脈高壓專題討論會(world symposium on pulmonary hypertension,WSPH)中,科學界不斷揭示PH相關基因:BMPR2、ALK1、ENG、SMAD9、SMAD1、CAV1、KCNK3、TBX4、E2F2AK4、GDF2、ATP13A3、AQP1、SOX17[17-18]等,增強了對PH復雜遺傳基礎的理解。
5.1 基因敲除模型據文獻報道,約有70%~80%的FPAH和10%~20%的IPAH病例是由BMPR2突變引起的[19]。有研究證明BMPR2突變類型與PH敏感性之間存在基因型-表型關系[20]。去除外顯子4、5的BMPR2基因敲除小鼠(BMPR2△Ex4-5/+)會表現出輕度PH,損害肺血管系統對長時間低氧的重塑能力[21]。還有去除第2個外顯子的BMPR2基因敲除小鼠(BMPR2△Ex2/+),這種小鼠對低氧反應性增加[20]。除此之外,有研究采用平滑肌特異性強力霉素誘導BMPR2第899位氨基酸的突變(SM22-rtTA x TetO7-BMPR2R899X),產生了非常接近人類的PH[22]。
除了BMPR2基因敲除模型,還有其他基因敲除模型,如敲除血管活性腸肽的小鼠(VIP-/-)自發形成中度至重度PH;敲除載脂蛋白E的小鼠(ApoE-/-)可自發為PH并伴有肺動脈肌肉化;內皮素受體B(ETB)敲除模型,當內皮素受體表達降低會增加肺內皮素水平,從而促進PH。
5.2 基因過表達模型5-羥色胺轉運蛋白(5-hydroxytryptamine transporter,5-HTT)的過度表達是PH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因素。首個5-HTT過表達轉基因小鼠模型是通過一個人工染色體對5-HTT的C端血凝素抗原決定簇和內部核糖體進入位點的一個lacZ報告基因進行修飾[23]。之后有研究采用平滑肌啟動子SM22建立5-HTT基因過表達模型(SM22-5-HTT+),這種小鼠肺部鉀離子通道表達水平降低,并且5-HTT表達增加的水平非常接近于人PH[24]。
常用的還有過表達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轉基因小鼠,對研究IL-6在PH發展中的作用以及抗炎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有研究采用過表達血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1,Ang-1)建立大鼠轉基因模型,Ang-1的表達水平與PH的嚴重程度成正比[25]。研究表明大約5%的S100A4/Mts-1過表達的小鼠發生肺血管重塑,可觀察到其他模型沒有的叢狀病變[26]。
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制備PH模型,能從動物整體水平研究目的基因的表達調控規律,加深了我們對PH病理生物學及治療學的認識,但是該方法存在技術難度大、動物模型品系過少(主要是小鼠)等缺點,仍需進行多方位的改進。
6 混合因素誘導模型
單一因素誘導模型會顯示人類PH早期階段的特征,但與單一因素相比,混合因素誘導的疾病模型與人類重度PH的關聯性更好。其中SuH模型最具有代表性,即采用C57BL/6小鼠通過單次皮下注射VEGFR2抑制劑SU5416(20 mg·kg-1)并將其置于常壓低氧室(10%FiO2),缺氧3周,若進行長期實驗,可每周注射一次SU5416[27]。與單純低氧誘導相比,該模型出現新內膜增厚和叢狀病變,并且對其他器官血管沒有影響,避免其他因素干擾。
除了利用低氧聯合SU5416造模,也有研究采用低氧聯合MCT模擬重癥PH,還可觀察到血栓性病變[28]。除此之外,切除左肺,使血液僅在右肺循環,手術后1周內注射MCT或SU5416[29],肺血流量增加和內皮功能障礙聯合誘導新生內膜形成的重度PH,其局限性是需要一定的手術技能。
多因素干預提高了模型的成功率,但也增加了動物的死亡率。由于臨床診斷通常是重癥,混合因素誘導模型更有助于發現肺循環血流動力學和結構改變的相關治療靶點。
7 結論和展望
PH的異質性和治療難度對動物模型的使用和改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PH動物模型的發展主要經歷了2個階段[30],第1階段是肺動脈非特異性內膜和外膜增厚,主要包括經典模型(即低氧和MCT);第2階段是發生叢狀病變,血管逐漸閉塞,肺動脈壓進行性升高,即手術分流、栓塞模型、遺傳修飾以及混合因素誘導造模。本文概述了PH研究中的不同動物模型,同時重點關注它們與PH患者的相關性,有利于科研工作者根據疾病的不同階段選擇合適的動物模型,取得理想的造模效果。同時,也為進一步闡明PH的病理機制、提高PH患者的預后、探索新的治療靶點提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