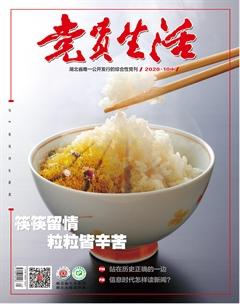讓別人看到自己的全力以赴
步入30歲不久后,我維生的方式是在日本販?zhǔn)蹚拿绹?guó)買回的舊書(shū)與古董。對(duì)沒(méi)有背景也沒(méi)有實(shí)體店面的我來(lái)說(shuō),這門(mén)生意并不好做。
想了很久,我想到的解決方式是——寫(xiě)信。這是從過(guò)去我母親的做法中得到的啟發(fā)。
家母以前就勤于讀書(shū),是個(gè)幾乎每天都在寫(xiě)信的人。她一天要寫(xiě)好幾封信,不只是寫(xiě)給親戚朋友,更包括寫(xiě)給客人的感謝信與邀請(qǐng)函。
那時(shí)她經(jīng)營(yíng)一間麻將館,不需要太多設(shè)備,也不用供應(yīng)多正式的餐點(diǎn),正因所有麻將館的差異性不大,反而更考驗(yàn)經(jīng)管者的手腕,特別擅長(zhǎng)與人溝通的她成功的原因或許就在這里。
“從寫(xiě)信開(kāi)始,也以寫(xiě)信結(jié)束。”這是母親的口頭禪,她還常說(shuō):“不能打電話,寫(xiě)信更重要。”
這已經(jīng)是20年前的事了。沒(méi)有店面,以上門(mén)挨家挨戶推銷方式開(kāi)始賣書(shū)的我,遇到的第一道關(guān)卡就是“如何讓對(duì)方答應(yīng)見(jiàn)面。”
但從電話簿里查到的聯(lián)絡(luò)電話,幾乎每個(gè)人都是大師級(jí)人物。無(wú)論是打電話到設(shè)計(jì)師事務(wù)所或攝影師工作室,除非有很重要的事,否則大師們本人是不會(huì)親自接電話的。
就在無(wú)法順利拜訪客戶而感到一籌莫展之際,我忽然想起昔日母親的做法。于是我在制作商品說(shuō)明資料時(shí),會(huì)附上一封信,一起寄給對(duì)方。每一封信都親手書(shū)寫(xiě),信上說(shuō)明自己從事這種工作,往返日本與美國(guó)兩地,銷售自己挑選的書(shū)……等等。
但沒(méi)想到情況依舊,當(dāng)我苦思時(shí)想到的還是母親。她那時(shí)的信都是用毛筆寫(xiě)的,連信封上也是漂亮的毛筆字,給人一種很體面的感覺(jué)。相較之下,我的信一看就是“姑且寫(xiě)寫(xiě)看”的敷衍,用的是在便利商店隨手買來(lái)的信紙和原子筆,把信投進(jìn)郵筒時(shí)還想著“反正一定沒(méi)希望”。抱著這種心態(tài)做事怎么可能順利!
后來(lái),在把信投進(jìn)郵筒前,我隨手拿起其中一封,以不知道是誰(shuí)寄給我的假想心態(tài),結(jié)果連自己都覺(jué)得,如果是我收到這封信,一定拆都不想拆。
同樣是親筆信,和母親看起來(lái)禮數(shù)周到又落落大方的信差得太遠(yuǎn)了。
“要是能像母親那樣寫(xiě)信,應(yīng)該就不會(huì)被丟掉了吧。”我懷著這種想法,買來(lái)毛筆和信封,信件內(nèi)容都用毛筆寫(xiě)。如果收到用毛筆寫(xiě)的信,感覺(jué)上總是比較特別。助手或公司其他人或許也會(huì)被這樣的原因打動(dòng),而產(chǎn)生“必須讓大師親自看到”的想法吧。
我一樣算準(zhǔn)對(duì)方的收信時(shí)間打電話過(guò)去,這次得到的反應(yīng)和之前完全不同。“您好,我是前幾天寄信過(guò)去的松浦彌太郎。”這么一說(shuō),接電話的人立刻回答:“喔,的確有收到這封信。”
毛筆寫(xiě)信既罕見(jiàn)又引人注目,容易讓人留下印象,電話立刻被轉(zhuǎn)接給大師的次數(shù)也增加了,我想拜訪的對(duì)象似乎也被如此禮數(shù)周到的信打動(dòng)。
寫(xiě)信這件事本身就是禮數(shù)周到的行為,再加上用毛筆嚴(yán)謹(jǐn)工整地書(shū)寫(xiě),更是禮上加禮。全力以赴的行動(dòng),能為我們突破僵局,這是當(dāng)時(shí)的我所能盡的全力,也是我希望能讓對(duì)方獲得的感動(dòng)。
直到現(xiàn)在,我仍非常重視親筆寫(xiě)信這件事。因?yàn)椋寗e人看見(jiàn)自己“全力以赴”的方法不只一種,而這些方法都沒(méi)有說(shuō)明書(shū)可以參考。
摘自《正直》,天津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