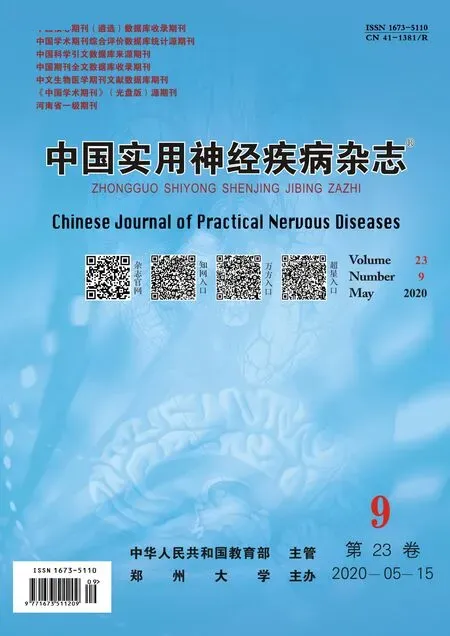腦內淋巴引流和Aβ清除機制對阿爾茨海默病防治的研究進展
周雪瑩 徐武華
1)暨南大學醫學院研究生院,廣東 廣州 510220 2)暨南大學醫學院附屬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 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臨床病態營養研究所,廣東 廣州 510220
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種起病隱匿、以認知障礙和記憶力損害為主的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不幸的是,至今尚無有效的藥物來逆轉甚至減緩這種疾病的進展[1]。關于的AD發病機制存在許多假說,其中β淀粉樣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級聯反應學說作為各種主、被動免疫治療的理論基礎,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該學說認為,各種誘因導致神經細胞表面的Aβ前體蛋白異常,大量被切割成具有高度神經毒性的Aβ,由于其生成速度和總量遠超過腦內清除能力,使得Aβ聚集形成不可溶性的Aβ斑塊,并誘發炎癥、細胞凋亡等一系列難以逆轉的級聯反應,最終引發一系列全面性、進行性、不可逆的臨床表現[2]。因此,減少Aβ生成對AD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思路。但在過去二十年里,以Aβ免疫清除為標靶的Aβ疫苗研究卻無一獲得成功[3],這使人們需要反思級聯反應學說的局限性并繼續探索Aβ失衡的真相。
近期實驗表明[4-5],在絕大多數的散發性AD患者腦中,Aβ的生成速度保持相對恒定,只是清除速度出現明顯下降,故內源性Aβ清除機制損傷(而非生成增加)可能為AD病理的真正原因。最新證實的腦淋巴引流系統[6-8]和睡眠狀態下大腦代謝廢物的自我清除機制[9]為其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本文從腦淋巴引流的角度闡述其在Aβ清除機制中的影響,并展望對未來AD防治的作用。
1 腦淋巴引流的組成和分類
長期以來,由于未發現解剖意義上的淋巴管結構,大腦始終被認為處于一種獨立封閉的免疫豁免狀態。腦脊液-蛛網膜顆粒-靜脈通道可有效清除腦內的代謝廢物,發揮類淋巴的作用。有人也觀察到軟腦膜延伸至腦實質內并在動靜脈周圍形成的微小間隙-血管周圍間隙(paravascular space,PVS)中存在著活躍的物質交換現象,由此認為PVS可能具有類淋巴功能[10]。直到新近證實的腦膜淋巴管[7,11],腦內淋巴引流的完整通路才逐漸清晰,并使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對Aβ代謝的影響。目前已知的淋巴引流至少存在以下兩種途徑:類淋巴途徑(動脈壁間引流途徑、膠質-淋巴途徑)和腦膜淋巴管途徑。
2 類淋巴途徑對Aβ清除的影響
2.1動脈壁間引流途徑采用立體定向和熒光技術,CARARE等[8]發現了大部分可溶性溶質先擴散至腦實質,再沿腦毛細血管和小動脈的基底膜運輸,最后排出大腦,由此推測血管基底膜在清除Aβ時起到淋巴管的作用。而WELLER等[12]首次建立了“動脈壁間引流途徑”的理論模型,并提出了與血流方向相反的循環動力來源于動脈搏動。該途徑在AD和腦血管淀粉樣病狀態下被明顯削弱,并伴隨著基底膜大量的Aβ沉積[13]。
研究證實,影響該途徑的主要因素包括ApoE 4等位基因、免疫復合物沉積、動脈的年齡和搏動頻率等。ApoE4等位基因是遲發型AD公認的危險因素之一,ApoE4可競爭性地抑制Aβ與低密度脂蛋白受體相關蛋白-1結合,同時還能與Aβ結合成ApoE *Aβ免疫復合物,從而削弱腦組織對Aβ的非免疫清除[14]。KYRTSOS等[15]的研究則顯示,作為血管年齡關鍵指標的血管剛性和心率也積極參與了這一途徑。當腦動脈剛性指數增加2倍時,腦組織Aβ40和Aβ42水平分別增加近100和1 000倍;而運動所帶來的心率增快(90次/min左右)也有助于加快Aβ的清除速度,這與AD的血管機制假說以及運動有助于AD防治理念相符。盡管有學者質疑出現在上述研究中的動脈壁間示蹤劑聚積現象可能為注射壓力推動所致,而非自然狀態下腦組織間質液(interstitial fluid)的整體流現象[16],但鑒于AD越來越被視為一種“從搖籃到墳墓”,且與飲食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慢性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進一步明確該途徑不僅有助于解釋AD的發生和發展,還有望將腦卒中和AD這兩種最為常見,但性質迥異的腦病防治整合在同一平臺之上[17]。
2.2膠質-淋巴途徑星形膠質細胞是血管-神經單元的重要組成。LLIFF等[6]利用雙光子顯微鏡發現星形膠質細胞足突末端的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4,AQP-4)在介導腦實質主動運輸Aβ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并由此提出了“膠質-淋巴”途徑的概念。該途徑與外周代謝產物的淋巴循環極為相似,而前者最大的特點在于需要反復、主動依賴AQP-4。敲除AQP-4的基因小鼠會使Aβ清除率下降55%~65%[6],并增加APP/PS1小鼠腦內Aβ斑塊沉積,加劇星形膠質細胞萎縮,并最終導致神經突觸蛋白損傷和認知功能障礙[18],推測AQP-4的缺乏可能導致Aβ難以順利被動、靜脈之間的膠質-淋巴途徑清除。
影響該途徑的主要因素與動脈壁間引流途徑相似,除外前述的腦動脈搏動,還包括睡眠狀態、睡眠姿勢。LLIFF等[19]分別通過手術結扎單側頸內動脈和靜脈注射多巴酚丁胺兩種方式,觀察到CSF-ISF交換速度的明顯變化,前者減慢,后者加快,并認為腦動脈搏動很可能是Aβ等代謝產物從動脈端PVS進入腦實質的關鍵驅動力。此外,睡眠狀態下(尤其是快速眼動睡眠期[9])示蹤劑沿PVS流入顯著增加,以及睡眠期間腦細胞體積變小和腦間質空間增加等現象[20],可能有助于降低包括Aβ在內的腦代謝產物在腦組織間的流動阻力,便于代謝產物的清除。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相比仰臥位和俯臥位,側臥位的膠質-淋巴清除效率更高,推測這可能是長期的人類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腦代謝產物優化清除方式[21]。考慮到絕大多數癡呆患者普遍存在睡眠障礙和睡眠節律異常,進一步佐證了睡眠在AD病理機制的重要地位。
3 腦膜淋巴管途徑對Aβ清除的影響
2015年,LOUVEAU等[7]和ASPELUND等[11]兩個團隊首次在小鼠硬腦膜中發現了淋巴管結構,這一發現隨后在斑馬魚[22]、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23]中相繼得到證實。當結扎小鼠頸深淋巴結后,腦膜淋巴管中的Aβ強度明顯增加,同時伴隨著管徑的明顯增粗,而嗅神經的神經鞘和周圍小血管也共同參與了顱底硬腦膜淋巴管網的組成[11],這些發現對于理解諸如AD和帕金森病等患者的首發癥狀(如嗅覺減退)和常見病理區域(如內嗅皮層)至關重要[24]。
4 腦淋巴引流和Aβ腦內清除機制對AD防治的啟示
腦淋巴引流系統是一個復雜完整且多渠道的腦代謝產物排泄體系,全面參與了AD的病理過程,但以該系統為干預靶點的防治性研究不多。ALBARGOTH等[13]發現,經由腦池注射的藥物在腦不同部位的滲透深度差異有別,其中腦橋是Aβ穿透率最高的區域,間接驗證了動脈壁間淋巴引流途徑的客觀存在,也被視為腦池內注射反義寡核苷酸成功治療脊肌萎縮癥的藥理基礎[25],值得未來AD藥物臨床治療借鑒。XU等[18]在AD模型小鼠中發現,通過基因調控技術可以改變AQP-4的通透性。而聯合磁共振技術、近紅外光譜和靜脈注射示蹤劑等手段能動態、活體監測膠質-淋巴途徑的流體動力學,有望成為預測或早期識別AD的新方法[26-28]。MESQUITA等[29]分別通過向小鼠腦池內注射維替泊芬(一種可消融腦膜淋巴管的光增敏劑)、結扎小鼠頸深淋巴結、采用Prox1+/-小鼠(腦膜淋巴管基因缺陷小鼠)等三種淋巴引流障礙模型,均觀察到腦脊液從動脈端PVS流入和組織間液從靜脈端PVS流出的速度明顯減慢,但能被一種叫作血管內皮生長因子C的物質部分逆轉。
隨著越來越多的流行病學和循證醫學證據支持睡眠、適度的運動、腸道菌群[30-31]等與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和AD發生發展之間的密切關系。由于腦淋巴引流系統主要參與的是腦代謝產物的日常清除,與以往疾風暴雨式的Aβ主/被動免疫清除不同的是,基于該系統的AD防治手段可能需要更長的周期和更早的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