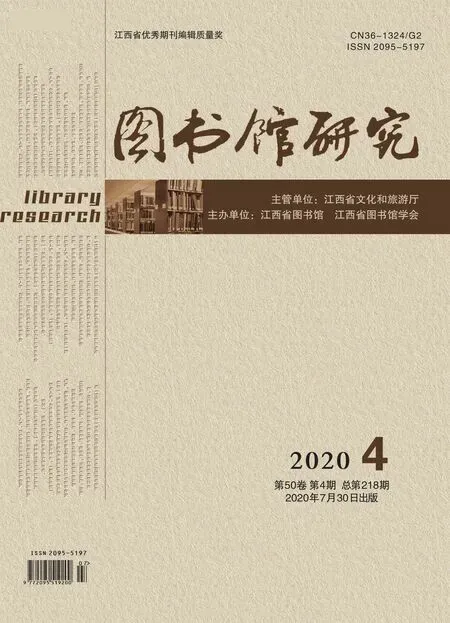書簽考*
王甜甜
(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辭源》釋“籤”曰:“標簽,于竹片上書符號。凡標題皆謂之籤。同‘簽’。”[1]《漢語大詞典》進一步解釋道:“指竹片或紙片上寫有文字符號的一種標識。”[2]由此可知,書簽最早可能出現在竹簡廣泛使用的簡牘時期,后來隨著書寫材料的改變,普遍用于傳達紙質書籍的書名信息。由于書簽信息傳達的實用性,為多數學者和使用者所熟知并研究,但對它起源、發展史等的探討或不夠深入具體或有失誤。①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如:王萌《中國書簽鑒賞》(湖南美術出版社,2012.1:1-7),李敏麗、陳勇《淺談“書簽”》(《江西圖書館學刊》,2006(4):122-124),王靜憲《說題簽》(《收藏家》,1996(3):46-49),溫曉婷、楊帆《邊緣文化的生命力和當代價值——以書簽為例》(《大眾文藝》,2007(18):120-121),回聲《一葉書簽半部史》(《中華手工》,2017(02):118-121),陳和軍《說“書簽”》(《咬文嚼字》,2000(8):36-37),李更旺,李維純《古書史中卷軸書制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1):56-64),包書燕《簡論書簽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燕山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等較全面地論述了書簽在各歷史時期的發展概況。鑒于此,本文在參考前人成果和廣泛搜集材料的基礎上,擬從書籍史的角度,將書簽分簡牘、卷軸、冊頁三個時期進行系統考察。
1 簡牘時期的書簽
目前,學界對簡牘時期的書簽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李敏麗,陳勇②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如:王萌《中國書簽鑒賞》(湖南美術出版社,2012.1:1-7),李敏麗、陳勇《淺談“書簽”》(《江西圖書館學刊》,2006(4):122-124),王靜憲《說題簽》(《收藏家》,1996(3):46-49),溫曉婷、楊帆《邊緣文化的生命力和當代價值——以書簽為例》(《大眾文藝》,2007(18):120-121),回聲《一葉書簽半部史》(《中華手工》,2017(02):118-121),陳和軍《說“書簽”》(《咬文嚼字》,2000(8):36-37),李更旺,李維純《古書史中卷軸書制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1):56-64),包書燕《簡論書簽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燕山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等較全面地論述了書簽在各歷史時期的發展概況。、王靜憲、回聲、包書燕等學者所持有的首簡或贅簡是簡牘時期書簽的觀點;另一種以李更旺,李維純為代表,認為文書簽牌為該時期的書簽。這兩種觀點都有尚待商榷之處。
迄今為止,在出土文獻記載中,發現最早的書簽是晉《王逸集》的象牙書簽[3]。簡牘時期還沒有發現具體的書簽實物,但并不意味著這一時期的書簽就無從考證。書簽,又稱書籍題簽,是每個歷史時期的書籍都具有的物質屬性之一。因此,將題簽置于整個書籍發展史中加以考察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關于題簽,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七《甄正論》卷上“簽題”條注云:“小簡也,古者題簡以白事謂之簽。”[4]簡牘學界將這種“小簡”稱之為“簽牌”。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西域考古發掘品中保存有大量的文書簽牌,從中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了解到簡冊時期的題簽形制。這種題簽由竹木制成,長度比23.1厘米左右的標準簡短,主要有兩種形制,一種是為了與簽繩相連,在題簽上端中部鉆孔,如Or.8211/598③本文所引的簡牘文獻、英藏敦煌文獻、法藏等敦煌文獻均來自于“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英文簡稱IDP)”網站;文中所引的俄藏敦煌文獻引自《俄藏敦煌藝術品(2)》(俄羅斯國立艾而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號題簽,長6.1厘米,寬1.5厘米,上端中部有孔,孔中簽繩尚存。此木牌正反兩面的孔口下端都題有標題,正面題有“王門廣新隊”,背面題有“大黃承弦一”。其他如Or.8211/599、Or.8211/693、Or.8211/705號簽牌都是此種形制。另一種是為防止簽繩滑脫,在題簽上兩邊對稱處分別刻削三角形狀的契口,并以雙契口為參照物,在其下題寫標題,如Or.8211/616號題簽,長7.1厘米,寬3.2厘米,雙契口處尚纏繞有簽繩,契口下方墨書標題“兵四時薄”。此外,Or.8211/891號藏品也是此類題簽。由是,可推知此期的書簽應是在題有標題的竹木簡上打孔或刻削契口并通過簽繩與簡冊古書相聯結。
對于首簡或贅簡之說,其上標題多為篇名。黃威指出,簡帛古書還有統攝眾篇之書的書名,它并不直接題寫在載體上,而可能存在于書帙、牙簽或目錄上[5]。關于書帙,馬怡在《書帙叢考》中認為它是帛書和卷軸形態之紙書重要的裝具[6]。根據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系在竹笥上的實物簽牌[7],和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出土的系在絹袋口沿處的實物簽牌[8],以及下文將要提到的張政烺所考證的《王逸集》象牙書簽系結于書帙之外[3]等實例,推測簡帛古書的書簽還有系結在書帙外的可能。因此,不能簡單地把首簡或贅簡當成是簡牘時期的書簽。
綜上,通過對文書、實物簽牌類題簽的考證和書籍存放于書帙中流傳的可能性,可以間接推知簡帛古書的書簽應是在題有標題的竹木簡、牙骨上打孔或刻削契口并通過簽繩系結在簡冊上或書帙外的書簽,即是下文提到的“掛簽”。由于年代久遠,這些竹、木、骨制的掛簽易于散亂,多與簡冊、書帙分離,再加上形制短小、長期漫漶等原因,時至今日,我們已很難發現確切的簡牘時期的書簽實物。
2 卷軸時期的書簽
卷軸時期是指漢至唐代以卷軸裝為主要裝幀形式的書籍發展階段。卷軸古書是繼簡冊古書后,用縑帛或紙制成的貫軸舒卷的書籍。它主要盛行于西漢造紙術發明后的紙寫本時期,是紙寫本最早的裝幀形式。書寫材料和書籍裝幀形式的變化,使得這一時期的書簽呈現出與簡牘時期不同的形態。
卷軸裝書籍的書簽主要有以下四種形式:
2.1 掛簽
掛簽,顧名思義,即懸掛于書籍外側的一枚題寫書名信息的小牌子。卷軸古書上的掛簽主要系結于軸頭上或書帙外側。由于書簽材質的不同,此期的掛簽可分為牙簽、木簽、紙簽等。
牙簽,又稱“牙黎”,它由象牙制成,因象牙貴重難得,多為宮廷王府或富庶之家藏書所用。牙簽的使用與卷軸書入藏的方式有關。馬衡指出:“卷軸以帙裹束,置于架上,每患不易檢尋,故有簽以為標識。”[9]李更旺更為詳細地論述了卷軸書入藏存放方式與牙簽位置的聯系:“諸多卷書平放在書架上,軸桿的一端向外,由于每一卷書的書體被書衣套裹,使人們無法見到卷數的名稱或卷次,為便于檢索卷書,所以在每個卷書露在外面的軸頭上掛一個牙簽作為標識,牙簽上刻有卷書的書篇名或卷次,有的還給牙簽染上不同的顏色,以此作為查閱、插架或抽架的依據。”
然而,由于世事變遷,這些官府或私家藏書卷子上的牙簽制度很少有實物發現,僅粗泛地見于史料記載,沒有詳盡的形制、文字等方面的描述。迄今為止所知的最早的書簽實物是“漢王公逸象牙書簽”,此簽為張政烺在清人黃俊編輯的書法篆刻類作品《衡齋金石識小錄》中發現,但沒有關于出土和流傳情況的記載。張先生認為此牙簽是系結在《王逸集》之外的書簽,根據其字體勢在隸楷之間和首行“元初”二字誤倒為“初元”,判定此牙簽應為魏晉或北朝時的產物,不早于漢代;依照牙簽上所刻文字對王逸、王延壽父子文集的概述性介紹,以及牙簽正反面皆有文字且上部有圓孔的形制特點,該牙簽當不是某一卷的書簽,也不能附著于物,而是引孔穿繩系結于書帙之外的書簽,其功用為方便翻檢和舒卷[10]。
卷軸古書的掛簽也有松木、紙張等材質的。王應麟《玉海》卷二七引晏殊《表》云:“縹帙松簽,盡黃香之未見。”[10]此句表明北宋時期卷軸古書上的書簽可能是用松木制作而成的。松木可防蟲蛀和經久耐用的特性的確可用于削制書簽的原材料。此外,李成晴曾提到,日本龍門文庫藏有卷軸本《遍照發揮性靈集》卷四,該書為鐮倉時代(1185-1333)空海法師詩文集。該卷書的系帶根部掛有一個用硬紙裁制而成的上窄下寬的梯形狀紙質書簽[11]。從形制上看,也屬于掛簽。
2.2 帙簽
帙,《說文·巾部》曰:“書衣也。”[12]是指以絹帛、布、竹等材料制成的用于包裹在書籍外部,起保護作用的書套。敦煌藏經洞內保存了大量的存放在書帙中的隋唐時期卷軸裝的佛典,它們的制作較為簡易,多數沒有軸桿,依托中古黃紙的堅韌,直接卷舒。其標題一般題于帙皮上或將題有標題的長條形簽條縫綴、粘貼在帙皮上。這種縫綴、粘貼在經帙帙皮上的題簽,我們稱之為“經帙標簽”,簡稱“帙簽”。
依據材質,帙簽可分為絲質和紙質兩種類型。絲質帙簽是縫綴在帙皮上的,根據其形制或位置特征,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上端連接帙皮,下端為倒三角形,正反面墨書經名、寺名等楷體字樣的帙簽。如S.6080①本文所使用各家所藏敦煌文獻編號簡稱如下:S.─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斯坦因編號,;P.—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伯希和編號,如果寫卷后附有碎片,則以p1、p2、p3……表示;Дх—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敦煌文獻編號;EO.—法國集美博物館藏敦煌文物編號;MAS.—英國國家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編號。其中不同拍攝角度的敦煌寫卷在編號后加有1、2、3……;若表示卷背內容,則在編號后加V。號帙簽為絹布材質,其上端縫制在較厚的麻紙上,二者接縫處可清晰地看到針腳痕跡,帙簽呈黃色,其上可能因時間久遠,有些許霉斑點,且下端被裁成了倒三角形樣式。簽條正面題有經名“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帙”字樣,背面題有寺名“三界”;敦煌研究院藏D.0816號帙簽也是絹布材質,呈黃色狀,其上沿留有針腳痕跡,下部為三個角上懸有紅、黃、綠不同顏色綴穗的倒三角形,簽條上墨書經名“廣博嚴凈經等一帙”。類似的帙簽題還有P.5013、P.3967p3、P.4514、Дх274和Дх275等。另一種是帙簽直接被縫制在竹制帙皮的左上端。這種情況較為少見,目前僅在IDP網站中發現EO1200和MAS859兩例帙簽。它們都位于經帙左上角處,與竹制帙皮上線織的花紋相連,精致美觀。紙質帙簽是上端或下端粘貼在帙皮(帙皮多為紙質)上,單面墨書經名、寺名或帙號的長方形簽條。根據其與帙皮的位置特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帙簽上端連接帙皮的帙簽題,如S.4664、S.4689-3、S.10394、S.10611、S.10613、S.10620、S.11324等;一種是下端連接帙皮的帙簽題,如 S.4701-2、S.4702-1、S.10391、S.10539、S.11364、S.11378等。因年代久遠,長期漫漶或散亂等原因,多數帙簽已與帙皮分離,僅有S.4664、S.4689-3、S.4701-2、S.4702-1等少數帙簽還與紙質帙皮連接。這種紙質帙簽在敦煌藏經洞中發現較多,大概是它相較于絲質帙簽而言更為便宜易得。
此外,這種紙簽不僅出現在經帙帙皮上,還會出現在卷軸古書的另一裝具——“函套”上。《太平廣記》卷300《杜鵬舉》記載了唐代濟源縣縣尉杜鵬舉游地獄的經歷,當杜鵬舉被引領到杜氏家族的籍冊旁時,文中寫道:“因引詣杜氏籍,書箋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具。”[13]可推測,這里的題簽當為紙書簽且粘貼在紫函之外。不過這種書籍函套主要用于收裝冊頁古書,在卷軸時期收裝卷軸形態的書籍還是多用書帙。
2.3 包首題簽
所謂包首,是指接續在卷軸裝書籍卷首的起保護內文作用的長條形紙張或絲綢。包首題簽,則是將題寫有書籍標題的長簽條粘貼到包首背面左上角邊緣處的標簽形式。它是粘貼于書籍包首背上的,本質上是附屬于卷軸古書上的標簽,因此,我們認為包首題簽是卷軸古書書簽的一種形制。
包首題簽在敦煌寫本文獻中較為常見,且裝飾性明顯。如S.11005、S.11077、S.11227等號題簽的簽紙都是考究的瓷青色紙,經名、帙次等標題信息都是用泥金書寫的工整規范的楷體字。其他如P.2521、P.4596、P.5027-1、P.5027-2、S.10977、S.10972、S.11015、S.1048號題簽雖沒有考究的裝幀,但墨書的標題甚為工整,簽紙都經過著色,裝飾性也較明顯。此外,敦煌文獻包首題簽首字上方往往有一個雙勾式的符號,它由兩個開口方向朝上的的對勾狀的符號組成,頗為美觀大方。黃威將這一符號稱之為“包首題符號”,認為它具有裝飾功用:依據其形態,總結歸納出四種基本樣式,指出了該符號樣式的多元化和裝飾屬性[14]。而包首題符號的裝飾功能也直接體現出了包首題簽形制的裝飾性。總之,不論裝飾與否,包首題簽以其粘附于卷軸古書包首背的特性,使之成為卷軸裝書籍的書簽形制之一。
2.4 軸簽
宋元時期,隨著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冊頁裝書籍盛行于世,但并不意味著卷軸裝書籍已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書籍從卷軸裝到冊頁裝的更替有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這從當時卷軸裝古書的書簽形制上可以窺見一斑。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國內并沒有發現從卷軸裝向冊頁裝過渡時期的書簽實物。李成晴發現在同時期的日本保存的一些卷軸裝文書中存留有與我國不同的書簽式樣,可窺見書簽制度的再演變,并對其進行簡要論述[15]。下面我們主要以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保存的荻野研究室所搜集的11-14世紀的寺廟田產類卷軸文書寫卷為例,對軸簽形制進行詳細論證。
在這些文書寫卷上,我們發現了許多位于軸桿上端且與軸頭連為一體的木制書簽。日本把卷軸古書上的軸桿稱為“往來軸”,因此,我們把這種書簽稱之為“往來軸簽”,簡稱“軸簽”。這種軸簽多是與軸頭相連的一個上窄下寬的梯形小木牌,上端的兩個角被斜著削去,呈現三角形的樣式,正反面題有文書名、寺廟名、時間等書名信息。如請求記號為“文庫12 00002 0001”①的《觀世音寺文書:筑前國.甲》上的軸簽就是此種樣式,正面墨書“觀世音寺”,背面墨書“早良奴婢例文”,而且裹卷在軸桿上的文書背面也有墨書“觀世音文書甲”,進一步標識書名信息。此文書寫于日本報安元年(1120),相當于中國的北宋宣和二年。《平群姉子田畠売券》(1114)、《僧広順家地沽卻狀》(1159)、《僧教厳山地沽卻狀》(1146)、《僧宗得田地沽卻狀》(1210)等寫卷上的軸簽都與之類似。
基于以上論述,可以發現卷軸時期的書簽形制多樣化顯著,但并非無繩準可言。通過對以上四種基本書簽材質和樣式的考察發現,它們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帙簽和包首題簽,簽條一般縫綴或粘貼在書帙帙皮、包首背上。這種縫綴或粘貼的方式也決定了題簽為質地柔軟的紙張或絹布材質。從式樣上看,這類題簽多為長條形的小簽條,有些簽條下端的兩個角會被裁去,形成倒三角形的樣式,上述的第一種絲質帙簽即是如此。此外,多數帙簽并不像包首題簽那樣,完全粘貼于包首背上,而是簽條的上端或下端縫制或粘貼在帙皮邊緣,這樣的設計或許是因為入藏合帙的卷軸書在堆積存放時,完全縫制或粘貼在帙皮上的題簽不易顯露,為了便于檢索,使得一部分題簽顯露在外。另一類是掛簽和軸簽,多為骨制和木制,主要通過簽繩系于軸頭、褾帶或與軸頭連為一體的方式和卷軸書籍聯結。這類題簽多是適應卷軸古書插架存放的需要。卷軸書在插架存放時,為了方便尋檢,會在軸頭或褾帶上懸掛書簽。可能由于通過穿孔引繩與卷軸古書軸頭相連的掛簽易于墜落和散失,在日本收藏的宋元時期的卷軸書籍上發現了與軸頭連為一體的軸簽,這樣做使得題簽的標識和檢索功用更為顯著。
從書籍演變史的角度來看,此時期的書簽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掛簽當是從簡牘時期系結在簡冊或書帙外側的書簽繼承而來。卷軸制向冊頁制過渡時期的軸簽也可看成是掛簽為克服其易散亂、掉落的缺點而進一步演變而成的書簽式樣。同時,帙簽和包首題簽都直接影響了冊頁時期的書簽形制,即冊頁古書上的書簽多為直接粘貼在書籍封皮上的面簽。可見,中國書籍史的發展是一個無間斷的演進過程,某一時期的書籍所呈現的某種物質屬性不僅可以追述到前代,還會對以后書籍的發展演變產生深刻的影響。
3 冊頁時期的書簽
唐朝末期,冊頁裝書籍隨著雕版印刷術的出現而產生,它由印刷出來的多張單頁裝訂成冊而成,是我國古代書籍發展的最后階段。受書籍裝幀形式的影響,本時期的書簽主要是粘貼在封皮或函套上,被稱為“面簽”“貼簽”或“浮簽”。這在時人的文學作品中也可略知一二,如清胡虔《柿葉軒筆記一卷》:“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皆抄本。……其面簽皆用絹,經以綠,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淺絳。”[15]清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此書)原裝十二冊,簽題皆藏經紙,題曰:《淮南子》。”[16]文中的“面簽”“簽題”都是指粘貼在封皮上的書簽。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集了大量的自宋代以來的帶有面簽的中國古代典籍,下面我們主要以此處所藏的漢籍為材料來源,從形制、位置和題寫的書名信息三個方面來介紹一下這一時期的書簽。
首先,從形制來看,為長方形題簽且占據封皮左側邊緣三分之二左右的空間。冊頁古書面簽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裝飾性顯著。這不僅體現在簽紙多用瓷青紙、藏經紙、黃麻紙等考究的紙張,還體現在邊框的樣式上。題簽邊框以內細外粗的雙邊框居多,部分考究題簽邊框會以各式各樣的花紋呈現,如《爵秩金覽》①書籍題簽上的外邊框是“龍鱗”式花紋;《大清縉紳全書》《云峰書屋集印譜》的內邊框是“磚瓦”狀花紋。《嘆世無為寶卷》《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寶經》、《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經》等“寶卷”類書籍的邊框鑲有泥金。面簽邊框紋落的多樣化在凸顯書名信息的同時也彰顯了文人志士們的高雅情趣。
其次,從粘貼位置來看,以豎直粘貼在封皮的左上端為多。這一特征主要受冊頁古書的裝幀形式和人們的閱讀習慣、生理特征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冊頁古書一般是右側線裝成書,書口的開口方向朝左,人們從左向右翻閱書籍。同時,中國古書豎排書寫,人們也習慣自上而下閱讀。因此,當古人手持書籍閱讀時,人眼一般集中在書籍的左上端,決定了將簽紙粘在封皮的左上部位更方便使用。
最后,從題寫的書名信息來看,很多面簽在書名的上方題有書齋名,下方題寫有篇名、卷數、冊數、書名題寫人、成書時間和印章等相關的書名信息。但有時這些書名信息并不題寫在書名下方,而是另外用一張小紙條粘貼在書籍右側上方處,如《唐安定郡王李光進神道碑》的右上方粘貼的小紙上題有“趙村碑帖上”,進一步對書中內容進行解釋說明。《爵秩全覽》《大清縉紳全書》《大清中樞備覽》《陜西延綏鎮志》等書則在面簽右側貼有一個比其略寬的長方形紙條,上面寫有類似目錄性質的對全書基本內容的介紹。題名字體大多為方大且古樸厚重的楷體字,少數為飄逸瀟灑的行書,部分“寶卷”類古書還會用泥金來題寫書名,更為人以視覺美感。
此外,此期用于收裝書籍的裝具主要是函套。函套上的書簽除面簽式樣外,“別子”上有時也刻有書名信息,以此充當書簽。別子有骨、竹、木、玳瑁等材質,相當于牙簽、竹簽等書簽款式。清鈕樹玉《非石日記鈔》:
十一月十五日,黃蕘圃來,購得南宋本《戰國策》。惜首闕二葉,末闕一葉,俱鈔補者,然已為罕見之秘笈矣。黃君云:“昔在京師得牙簽一,上刻‘宋本國策’,今此書適出,竟符夙愿。”[17]
這里提到的“牙簽”即指“別子”,它可以看成是卷軸古書書簽的遺意留存。
清代中后期以后,印刷技術顯著提高,精裝書和平裝書盛行,書名可以直接印在封皮上。但書簽并沒有消失,而是變成夾在書中,標記閱讀進度或疑難處的小薄片。隨著書籍裝幀技術的發展與革新,書簽已不僅局限于紙質,還出現了銅書簽、紅木書簽、和田玉書簽、景泰藍書簽等,甚至樹葉、花草、尺子、棉線等,只要能夠標記閱讀進度或疑難處,都可以當成書簽使用。書簽發展到今天,已不只是標識書名,它還具有了更多的供人欣賞、收藏的藝術價值。同時,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和普及,瀏覽器上的書簽功能和網絡書簽形式更多更便捷地承擔了書簽的標識功用。
4 結語
綜上所述,書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簡冊古書和書帙外的掛簽。由于書寫材料由紙代簡的轉變,卷軸古書上的書簽主要有掛簽、帙簽、包首題簽和軸簽四種形式。根據其材質和式樣,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主要以縫綴、粘貼為主的帙簽和包首題簽,多為絹布或紙張材質的長條形簽條;一類是系結在卷軸古書、書帙上的掛簽和與軸頭相連的軸簽,主要以樹木、硬紙等材質較為堅硬的長方形的題簽。后來,隨著書籍形態完全由卷軸變為冊頁,冊頁古書上的書簽形制主要是粘貼在書籍封皮或函套左上端的長條形的紙質面簽。
同時,不同書籍發展階段的書簽形制有著前后相承的演變關系。卷軸古書上的掛簽當是從簡牘時期流傳而來;敦煌藏經洞中的經帙帙簽對后世的面簽也有直接影響。此外,清代江標《黃蕘圃先生年譜》中記載的南宋本《戰國策》函套上題有書名信息的“別子”則是簡冊和卷軸時期牙簽制度的余緒。乃至今天,書簽雖更多地以裝飾性和收藏價值取勝,但書籍封皮上題寫的書名信息仍是其標識功用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