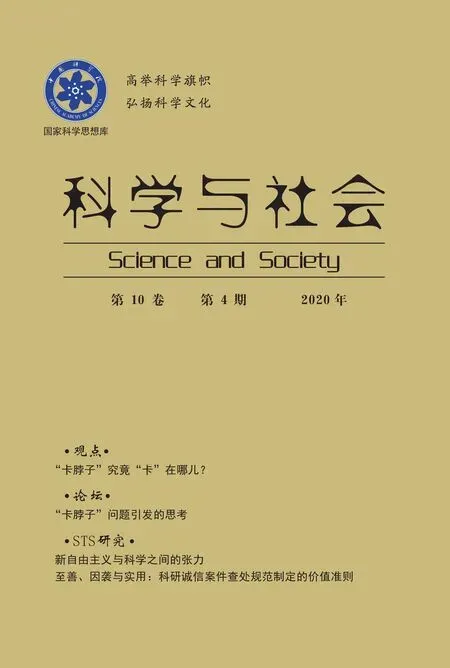新自由主義與科學之間的張力
2020-01-07 00:29:47王學謙
科學與社會
2020年4期
關鍵詞:科學
王學謙 蔡 仲
(南京大學哲學系)
一、前 言
在馬克斯?韋伯時代,普魯士處于俾斯麥的治理下,高效的官僚組織滲透到科學管理體系之中,使得國家快速實現了工業化,但傳統的科學精神亦受到相應的挑戰。韋伯對科學問題的思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在“科學作為天職”的演講中,他提出“科學①韋伯演講中的Wissenschaft,并非僅限于當時的自然科學,而是指理性化的學術,但科學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這種理性化的典范。進步是理智化進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1]一方面,他堅持傳統的科學自治精神;另一方面,他又直面專業化和官僚化對科學的影響。專業化和官僚化給工業時代的科學帶來了機遇,也沖擊了科學的自主性,引發了韋伯思考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張力問題。
當代“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概念的顯現,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潮的蔓延,使得科學在政治的壓力之下,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況:背負應用的語境、研究的商業化、市場的導向、創業創新的使命,科學無論是方法論層面還是制度層面上,都經歷了巨大的轉變,[2]形成了所謂科學的“跨時代斷裂”(epochal break)命題。這一時代在給科學與社會帶來空前的發展機會的同時,也極大地壓縮了科學的自主性,從而對科學產生了某些負面影響。由于新自由主義對科學的介入,特別是在特朗普上臺以后,科學家在政治的壓力之下,從傳統的氣候變化、能源問題,再到現在的疫情等各領域,科學未能真正履行其“天職”。……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科技教育(2020年2期)2020-12-07 05:55:01
中國科技教育(2019年11期)2019-09-26 10:49:15
中國科技教育(2019年10期)2019-09-26 10:48:13
中國科技教育(2019年12期)2019-09-23 08:02:08
小小藝術家(2019年6期)2019-06-24 17:39:44
今古傳奇·故事版(2016年15期)2016-09-07 06:57:32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6年7期)2016-05-14 10:24:41
小雪花·成長指南(2015年3期)2015-05-04 00:04:37
雕塑(1999年2期)1999-06-28 05: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