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土地的吶喊
張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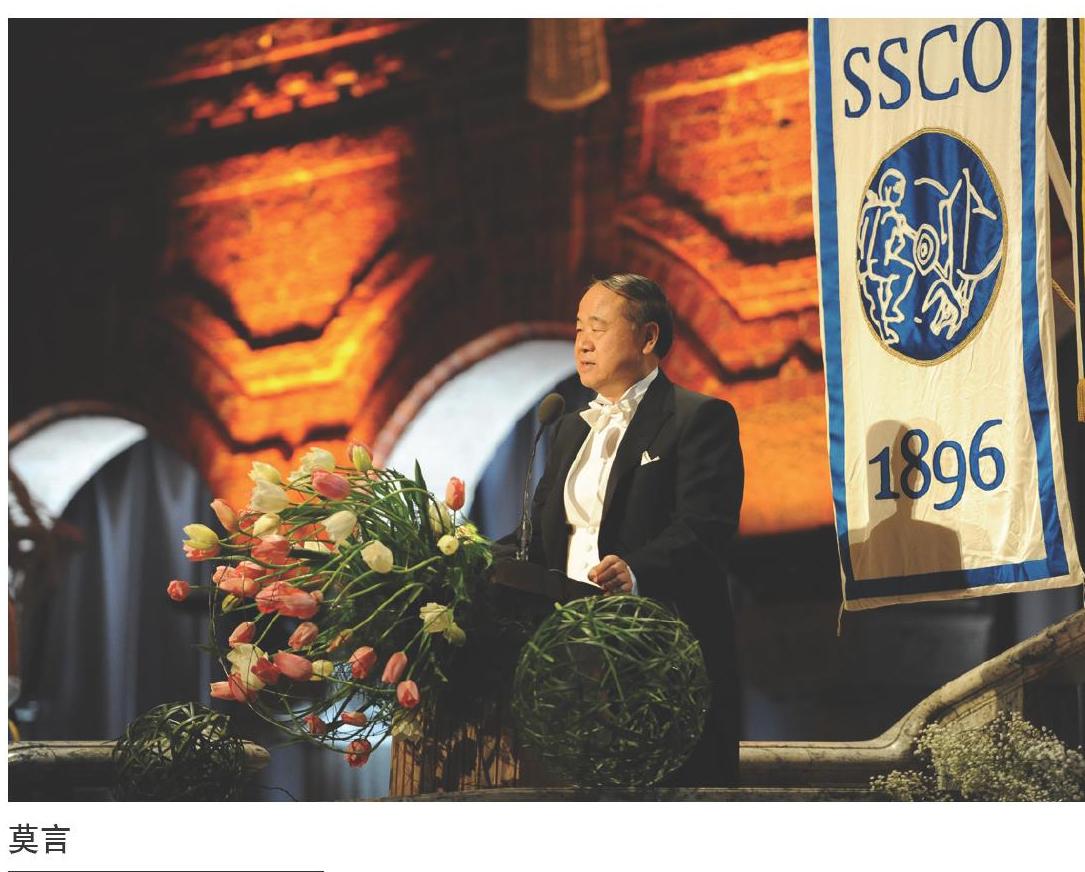
1.緣起
拍攝《文學的故鄉》蓄謀已久。日歷翻到2012年12月10日,瑞典國王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先生。那時我正客居洛杉磯,從電視屏幕上見證了這一時刻。我突然意識到,紀錄片應該為文學做點什么。
意識來自魯迅先生。中國電影繁花爛漫的30年代,沒有一臺攝影機為魯迅留下哪怕一分鐘的活動影像,沒有留下魯迅用紹興口音朗誦《阿Q正傳》的片段。待明星公司意識到魯迅的分量帶著攝影機趕來時,先生已經走在去萬國殯儀館的路上。
魯迅已矣。歷經百年陶煉,中國新文學已經到達世界高度。與這些杰出作家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下是我們的幸運,而不是低估文學的理由。作為一名文學的逃兵,我希望用攝影機為當代魯迅留下一段影像。
2.創意與影像
《文學的故鄉》并非作家傳記,也不是作品讀解,而是講述作家如何把生活的故鄉轉化為文學的故鄉。這一靈感依然來自魯迅。《阿Q正傳》里的未莊、 《祝福》里的魯鎮是否是少年魯迅生活過的安橋頭?《紅高梁》里的高密東北鄉是否就是莫言生活的故鄉?這一念頭引誘我用影像探尋文學的故鄉。
《文學的故鄉》拍攝的作家首先是在作品里成功地塑造了文學的故鄉,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其次, 《文學的故鄉》里的作家大多生長于鄉村,這也是故鄉最初、最原始的內涵;最后, 《文學的故鄉》里的作家應擁有不同的地理形貌與文化背景,組合起來基本象征了中國的面貌。
然而,文學是作家的心理搏斗,紀錄片需要物質形象,如何把心理戲劇呈現為畫面?有人擔心紀錄片拍成了采訪加空鏡,也有人擔心拍成一組生活碎片,而不是文學表達。 《文學的故鄉》首先呈現的是土地。每位作家都來自土地,每片土地都有河流:膠河流過莫言的高密平原,黑龍江流過遲子建的冰雪北國,梭磨河流過阿來的嘉絨藏區,丹江流過賈平凹的商州鄉村,黃河穿越劉震云的延津世界,里下河流進畢飛宇的蘇北水鄉。土地里不僅滋生莊稼草木,也滋養文化風俗。其次, 《文學的故鄉》跟蹤記錄作家回故鄉的影像。故鄉隱藏著作家的童年、成長與最初的感知,一旦回到故鄉,所有記憶都將被激活,可能隨機迸發出精彩的紀實場景,成為鮮活的文學現場:作品里寫過的地方,寫作的地方,留下童年記憶的地方。第三,作家心理創造過程的文學意象再現。藝術創作比女人生育還要神秘——什么情境下受孕,怎樣發育為嬰兒,如何生長為健壯的生命,飛鴻踏雪,幾乎無跡可循。然而,本片力圖情景化再現文學作品的受孕過程,揭示藝術創造的神秘機理。
為此,本片確認了攝影美學:
①土地山川
土地之寬厚,山川之壯麗,季節之峻美,非航拍不足以完成表達。航拍不是空洞的山水風光,而是準確描述作家身后的獨特地貌與風神。特別是從空中觀看作家在大地山川上的活動,作家仿佛故鄉土地上一棵行走的樹,一株活動的莊稼。
②還鄉場景
還鄉是本片的核心內容,全部采用長鏡頭跟蹤拍攝,捕捉作家在還鄉過程中的情感悸動,眼神閃爍,與家人、朋友、鄉親的交流,童年生活場景以及文學現場。盯住現場,發現現場,還原現場。
③文學意象再現
文學意象再現采用蒙太奇方式拍攝,突出意象造型與象征,并通過剪輯打通現實與虛幻,制造亦真亦幻的藝術效果。
3. 《文學的故鄉》制作關鍵詞
劇本。劇本是本片的基礎,結構、觀點、故事、表達都要在劇本里盡可能體現。所選作家的主要作品我大多讀過,但面對如此龐大的專業閱讀,我依然分身乏術。于是,青年作家楊栗應邀加入劇組,她承擔賈平凹、莫言、畢飛宇等作家的劇本工作。事實上,這三位作家的拍攝基本上按照劇本進行。拍攝之前,與賈、莫兩位老師溝通了劇本大綱,得到基本認可。畢老師更是直接參與了劇本策劃,從結構、意象、場景甚至到一些有趣的細節。唯一的遺憾是他不愿意回到出生的村莊。
但另三位作家卻是不同的風景。遲子建不愿按照劇本拍攝,她建議邊走邊拍, “隨便都夠編50分鐘了”,她表示可以做個副導演。劉震云客氣地表揚了一番,然后建議放棄劇本,跟蹤紀實拍攝。阿來則不太關心劇本如何, “就按照你的想法拍吧。”事實上,這三集在后期編輯中所付出的功夫數倍于劇本拍攝。
敘事。莫言在諾貝爾頒獎禮上演講的題目是《講故事的人》,作家就是當代說書人。那么,作家的故事誰來講述?最初的劇本帶有解說詞,甚至《賈平凹》集就是按照這一思路拍攝的。然而,拍完賈平凹采訪,我立即意識到,應廢除包治百病的解說詞,讓作家第一人稱講述自己的故事。賈老師的陜西話自然親切,講到精彩處妙語連珠,表情生動,瓦解了照片上嚴肅緊張的刻板神情。我意識到,作家才是最優秀的故事講述者。于是,清退解說詞,屏蔽標識時代特征的歷史影像, 《文學的故鄉》放棄宏大敘事的沖動,回歸單純的個人講述。
象征。《文學的故鄉》希望為每位作家找到一個意象,既有現實邏輯支點,又具象征意蘊,從某一角度提煉作家的精神氣質。《莫言》集篇里反復出現的是一位民間說書藝人,他在田間地頭、橋上樹下擺出小鼓,用高密茂腔、山東快書、西河大鼓演唱莫言的打油詩——藝人說莫言,莫言說文學;賈平凹篇里,一位農民在油畫般層層疊疊的遠山前鋤地,迎著日頭,步步向前——賈平凹曾說“我是農民”。而其余四位作家則提取一組象征性動作,本人出演:水鄉的畢飛宇駕一葉小舟順流而下,沿途遭遇小說里的人物青衣、玉米、端方,最終到達一片浩瀚的水域,每次都從水轉場;北國的遲子建乘坐馬爬犁越過雪原,越過歲月,駛入文學的冰雪根芽;山地的阿來從出場到結尾一直行走——他就是一位大地旅人,走過山原,走過河流,走進文學,行走是他與世界交談的方式;劉震云則是兩種意象的交叉:人群里的劉震云侃侃而談,發表演講、接受采訪;獨處的劉震云靜默,讀書,寫作,思考,媒介里的名人與生活中的作家,兩幅側影。
背景。一幅油畫,背景往往是郁積的油彩,前景是人物。小說亦然。遲子建說, “我筆下的人物出場的時候,他背后像馱著一架山。”是的,每位作家都背負著自己的大地山河,草木四季。紀錄片應該呈現每位作家最貼切的背景和季節。遲子建的故鄉矗立于冰雪北國,雪野,白樺林,冰封的黑龍江和松花江。阿來的故鄉盛開在夏季,從草原、森林、灌木到草甸,大地的階梯(借用阿來語)逐級升高,每升一級就上演不同的地理形貌、植物花卉。賈平凹的商州隱藏于山勢連綿的秦嶺,劉震云的延津停泊在一馬平川的黃河邊,畢飛宇的故鄉是水盈盈的河網、黃燦燦的菜花,莫言的高密則是四季變幻的容顏,從紅高梁、黃小麥、綠玉米到一片蒼茫的原野。
紀錄片里的風景不是形容詞的華麗堆砌,而是人物活動的真實舞臺。
再現。再現是局部的,節制,素樸,且是意象化處理,卑微的愿望只在為觀眾提供一個進入歷史和文學的影像通道。
莫言的再現主要是童年時代,這是莫言文學的支點,卻無任何個人影像。為了原汁原味地再現,我們從莫言村莊里找到一位少年,酷似《透明的紅蘿卜》里的小黑孩,草叢中放羊,谷地里抓螞蚱,一人游蕩于田野上,背景避開了現代文明的所有元素。
《文學的故鄉》是一部紀實與想象交織的作品,呈現的不僅是物質真實,更是心理真實。伏案寫作幾乎是所有作家的公共姿勢,紀錄片里的寫作場景展示的只是寫作環境,但真正的創作發生在心里:情感與思想的搏斗,想象與創造的糾纏。如何把一位作家的內心戲劇呈現在畫面里?我們不惜冒犯傳統讓幻象開進紀錄片。阿來走進官寨,遇見小說里的土司。畢飛宇駕一葉小舟,沿途遇見小說里的人物。為了拍攝青衣,舞劇《青衣》演員、著名舞蹈家亞彬專程趕到興化,小橋上、菜花田,留下兩場實景舞蹈。
這是蒙太奇真實,不是長鏡頭真實。
這是心理再現,不是真實再現。
4.現場
紀錄片的現場是神圣的。用影像建構一個完美的現場,是紀錄片的最高境界。現場跟蹤拍攝要求攝影師具有“三到”真功:眼到,心到,手到。關鍵是三到同時到,發現的同時想好拍攝方法,并用攝影機美學地、準確地捕捉下來。這不僅要求攝影師技術熟練,觀察細膩,反應靈敏,而且需要高度人文修養與美學積淀。我把攝影師分為三個層次:用手拍攝的,技術熟練,章法分明;用腦袋拍攝的,新穎別致,影像奇崛;用心靈拍攝的,物我一體,自然圓融。《文學的故鄉》里,攝影師大飛基本上實現了三到拍攝。假如說剛開始的紀實場景還略顯慌亂,那后來的拍攝則越來越嫻熟自然,甚至紀實里帶有表現的味道。
我堅持請求每位作家回故鄉,就是希望作家重返現場,回到真實空間,情有所動,心有所感,觸發自然而內在的反應。《文學的故鄉》里最珍貴的正是現場捕捉的影像。莫言回到家里,用高密話請95歲的父親去縣城過生日,父親堅決拒絕。莫言又說又寫,反復勸解,父親才勉強同意,卻突然問道:家里還有饃,還有煙,要不要帶上?賈平凹走進秦嶺深處的村莊,看見炊煙升起的房子,三句兩句便與一位農婦拉上家常,走過去幫著炒菜,仿佛鄰家大嫂。遲子建回北極村,一見白樺林便情不自禁地躺在雪地上,全然忘了零下40度的極寒天氣。春節前夕,阿來回到馬塘老家,久未見面的媽媽喜極而哭,把頭倚在兒子肩上。天黑了,一家人載歌載舞,阿來也興奮地又唱又跳。痛飲狂歌之后,他沙啞地說,“我剛才我拉著我媽手,我都流淚了。我從來不是這么脆弱的一個人,我是個男人啊!但你說鄉愁這件事情,你經常地回去,它就不是鄉愁。我覺得我家鄉很美好,但是你讓我留在這兒,我不愿意。”劉震云回到老莊,碰見一位養雞的老步,老步當即表揚劉震云在北大的演講好,關鍵是收尾收得好,又回到了吃的。
最有戲劇性的是畢飛宇。他原本不愿回到出生的村莊,擔心情緒失控。無奈只好找一個相對古樸的村子拍攝。然而,畢飛宇在村里漫步一圈,默默不語,若有所思。突然,他扭過頭說, “還是去楊家莊吧。”楊家莊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一個模擬空間里,他找不到自己的童年。魯迅先生說,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信哉斯言1
30年別離模糊了畢飛宇的記憶,他努力打撈起來的只是無法拼接的碎片。左問右尋,在一片河灣前,他確定記憶的版圖,卻無法印證。他疑惑地四處打量,突然拍了一下腦門, “啊”的一聲轉過頭去。攝影機監視器里,畢飛宇從特寫走到中景,男子漢寬厚的背部微微抖動。攝影師大飛一動不動,穩穩地盯著背影,唯有鳥兒自在嗚叫。長達一分四十秒的靜默之后,畢飛宇轉過頭,擦了一下發紅的眼圈說,“就是這兒”,走出畫面。順著他走去的方向,我看見四個生銹的鐵字:楊家小學。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小學對面是木匠家,畢飛宇自稱5歲前幾乎長在這兒。家里沒人,他屋里屋外轉了一圈,準備離開,一個影子從胡同深處緩緩飄移。鄰居說,啞巴回來了。啞巴是畢飛宇的童年玩伴。他迎上去,握住啞巴的手,一起走進家門。啞巴嘴里發出單調重復、含義不明的聲音,不時用手指點墻上相片里的木匠。畢飛宇用手比畫著,啞巴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無法確認。這是一場沒有語言的交流,仿佛默片電影。作為一位老紀錄片人,盡管并不驚奇,但我依然要重復一句:生活遠比舞臺更有戲劇性。戲劇是可以導演的,生活沒有導演。
事實上,阿來幾乎所有拍攝都在現場進行,包括訪談:在草原上說青年時代的漫游,在梭磨河邊說當年的詩人歲月,在土司官寨說《塵埃落定》,在森林說《空山》,在海拔4400米的山峰講他即將著手的小說《植物獵人》。連惠特曼的詩歌都是在草甸的晨霧里朗誦的。
現場無法安排,無法調度,也不可預測,但現場最富于情感張力與戲劇效果。現場把紀錄片的根扎進土地。
5.拍攝
《文學的故鄉》拍攝六位作家,按照工業化制作模式,應該至少三個導演組,分頭并進。但最終我還是選擇了最原始的手工作業方式,一個導演、一個攝影從頭拍到尾。六位作家,六座巍峨高山,我要一座一座攀登,品味,思索,留出足夠的耐心、韌性與節奏。從2016年4月啟動,到2018年5月完成后期制作,歷時25個月。這并非我紀錄片生涯中制作周期最長的一部作品,卻是我個人投入心力最多、耗時最長的一次審美之旅。兩年時間里,我殘忍地拒絕了幾乎所有講學、開會、評獎乃至聚會的邀約(包括我曾答應又爽約的,這里再次向朋友們致歉),全身心沉浸在《文學的故鄉》里。這種緊張、焦灼、興奮與疲勞交織的純粹時光沉淀為生命里一道深深的刻痕。
我們的攝制組是一支美學收割隊,從零下42度的北極村,海拔4400米的巴郎山,油菜花盛開的蘇北水鄉到高梁紅透的高密東北鄉,秦嶺深處,黃河岸邊,一路收割現場,收割季節,收割美學。
多數拍攝是跟蹤式。《文學的故鄉》開機堪稱閃電式。從溝通、決定到趕赴現場在一天之內。第一個拍攝的是劉震云,他正忙于電影《一句頂一萬句》的首映,去西安參加絲路電影節。通完電話我立即召集攝影組,當天到達西安。所有活動都由電影節安排好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新聞記者一樣抓拍。然后跟隨劉震云五天四城拍路演,大飛真的忙飛了。莫言去煙臺長島、龍口一帶故地重游,在快艇上、景區與當年軍營舊址,我們一路跟蹤拍攝。分開陪同的熱情人群已屬不易,跟上莫老師軍人式的步伐更是緊張,大飛幾乎一路都保持了百米沖刺的速度,趕到前面尋找攝影角度,把跟蹤紀實拍出構圖與節奏——因為我不喜歡黑乎乎、晃悠悠的跟腚派。莫老師感慨地說:日本NHK來高密拍攝時我覺得就很敬業,沒想到你們的團隊更認真。
即便作家專程接受拍攝,跟蹤紀實也是高難度動作,因為所有現場都不可能擺拍。遲子建回北極村舊居與新住戶交流,畢飛宇回中堡鎮老街,偶遇許木匠,木匠認出之后伸出熱情的雙手大喊“畢飛宇”,如果沒有抓拍到就會永遠錯過這些場景,即便排練都無法重現。巴郎山,爬上海拔4400米高峰,還要搶拍阿來尋找植物的場景。這些情景來不及構思,大飛憑本能的直覺和豐厚的經驗準確、細膩、美學地捕捉下來。
莫言老師開始接受拍攝時就說,作家不是演員,不能讓作家這樣那樣。我并非擺拍的仰慕者,但拍作家僅僅限于物質表象的紀錄是不夠的,要傳達精神氣質,意象鏡頭無法缺席。而意象鏡頭需要造型,需要光影,需要調度。為此,我不得不請作家像演員一樣走來走去。好在莫言老師諒解我們的苦衷,從紅高梁小橋、玉米地到荒草萋萋的膠河河床走了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拍到后來,每次講完之后莫言老師都會主動說“我走一圈”。最神奇的拍攝發生在高密楊林,我稱之為美學森林——恰如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筆下“象征的森林”。秋天的陽光射進密林,莫言老師踩著金黃的落葉悠然漫步,詩興大發: “藍天白云,陽光燦爛,這不正是詩歌的境界嗎?”午后一團濃云掠過,雨雪霏霏,白茫茫一片化境。一天之內,我們捕捉了楊樹秋冬兩季容顏。紀錄片里,我把陽光和雪景交叉剪輯,配上莫老師講述“文學故鄉”的畫外音,季節交替、情景交融,莫言老師甚為滿意。拍攝一月之后,高密的朋友發來照片,楊林砍伐一空,空茫茫大地真干凈。
造型鏡頭拍攝最辛苦的是遲子建與畢飛宇。
馬爬犁是北極村民俗表演項目,原來卻是林區的主要交通工具。借用馬爬犁的意象,讓遲子建駛回童年,駛入文學。拍攝那天早晨,零下40多度,羽絨服如同單衣,攝制組每人都配備了專業御寒服,攝影機也貼上曖寶寶。遲子建一來就把爬犁上的被子換成野草,車夫鞭子一甩, “駕”的一聲,白馬快跑,身著紅色羽絨衣的遲子建成為雪原上一道流動的風景。大飛乘坐另一輛馬爬犁,捕捉奔跑中的遲子建,又躲在樹林后拍攝林中移動的馬爬犁,接著又同車拍攝近景。速度就是溫度,馬的奔跑鼓動如針的風毒辣地刺向遲子建。兩個小時過去,遲老師的臉已經皴了一片。我宣布馬爬犁拍攝到此結束,可遲老師看見大飛意猶未盡,毅然決定再來一條。北極村3小時高寒拍攝最終在影片里濃縮為48秒。
為拍攝畢飛宇劃船遇見小說人物,我們選定的一條小河流經大片油菜花海,穿過簡陋的小橋,伸向一片浩瀚的水域——這個意象準確裝載了文學隱喻。我請畢老師自己劃船,但他并不自信——畢竟40多年沒碰篙了。趁大飛和我實地偵查小橋的工夫,畢老師悄悄操練身手。待我們歸來,他宣布已經找回了舞水少年。對于水鄉人,水不僅流在河里,也流在血液里——畢飛宇如是說。
拍攝開始了,畢飛宇手持長篙,左右逢源,身體應和著水的律動,節奏悠然,小舟緩緩游動。對著攝影機鏡頭,向左看,向右看,向小橋上看——看想象中舞蹈的青衣。當無人機飛起,大片油菜花迅速后退,畢老師劃船駛出河道,駛進一片遼闊的湖面。
劃船并不是最折磨人的事業.揚州大學的拍攝才稱得上一次考驗。在當年的教室,大飛設計了一條一分四十三秒的長鏡頭:畢飛宇從樓道走進,路遇一位女生,到教室門口攝影機進屋,穿過書架看見一位正在看書的大學生,窗外,畢飛宇向書架張望。攝影機穿窗而過,轉移到畢老師身后,畢飛宇看見大學生的背影從樓道遠去,抬腳走出小樓。教學樓連接了兩段人生,今日畢飛宇仿佛看見自己青春的背影。拍攝難度首先在于三個人物的復雜調度,速度、節奏、眼神與攝影機的配合;其次,攝影機穿越布滿鐵欄桿的窗戶,里外兩位攝影師需要無縫對接;最后,鏡頭一氣呵成,全程手持拍攝,焦點、光線、景別、運動,任何一點疏漏都得重來。第一條,女生慢了;第二條,男生快了;第三條,攝影機穿窗時碰了欄桿……后來,畢老師告訴我,拍到第三條他已怒火中燒,好在他自己帶了消防栓,依然一條一條按照調度拍攝,直到第七條完美無缺。看了成片,畢老師說:長鏡頭最好。
拍攝的日子,凌晨4點等日出,深夜1點倒素材,都是家常便飯,每天還要看罷素材才能休息。散會了,大飛還有自己的功課要完成:健身。年輕的攝制組始終保持著激情和斗志。
從2016年9月18日開機,攝制組六下高密,三赴馬爾康,兩去商洛、延津和興化,多次在北京、上海、南京、揚州、濟南、煙臺、成都、西安、廣州等地拍攝,并遠赴日本、美國、法國、瑞典,采訪30多位國際學者和翻譯家、出版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直到2018年4月27日補拍劉震云一場,歷時一年七個月,實際拍攝時間超過220天。
我們一直在路上。
6.后期
后期制作從2017年夏天正式開始,至2018年5月最后結束。
結構。
六位作家,除了第一人稱自述之外,規定動作很少。為每個人找件合身的衣服,成為后期最重要的工作。
《莫言》集和《賈平凹》集在劇本階段就定下了結構,采用順敘方式,基本按照時間推進人生故事與文學發展。
《畢飛宇》集和《遲子建》集采用復線敘事,明線是現在進行時的回鄉之旅,暗線為文學創作的發展。
《阿來》集則采用戲劇化結構,開篇便是30歲人生抉擇,順敘講文學創作到現在,然后再回溯成長,最后又回到現在進行時,講述即將開始的創作。
《劉震云》集的結構則全然放棄時間線,按照空間進行結構,一是世界的、媒介的空間,作為名人的劉震云;一是鄉村的、獨處的空間,作為作家的劉震云。劉震云在小說結構上異常用心,看片時剛剛轉入第三個段落,他回頭說了一句:“結構的力量。”
節奏。
結構是骨架,節奏是靈魂。
節奏包括段落與段落之間的大節奏,與段落內部的小節奏。每一個現場、每一組素材里都沉睡著一種節奏,但從散亂的紀實素材里提煉節奏,猶如從石料中發現雕塑。比如阿來拍攝植物的段落,內容很精彩,但粗剪效果卻冗長,沉悶。經過反復研究,發現這一段落缺了敘事的推進,只剩細節,便嫌重復。于是,把阿來開始拍攝、逐步認識植物、植物與文學的關系到最后決定寫關于植物的小說理出一條敘事線,再加上烏云暴雨、路邊野餐等環境、細節鋪墊,這個段落就變得跌宕起伏,節奏生動。敘事是核心推動力,而細節從屬于敘事。再生動的細節如果不能置于敘事鏈里,也顯得蒼白。
聲音。
《文學的故鄉》突出紀實氣質,聲音上以同期聲和音效為主,音樂輔助敘事,渲染情緒。音樂統籌王同為本片貢獻了智慧,基本上實現了音樂與文學的融合。但遺憾也是明顯的,本片音樂主題比較含混,辨識度較低。
特效。
《文學的故鄉》的文氣如何呈現?從包裝、字幕到片頭題字,我們做了一點探索。《文學的故鄉》片頭由莫言老師題寫,書法古樸而生趣。關于片中引用的圖書、雜志,我們借用竹簡形式制作了竹簡包裝板,并將竹簡與每位作家的地理結合,如遲子建的竹簡鋪在雪地上,阿來的竹簡鋪在草原上。人名條也用竹簡,每位作家的名字請書法家鄧寶劍書寫。原來設想小說段落都用書法表現,也請寶劍兄創作了一些小說片段的書法作品,但最終只有莫言篇里采用了書法,其他作罷。因為央視規定片中不能出現繁體字,而簡體字的書法效果又值得憂慮。
7.溝通
感謝參與本片的六位作家,他們付出了真誠、時間與智慧。假如本片確有值得牽掛之處,我相信那是作家和作品的魅力。
遠離文學20多年,我已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也與作家素無來往。于是,我邀請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張清華教授作為總策劃。清華兄器宇軒昂,俠氣凜然,茂密的胡須與卷曲的頭發渲染著詩人氣質。簡單溝通,一拍即合,很快形成了最初的拍攝名單。
然而,最初的協商是艱難的。我的紀錄片需要占有作家的時間,必須回故鄉回文學現場拍攝,接受采訪,但作家未必需要紀錄片。《文學的故鄉》所選的都是名家,忙碌是所有名人的共同特征。何況,有的作家習慣于隱藏在文字背后指點江山,不愿意暴露在鏡頭前。
懷著崇敬的心情,首先聯系莫言先生,但他委婉地拒絕了:“待有了新作品再說吧。”我理解,多年來,莫言老師不接受任何紀錄片拍攝。
感謝賈平凹先生帶著他的商州第一個接受拍攝,給了我最初的信心。這得力于西北大學張阿利教授的運籌協調。但人選依然遲遲難定,清華兄親自出面,善為溝通,劉震云、阿來兩位比較爽快地答應了,但畢飛宇在第一次通話中上來就說,“我沒有鄉愁!”當我闡述完對文學故鄉的詮釋后,他才表示接受拍攝。遲子建猶豫良久,直到秋天才勉強應允, “那就拍拍我身后的那片土地吧。”
此時,9月進入下旬,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森林即將落葉,高密的高梁已然紅透。不管莫言、遲子建是否同意,先讓大飛去采集額爾古納河的五彩林,收割高密的高梁,然后直奔興化種水稻。
不久,清華兄告訴我,莫言老師終于接受拍攝。我知道,這是他不懈努力的結果。于是,11月我們跟隨莫言老師拍攝他回高密為父親祝壽。
六位作家確定了,但安排拍攝依然艱難。出國、開會、寫作以及名目繁多的社會活動擠爆了日程表,為拍攝專門留出時間顯得過于奢侈,何況還得考慮季節、天氣等元素。能跟拍作家自己的活動盡量爭取,像莫言去濟南參加歌劇《檀香刑》的活動,劉震云為《一句頂一萬句》電影路演;必須單獨安排的拍攝帶有明顯的妥協性,在作家活動的空隙見縫插針。2016年秋季拍攝賈平凹,從10月一直約到11月,那一年但凡賈老師有空時商洛便秋雨連綿。2017年春節前拍攝了遲子建,湊了她回家過年的機會。從北極村直接去馬爾康拍攝,也是阿來春節前看望父母,但時間只有三天,回到成都已是大年三十。第二次拍攝阿來是翌年7月,從高山到草原,追隨花的蹤跡,這一次拍攝充分。2017年清明節是一次接近理想狀態的拍攝,春水泛綠,大片油菜花燃燒似的綻放,長達兩周的時間,畢飛宇幾乎全程陪同。劇本里所有設計都已實現,而劇本里沒有的紀實現場燦爛盛開。7、8月去山東,跟隨莫言去煙臺故地重游,又借他回鄉休假之際,拍攝紅高梁小橋、紅蘿卜的滯洪閘、城關小院、鄉村舊居。甚至莫老師已然同意去蒲松齡故居一行,但想到此行出現在影片里不過一分鐘,我克制了自私的愿望。9月去美國拍攝。10月赴日本、歐洲拍攝。11月拍攝劉震云回延津,多次約、多次變,終于回到老莊。至此,主體拍攝基本完成,零星拍攝一直持續到2018年4月。
拍攝開始時,我帶著小說尋找文字背后的土地。
拍攝結束時,我捧著泥土品味小說背后的意蘊。
8.作家的生成
我相信,每一位作家都是被命運選擇的人,作為一片土地的代言人。天賦是生命的基因,命運是生活的安排,性格是內心的驅動,土地則是文學的舞臺。所有這些因素集中呈現于童年,甚至可以說,童年決定了一個作家的基本走向。饑餓、孤獨與屈辱使童年莫言看到了人性的底線,體驗到自然的力量;父親的遭遇讓賈平凹感受到世態炎涼,體會了世道人心;漂泊的故鄉和野性的童年賦予畢飛宇敏感與好奇。這迫使他們尋找自己的方式面對世界,正如馮至先生談到奧地利詩人里爾克時所說的, “他呢,赤裸裸地脫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來觀看。”(《里爾克——為10周年祭日作》)。脫去文化的衣裳便是拋開前人的俗套,睜開原始的眼睛正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發現。由此,劉震云在一位河邊梳頭的農家女身上發現推動歷史的力量,開啟了寫作之路;莫言在小黑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釋放出未被文化腐蝕的感官世界,讓習慣了“文學經驗”的人耳目一新;阿來在土司傳奇里體味出人性的秘密,講述了一個陌生又溫潤的故事。
文學是土地的吶喊。法國作家巴爾扎克曾說, “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沉重深厚的土地,傷痛殷殷的土地,埋葬了祖先和災難的土地,堆積了太多流血的傷口和苦澀的記憶,堆積了厚厚的話語土層。與其說作家選擇了土地,不如說土地選擇了作家——高密東北鄉選擇了莫言,秦嶺商州選擇了賈平凹。被選擇的人注定要經歷更多的苦痛——不僅生活里經受,而且文學里體驗。幸福千篇一律,而痛苦姿態萬千。是痛苦讓文學溫暖、思考、升華,如同佛祖化身人間色相遍嘗眾生疾苦。文學是從大地里生長的植物,帶著泥土的憤怒、無奈、愛情與心跳,遠勝歷史書里的庸俗概括與肆意扭曲。
9.文學的故鄉
《文學的故鄉》是作家的故鄉,他們把生活的故鄉變成文學故鄉。
《文學的故鄉》也是我的故鄉,從作家的故鄉回到我的文學故鄉。
《文學的故鄉》更是所有人的故鄉,我期待每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文學故鄉。
文學的故鄉,其實就是精神的故鄉,美學的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