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螺絲
張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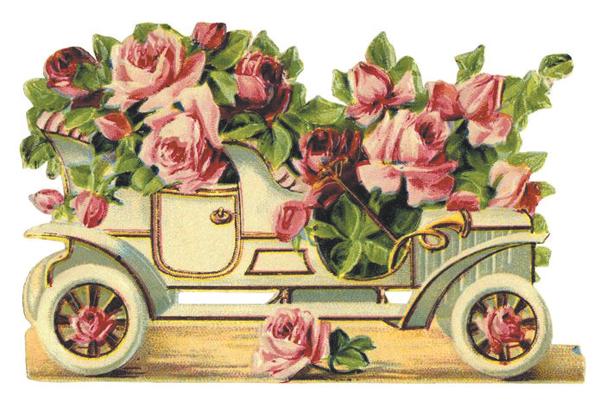
不少作者過去是寫詩的,現在還在不停地寫。因為愛詩,從小就寫,結果怎么也停不下來了。怪不得某人曾經戲言,到六十歲的時候,要成為一個大詩人——能成則成,不能成硬成。
“能成”是說技藝,能力達到了,很自然地成長為一個大詩人,這好理解。但是“硬成”指的是什么?不過是表明了對詩的深刻向往,一種急切到野蠻的追求。
詩是文學的核心部分,整個文學也許還有藝術,由此往外,一點點擴大,到了最邊緣的地帶,就是比較通俗的東西了。詩是人們用來抵抗生命存在的荒謬和荒蕪的一個最有力的武器,它在瞬間閃光,像電光一樣,其強度可以照徹最幽深的黑暗。人的存在是短暫的,要經歷苦難、掙扎和死亡,這中間是與生命誕生之初的全部希望和愿望大相沖突的部分。生命要逾越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礙,一直走到巨大的黑暗之中。生命的存在真的是一次最大的謬誤和虛妄。
人類進入了詩境,就以極大的通透和明晰,表達自己的藐視和反抗。那種瞬間的生命感悟如同閃電,藐視無所不在的可惡的規定,以及一切的陰謀和捉弄。只有詩才具有這種韌性和頑強,有超然的英雄氣概。以詩為核心建立的整個文學王國都具有這樣的意義——越靠近詩,越靠近這樣的意義。
從這個核心開始,通過語言往外延伸,最后與無邊的黑夜連接起來。
詩有一個了不起的作用,就是能夠把詞語的內涵給固定住,不讓其消散和流失,不讓其變形。它用魔法在一個個詞語的邊緣逐一擰上螺絲,不讓其滑脫。文學也正是如此,比如在某個特定的語境里,在某個語句中,如果出現了“感動”兩個字,那一定是極其清晰準確的,這與平常任何時候的“感動”都不一樣。它在那個瞬間語境里的面貌被詩的強光照得一清二楚,不容篡改。真正的文學寫作就是從具體的詞語固定開始的。它會把一個詞語牢牢固定在某一個瞬間,并企圖讓這個瞬間變為永恒。
這正是詩最了不起的地方。
(握里書摘自作家出版社《疏離的神情》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