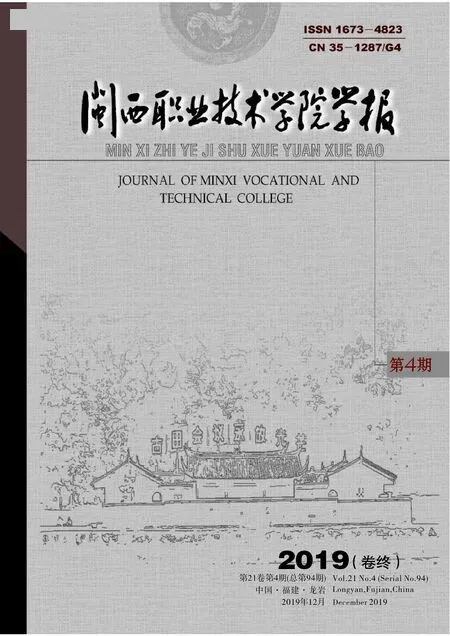任曉雯小說《好人宋沒用》的小人物書寫
邢玉茹
(安徽大學 文學院, 合肥 230031)
《好人宋沒用》是“70 后”實力派作家任曉雯的力作,講述一位蘇北女人宋沒用在上海艱辛打拼、忍辱負重、立足生根的故事。該書2017 年出版后,入選新浪2017 年度中國好書榜。目前,學界對《好人宋沒用》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沒用的形象分析和其所遭受的物質摧殘上, 而沒有將宋沒用的個體存在當作一個有所指涉的文學形象, 缺少對人物精神世界的分析及書寫價值的探討。
宋沒用是作家任曉雯“浮生”系列中的一個小人物,“兩千字意猶未盡,便寫成了長篇”[1]。作家巧妙運用敘事視點、 敘事話語, 細致把握小人物的苦難生活,向讀者呈現一系列小人物群像及其生存狀態,揭開了被歷史遮蔽的小人物坎坷患難的一生。
一、小人物書寫的創作緣起
歌德說∶“我在觀察事物之中, 總會注意它們的發生學過程,從而對它們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2]為了更加準確地理解小說《好人宋沒用》,從小說的創作緣起切入,是很有必要的。 任曉雯認為“即使最優秀的小說,也不過提供了另一個與現實同構的世界,這個世界,往往處理著現實中最卑微、低下、陰暗、扭曲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人們不愿看到甚至可以忽略的。而小說,恰恰照亮了它們”[3]。基于這樣的小說觀,任曉雯有意識地選擇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如漁民、商販、拾荒者、車間主任、癡呆兒童,并施以愛和憐憫的現實主義關懷。 《好人宋沒用》將筆觸伸向蘇北女人宋沒用,主要有以下三重因素。
(一)緬懷親人的夙愿
對于奶奶的緬懷是任曉雯寫作這篇小說的內在動力,“多年來,一位老太太在我腦海中婆娑走動,揮之不散。 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執拗、敏感、心地柔軟。除此,我對她的個人際遇,幾乎一無所知。那時我太年輕,沒能懷著體恤之心去愛她。我虛構了宋沒用, 部分出于對她的緬懷”[1]。 作為創作素材的奶奶,是“驅使作家投入文學創作,對整個創作過程起支配作用的或隱或現的意識”[4], 宋沒用的形象凝聚了奶奶的性格特點及作者對奶奶的情感。 宋沒用為巧娘子一家祈禱,晚年開始理解母親的打罵,種種行為都表現了她心地柔軟的性格。 任曉雯在小說中流露出對宋沒用的同情和憐愛, 也正是緬懷親人的情感訴求。
(二)閱讀興趣的偏愛
個人閱讀經驗、閱讀喜好會影響作家的創作。福樓拜的中篇小說《一顆單純的心》描述了平凡廚娘費莉西泰用愛抵抗苦難的故事, 任曉雯對這部小說贊嘆有加,她說∶“直至很久以后,我才能真正讀懂,為何福樓拜將這位普通農村老太太雞零狗碎的一生,與圣徒(《朱利安傳奇》)、圣人(《希羅底亞》)的經歷并稱為《三故事》。 ”[1]她真正折服于文盲村婦費莉西泰的苦難故事,領悟了福樓拜創作的真諦,積極向福樓拜的傳統致敬,創作由此展開。
(三)關注現實的悲憫情懷
任曉雯不止一次地表達想用小說照亮現實中卑微低下的東西, 探尋普通中國人如何回應苦難與死亡的想法。這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和悲憫情懷,決定了她將筆觸停留在磅礴歷史中的小人物身上。“我們認為現實主義是一種古老的、 源遠流長的藝術方法或藝術原則, 它的首要前提就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真實地反映生活, 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5]《好人宋沒用》就采用了這種方法,將宋沒用置于上海的浮沉歷史,塑造“耳聾,多話,皺皺巴巴”的小人物形象,在展示疲于奔命、艱難生活,一步步實現仁善的小人物生命故事中,關注現實,探討生存意義。
二、小人物的形象建構
(一)小人物群像概述
任曉雯說∶“我寫這本近35 萬字的作品,就是為了書寫一個人,書寫一個叫宋沒用的女人。”[6]作家基于探尋小人物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寫作意圖, 用白描手法掠過風云變幻的幾十年, 聚焦于歷史中寂寂無名的小人物。
宋沒用是貫穿小說的社會底層小人物, 少年喪父喪母,青年喪夫,晚年喪女。在上海疲于奔命,艱難立足。物質、精神的重壓像噴涌的洪水,滾滾而來,此消彼長。擺脫了淪為社會流浪者的不幸,轉身成為傳統舊社會的童養媳;靠生育獲得家庭的地位,又因物質的誘惑和純真的仁善卷入喪夫流浪的厄運; 建國后的物質生活日漸好轉, 卻又因為兒女雞零狗碎的家庭矛盾,徹底從宋梅用變回了宋沒用。
小說圍繞著宋沒用, 勾勒出一系列為生存而忙碌的小人物。為了養活妻兒,愿意干挑夫、更夫、拉糞工、澡堂臨時工、車夫等各種臟活累活,最后在酒精中失去心智的父親榔頭;因為“大丫頭一走,這家就塌了一半”而遲遲不被允婚的大姐[7],身體透支,成為瘟疫的受害者;迫于生計,在“鋼窗蠟地”的花園里弄做姨娘的二姐;孑然一身,飽受饑餓困頓,最后因貪吃拌過氟力酰胺的花生粒, 而瘋癲喪命的大哥宋大福;喪夫喪子,獨自一人守住老虎灶,養育小兒子的婆婆楊趙氏;仁善有愛,卻慘遭批斗的東家佘太太。藝術的根本基點在底層在民間,《好人宋沒用》 挖掘了底層民間雞零狗碎的家庭生活, 藝術地描寫了人們在生活重壓下的百般姿態, 塑造了一幅小人物群像。
(二)小人物的生存狀況
以宋沒用為核心的小人物群體,辛酸是常態,物質匱乏是第一道屏障。 小說中的小人物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因為物質貧困而失去生命的,包括宋沒用父母、大姐和藥水弄的底層民眾;因為物質貧困而道德淪陷的,包括暴力霸占房子的虎頭一家,對宋沒用病態折磨的婆婆楊趙氏, 表面和善內心狠毒的巧娘子一家,打瘸小江陰的宋大福;因為物質貧困而失去自我人格的,包括認為金錢等于親情的戰生、宋大福。物質的極度匱乏使得小人物深陷生存的泥沼, 如何生存成為核心命題。
精神壓迫是小人物生存的又一屏障, 也是最為致命的災難, 主要表現為封建的男權思想枷鎖和錯位的家庭倫理關系。
1.封建的男權思想枷鎖
小說以宋沒用為核心, 展開三代女性的男權壓迫書寫。 宋沒用以及宋沒用的母親、大姐、兒媳都不同程度飽受男權精神的束縛。 母親年逾40, 生育7女3 子,夭折5 個,“渾身關節痛,手指發黑變形,走起路來,拖著兩只扁腳”“大孩子打不動了,就打宋沒用”[7]。母親在飽受生育、生活帶來的身體和心理雙重傷害的同時, 還必須承受丈夫無情打罵和肉體出軌的精神壓迫。 即便這樣,丈夫喝酒發瘋時,母親仍舊嘴硬心軟,悉心照顧。 身為長女的大姐,困于貧困的家庭和父母的私心, 婚姻遲遲不被允許, 正當年華,卻永遠失去了追求愛的權利。 宋梅用的原名“沒用”客觀還原了女性在家庭的卑微地位,為人妻、為人母的她更遭受封建生育思想的禁錮。 宋梅用初次懷孕, 婆婆楊趙氏的態度先后迥然∶“你可得把我孫子好好生出來”“怎么是個女娃, 渾身紫里吧唧的? ”[7]簡短的語言,透露楊趙氏重男輕女的落后思想。 王青華、錢秋妹是新社會的新女性,也同樣逃不過精神鐵蹄的傾軋, 王青華生活在沒有愛情的婚姻中,屢遭懷疑和家暴,父親更是堅定地認為是女人的錯,父權夫權的禁錮加深了王青華的悲劇。錢秋妹因為生育了女孩,而遭受親生母親的冷嘲熱諷、惡語相向。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徹大悟。”[8]正因為難以大徹大悟,精神的壓迫具有延伸性,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往往會循環往復,正如張愛玲《金鎖記》中被封建文化環境荼毒、 變態復仇的曹七巧, 瘋狂破壞兒女的童年、婚姻,從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 宋沒用的母親是舊社會的地主女兒,和榔頭結婚后,不僅沒有享受美滿的婚姻, 反而要忍受丈夫的出軌行為和鄰里的戲謔嘲笑,成為封建文化的犧牲品。精神的毒害迫使她將怨氣轉嫁在兒女身上,不允許大女兒的婚姻,讓其成為負擔家庭重擔的機器; 享受二女兒生活補貼的同時,又對其做姨娘的職業嗤之以鼻;隨意打罵宋沒用,紙錢發霉也不允許宋沒用拿錢買米。長期地位卑微、忍辱負重的精神毒害難以消化,需要以另一種壓迫的形式來疏散, 苛刻地對待子女就是她精神枯竭的外在表現。
2.錯位的家庭倫理關系
錯位的家庭倫理關系同樣筑高了小人物精神壓迫的堡壘。 “家庭倫理,則泛指調整各種家庭關系以及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中與外界有關人員相互交往關系的道德意識、 原則、 規范、 要求及其活動的總稱。”[9]《好人宋沒用》中家庭成員之間的道德意識、原則規范混亂、無章法,家庭倫理關系的錯位,主要集中體現在母女(母子)、兄弟兩個維度的異化、失衡。
(1)異化的母女(母子)關系
“母親一詞,經過數千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識化或本質化了。一提到它,人們就會把它與一些贊頌母性品質的詞匯相連,例如偉大、慈愛、勤勞、養育生命、富于犧牲精神等。 ”[10]而《好人宋沒用》中的母親則冷漠無情,母女關系處于堅硬冰冷的異化狀態。母親與宋沒用、錢家阿媽與錢秋妹、宋沒用與楊愛華這三組母女關系貌合神離、危機重重。母親狠心對待宋沒用,動輒拳打腳踢,自己偷偷買了桂花糕,餿了也不給女兒吃,在母親臨終時,宋沒用終于喊出了壓在心底的“我恨你”。 錢家阿媽與錢秋妹則是一對生育利益捆綁的母女,女兒和兒媳同時生產,在兒媳生了男孩、女兒生了女孩之后,錢家阿媽在錢秋妹面前冷嘲熱諷,炫耀得意,兩人不相往來。當錢鵬程(兒媳生產的男孩)被診治為腦癱后,錢家阿媽又向錢秋妹哭訴,兩人一拍即合,搬回娘家,疏遠宋沒用。宋沒用與楊愛華是新社會的新型母女關系, 宋沒用溫情的小家庭兒女思想與楊愛華沖破小家庭束縛、 擁抱大家庭的思想格格不入,思想的矛盾造成了女兒改名(白蘭改為愛華)、絕食、跳窗、不和母親商量報名去西雙版納、在異鄉慘死的悲劇。
婚姻、財產、下一代等因素導致的母子間隙,是母子關系異化的主要表現。楊趙氏、楊仁道的母子關系因婚姻而漸漸產生間隙, 在楊趙氏看來婚姻就是傳宗接代,媳婦就是任勞任怨的生育機器,而楊仁道則在與宋沒用的相處中產生愛情。宋沒用、楊歡生母子則更加明顯, 楊歡生以犧牲母親尊嚴的方式迎娶了蠻橫嘴碎的錢秋妹,為了居住舒服和日后分房,夫妻倆霸占了大哥的房間,將母親趕進小房間,溫情的母子關系開始解構。第三代人楊怡的出生,加深了楊歡生與母親的隔閡, 孫女的出生燃起了宋沒用對家庭和諧相處的希望, 她希望這個小生命可以幫助散亂的家庭破鏡重圓,但錢秋妹骨子里“江北人低人一等” 的觀念和暴躁善變的性格卻加速了楊歡生母子的決裂。
“家庭屬于社會關系的范疇,最初的家庭是最原始的社會關系,氏族規制出現后,家庭便成為社會關系其中的特殊部分。 ”[9]母女(母子)關系是個人社會關系中的特殊部分,展現個人社會情感的狀況。錯位的母女(母子)關系給雙方帶來精神傷害,個人在毫無感情或感情漸終的親情關系中,飽受疏離和孤獨,懷疑個人價值,思索個人生存方式的合理與否。 《好人宋沒用》中思索無味、被現實包裹的楊歡生,最終成為對母親頤指氣使、 對愛人怨而不敢怒的社會小人物。
(2)失衡的兄弟關系
兄弟倫理關系的錯位主要體現在宋沒用、 宋大福和楊滬生、楊戰生身上。 “兄弟關系是由父子關系派生出來的一種家庭關系, 包括兄弟關系、 姐妹關系、姐弟關系、兄妹關系等。 ”[9]從生理基礎和社會層面兩方面看,兄弟關系應該是相互平等、相互關愛、相互尊重的,而《好人宋沒用》中的兄弟關系卻處于失衡狀態。在哥哥宋大福身上,看到的永遠是無盡的索取和無情的謾罵。
他一掌把宋沒用卡到墻上。 她的頸動脈在她的虎口跳顫。他慢慢松下手來。她憋青著臉,咳嗽幾聲,往旁邊退避。[7]
反觀宋沒用, 雖飽受婆婆楊趙氏的精神折磨和勞動壓榨,但仍舊偷偷地給哥哥送金條,在佘太太家做幫工,也不遺余力地滿足哥哥的需求。“‘我怎會餓死你呢? '她聽見自己說,‘有我一口飯,就有你一口飯。'”[7]宋沒用以德報怨的行為與宋大福的無賴索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兩者不對等的物質給予、精神安慰,加深了兄妹之間的鴻溝,造成倫理關系的名存實亡。
封建男權的精神枷鎖和錯位的家庭倫理關系讓原本就遭受物質摧殘的小人物陷入了精神的困頓。親情疏離,感情淡漠,女性地位卑微,這些精神圍城將小人物圍困在復雜瑣碎的生活中,難以突破。
三、小人物的敘事手法
“一個相同的故事會因講故事的方式方法不同而變得面目全非。 ”[11]在諸多制約因素中,敘事的結構模式與話語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任曉雯以居于歷史的回望姿態,采取了全知的敘事視點、緊貼時代的話語,展現小人物的物質和精神世界。
(一)敘事視點∶全聚焦模式
敘事視點, 即敘述人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敘述故事。 徐岱在《小說敘事學》中,將敘事視點分為三類∶全聚焦模式、內聚焦模式、外聚焦模式。 《好人宋沒用》采取全聚焦模式,全方位把握小說中的人物心理、行為、語言。婆婆楊趙氏生病臥床,宋沒用尋找老中醫的描寫,體現全聚焦模式的敘事優勢。
天色漸暗,宋梅用昏淘淘走到老虎灶,遙見兩扇實心黑漆松木門,鑲了一雙黃銅門鈸,壓著半方磚雕青瓦頂門頭。 她慢下步子,自言自語道∶柳神醫早搬走了,柳神醫不在,等不著他。我沒尋到人,大概地址不對吧。總覺語氣不自在,便坐到路邊,怔怔出神。[7]
婆婆楊趙氏脾氣暴躁,罵罵咧咧,陰謀老練。 對宋沒用來說,找不到柳神醫,婆婆生病暴斃是最好的結局。全聚焦敘事視角的運用,精準地寫出宋沒用內心的真實想法,頻繁變化的措辭,刻畫出宋沒用在道德仁善和陰暗狠毒中掙扎的復雜心理。“宋梅用渾身激靈,清醒了,伸手摑自己一掌,起身往回跑。”[7]敘述者隱藏在簡短的敘述中, 仿佛親眼見到她在掙扎中掙脫,走向仁善的內心世界。
(二)敘事話語∶貼著時代走
敘事話語,指作家在敘事中所選取的表達話語,敘事話語在小說中起到構建背景、豐滿形象、推動情節的作用。任曉雯在處理語言上別具匠心,力求語言貼著時代走, 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小說語言簡潔,善用方言,符合小人物的日常對話習慣,營造出年代感的效果,使小人物書寫更加真實有力。
“70 后”的作家或多或少會受到國外譯作的影響,任曉雯有意識地消化繁復的歐化長句,采取簡潔的、日常的、中國化的表達語言。 “一家商店,一桿路燈,一個小攤子”“老頭六十二了,怕巡捕和乘客看出年齡,黑帽遮臉,只露兩只眼睛”“婆娘不語。 轉頭在孩子們面前嘀咕,‘膽子忒小,還算男人嗎,也就欺負欺負家里人'”“(榔頭)故意拉歪帽檐,抱起手臂,曲一腿,微抖著”[7],小說中的場景、外貌、語言、動作等描寫力求精準,避免繁復,敘事情節綿密但又明快,人物形象特征鮮明。
蘇浙民眾大量移民上海是小說的歷史背景,這要求小說要精確使用不同地區的方言, 前期以蘇北方言、洋涇浜英語為主,后期則以上海話居多。 前期宋沒用的父親榔頭,在丟棄幺女后,跺腳道∶“我一個大男人,難道養不活一個小把戲。”[7]“小把戲”在蘇北話中就表示小孩子。榔頭經常被婆娘罵道“只知道挺尸,怎么不去死”[7],在蘇北,沒有正經工作,愛睡覺不勞作的行為被稱作“挺尸”。 后期宋沒用在上海生活后,就使用了“小赤佬”“男小囡”“女小囡”“囡囡頭”等滬語。方言的精確使用增強了小說的背景色彩,使時代的變遷、人物的沉浮更加真實。
古典字詞和虛詞的巧妙使用, 使得小說語言呈現出年代感。 小說敘事時間始于1920 年,終于1995年, 人物的生活境遇和語言習慣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 小說中的50 年代以前,語言緊湊,古典字詞較多,虛詞較少。 小說中描寫族人遭遇洪水這一片段,“夏杪,起洪水,作物殆盡。仲冬時節,族人聚會。各家口糧歸作一處,反復籌算,只夠吃百來天”[7],運用古典文言字詞,重現了族人聚集商討的畫面,與“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如出一轍。 小說還采用天干地支紀年法,“丁卯年”“戊寅年” 的運用還原了小人物們的歷史生活。 小說中的50 年代以后,語言的運用明顯減少古典字詞, 增加虛詞和富有時代特征的詞語, 透露時代氣息,“眾人跟風哄起來,‘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也有噓噓做聲,‘安靜安靜,讓新娘子講'”“楊戰生說話時,眉毛一聳一聳。他說楊戰生每晚挑燈學習《馬恩選集》,說他挖防空洞最為積極,肩膀被扁擔磨出許多血。有人打了個哈欠,還有人嗶剝嗑瓜子”[7]。虛詞“哄起來”“噓噓”“一聳一聳”“嗶剝”“打了個”的運用,增強了語言輕松舒緩的表達效果, 從中看出小人物在社會時代中的前進。
小說敘事話語緊扣時代變遷,簡潔、日常、精準、巧妙,完善了小說的敘事結構,串聯起故事情節,勾勒出小人物生活時代背景的變化和在時代巨輪下裹挾前進的生存狀態、精神世界。
四、小人物書寫的價值
“文學不是把哲學知識轉換一下形式塞進意象和詩行中,而是要表達一種對生活的一般態度。 ”[12]任曉雯創作《好人宋沒用》就在于探尋小人物“如何回應苦難, 如何看待死亡, 他們靈魂深處有什么秘密”[1],其書寫價值力求在物質貧困、精神壓迫的生活中,彰顯小人物與苦難斗爭的生命韌勁和仁善道德。
(一)頑強斗爭的生命韌勁
“人存在著,其本質必然是悲劇性的;人面對自然, 面對社會, 面對自己, 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甚至不可克服的困境。 ”[13]小說中多次提及小人物的苦難,“人活到這世上啊,不是享福的,是來吃苦的”“活著這件事,好比飯菜端到面前。 再難下咽,都得吃光”[7]。 宋沒用從出生到死亡, 始終與苦難為伴,經歷了家庭暴力、死里逃生、流浪搶糧、痛失親人、子女異心、孤獨終老等種種人生困境,但她卻表現出了驚人的生命韌勁。
宋沒用幼年出去撿垃圾維持家用, 機智記路,“拿筷子的手的方向,不拿筷子的手的方向”[7],甚至與垃圾為伴,想象童年該有的快樂。落入楊趙氏的壓榨圈套,幾次抱怨之后,便開始自我疏導,不記仇恨。被巧娘子一家騙去住房、流浪街頭時,宋沒用完美詮釋了“女子本弱,為母則剛”的真義,通過自己的勞動,換取家庭的生存。 宋沒用不僅戰勝了物質貧窮,而且在精神的高壓下做到了獨善其身。 父輩婚姻的失敗和殘酷并沒有使她對愛情婚姻喪失信心; 母愛的缺失,反而成為她心系子女、家庭的原動力;封建生育思想的侵害,使她偏愛女兒楊白蘭和孫女楊怡;顛沛流離,受盡社會的欺與瞞,卻仍然為巧娘子一家燒紙祈福,相信仁善的佘太太。
(二)迂回堅守的道德仁善
在物質匱乏、精神壓迫之下,如何選擇生存和道德是小人物生存哲學的關鍵, 被生活重壓擊垮走向頹唐, 或是堅定不移扼住命運的喉嚨, 成為雙向命題。 《好人宋沒用》向我們展示了小人物在苦難面前的道德迂回和最終回歸。宋沒用怨恨母親的同時,又同情母親被封建男權和生育思想毒害, 在子女各自為營的晚年,開始理解暴躁善變的母親。婆婆楊趙氏是宋沒用生命中遇到的第二個重要女人, 在婆婆楊趙氏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 楊趙氏平時對宋沒用勞動壓榨、惡語相向、拳打腳踢、人格侮辱,都可以成為宋沒用道德滑坡的最佳借口, 但在生存的極度渴求中宋沒用完成道德的善、惡博弈,幾度掙扎后,宋沒用編織的“沒找到醫生、醫生搬走了”的謊言最終在“一碗飯養恩人”的道德思考中破滅[7]。巧娘子的惡意欺瞞使宋沒用一家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宋沒用安慰自己,搶占住房一定是生活艱難,在得知其一家死于非命時,宋沒用竟然首先憐愛起和白蘭同歲的劉根。
“一個優秀的作家……要在洞悉人生真相后,找尋或創造一種承擔真相的力量, 讓人們在文字堆砌的藝術世界里獲得精神的撫慰,情感的引渡,同時給令人絕望的世界以微弱的抗議和無聲的否定。 ”[14]任曉雯悉心洞察社會,考證歷史細節,還原歷史背景下真實、苦難的小人物生存群相∶如何隨波逐流,茍且存命;如何忍受巨大的苦難,穿過死亡的幽谷;如何在波瀾不驚的外表下,經歷最壯闊的內心風景。在人性的善與惡、生存與道德的精彩博弈中,體悟和沉思小人物的生存哲學, 將宋沒用個人對苦難的忍受和反抗上升為整體意義上的苦難消解。
五、結語
社會不斷發展, 但小人物仍然是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是中國文壇普遍認同的文學對象。對于小人物的描寫,顯示出原始生命與生存的緊密關系。任曉雯始終從小人物的立場來書寫,真實表達身處弱勢地位的小人物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體現出對小人物的同情和關愛, 對頑強生命力的贊揚,體現知識分子對普通人生存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