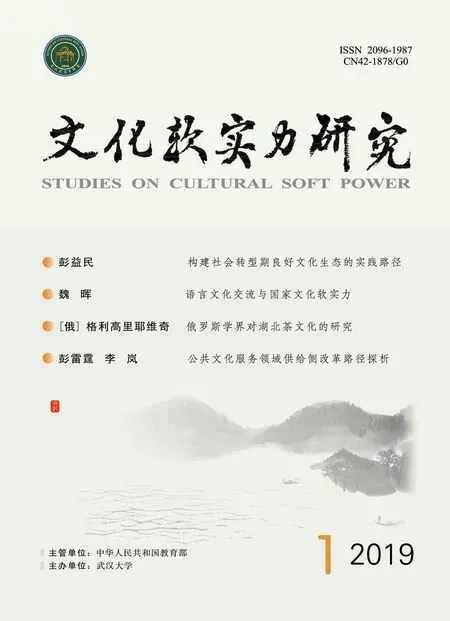匯聚大河文明共謀未來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2018大河對話”國際論壇綜述
吳 濤 張 巍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時強調,“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在2016年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從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看,大河承載著豐富的地理、生物和文化遺產,蘊含著生物和文化的多樣性,為生物群和人類提供重要生命支撐,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但是當前,世界上多數流動水系受到嚴重生態威脅,河流水資源安全性、生物和文化多樣性岌岌可危,迫切需要站在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歷史高度尋求跨文明共識和一致行動。基于這一考慮,由武漢市人民政府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主辦的“2018大河對話”于2018年10月28—30日在長江文明館舉行,來自全球19條大河流域的28個國家、50個組織或研究機構、18家文博單位、28所國內外高校的150余名中外嘉賓出席了論壇。
與會代表和專家圍繞“匯聚大河文明——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未來”這一主題深入研討和交流。論壇還設置以“大河流域管理中的河流文化與環境整合”為主題的高級別圓桌會議,以“河流文化——保護和發展大河自然與文化遺產”“大河沿岸‘水世界’——水博物館遺產記憶地域感”“大河沿岸城市發展——重塑城市與河流的紐帶”為主題的3個分論壇。
一、大河文明與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未來
在論壇開幕式致辭中,弗明·愛德華·馬多克(Firmin Edouard Matoko)指出,“將文化融入全球發展愿景”仍然是人類未來面臨的一大挑戰,這一挑戰最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創意城市網絡”提出;該網絡目前囊括了全球72個國家的180個城市,旨在通過“城市—大河—全世界”的密切合作來培育一種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秦昌威認為,如何應對經濟發展以及人口膨脹對資源造成的壓力,實現對河流的永續利用和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人類在21世紀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也是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必須解決的問題。馬建華指出,古往今來,大河與城市發展休戚相關、唇齒相依;當前,新的治江理念將共抓長江大保護放在壓倒性位置,順應了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有利于促進長江文明取得更多成果,促進流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周先旺指出,武漢素來有“江城”美譽,在長江文明孕育發展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大河對話”將有力地促進武漢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加快建設、清潔、綠色、美麗、文明長江,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為匯聚大河文明提供武漢樣本。
二、大河流域管理中的河流文化與環境整合
在高級別圓桌會議上,主持人歐敏行(Marielza Oliveira)表示,這次論壇第一次將文化、環境、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三個話題聯系起來一起討論,強調通過把城市、文化、大河流域管理結合起來推動可持續發展,這是具有全球獨創性的研討主題。通過這一平臺,在世界大河流域之間、城市之間共推學術研究、分享經驗教訓、加深合作互動,并謀求在論壇閉會期間建立各類對話機制,出臺各種議程,促成未來更好合作。
(一)豐富發展理念,推動多維度的可持續發展
在可持續的人類發展進程中,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環境多樣性扮演重要角色,應予以理解、尊重和保護。殷鴻福以《長江的教訓》為題,警示人們要堅守基本生態紅線,保持長江生態安全,把長江的大保護作為長江經濟帶建設的重要一環。約瑟夫斯·瑪麗亞·布里爾(Josephus Maria Brils)提出,要推動實施氣候變化、水質量、生態健康以及流域管理等方面科研創新項目,以實現可持續發展。胡甲均指出,長江以其豐富戰略資源,為近代工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對中國經濟穩定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作用,要不斷豐富長江理念,以推動長江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張松論述了高質量發展與河流健康的關系,認為當前黃河流域的文化和生態建設正成為流域沿線省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選擇,應借助黃河來提振經濟、弘揚文化、改善環境,為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新活力。
當前,全球對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理解逐步達成共識。其中,教育在保證文化可持續發展、凝聚人口以及社區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周洪宇認為,保護自然與文化遺產,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政府、企業、學校、社會各方面要共同努力,可持續發展教育在保護發展自然與文化遺產中作用不容忽視,湖北民族大學、日本岡山市的經驗值得借鑒。
以時空維度構思重建人和河流的關系,注重過往歷史更繼以及未來合作,讓大河文化支撐人類文明永續發展。李述永指出,武漢大河治理工作將充分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傳承發揚世界大河文明,逐步與大河流域城市建立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推動大河文明研究中心成為大河對話國際智庫,以大河文明名義攜手并進,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更加美好家園。樊志宏指出,要研究河流及其流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來探求其從哪里來、又會到哪里去;通過研究繪制地區文化演進的空間譜系圖和歷史脈絡圖,揭示出武漢留下了連續性的、長時間居于樞紐位置的長江文明傳承足跡,城市未來發展應以傳承創新長江文明為主線,在推進長江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二)搭建流域共同管理、共同發展合作平臺
跨境河流的管理依賴于跨國跨界合作。德拉甘·澤雷科(Dragan Zeljko)分享了河流管理經驗,指出通過成立薩瓦河委員會,統籌各項工作、加強與其他河域管理委員會合作,以此促進多國合作的河流管理。莫西歐·波塞利(Meuccio Berselli)從流域管理機構、流域面臨問題以及解決方法等方面,介紹了波河流域管理經驗,強調人類不僅要使用水資源,更要保護水資源,通過加強跨國合作,努力實現可持續發展。阿卜杜拉希姆·布雷梅·哈米德(Abderahim Bireme Hamid)認為,尼日爾河面臨水域退化、區域經濟文化發展不足等問題,應成立尼日爾河跨國聯盟,促成沿河流域各國共同發展。
加強流域管理、推動可持續發展,離不開流域層面多領域多系統協同互動。賈爾·維埃拉·丹尼斯(Jair Vieira Tannus Junior)指出,巴西生態系統非常豐富,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資源,不僅在國家層面、而且在聯盟層面或市長層面,設有流域管理框架及相應機構,以可持續的方式對水資源加以管理,確保水資源安全和可持續的用水供應。張廣燕介紹了珠江委在流域規劃、防洪減災、水資源優化配置等方面經驗,提出應推動實施流域管理和區域管理相結合、跨區域合作等工作模式。
三、河流文化——保護和發展大河自然與文化遺產
在主旨論壇中,卡爾·萬增(Karl Wantzen)指出,水是萬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人類先祖濱水而居、近水而住,城市文明因水而生、憑水而興;河流為我們供給了生存資源、提供了發展機會,同時我們要意識到并投身到相關風險控制中,對此流域各國及地區政府都要肩負起相應責任。馮天瑜指出,長江流域按上、中、下游劃分,依次為巴蜀—荊楚—吳越三個大的文化區,它們由不同族群在大致相同的時段創造,并在相互借鑒中共同發展,形成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流域文化特征。最新的考古成果證明,長江流域的文明生發決不晚于黃河流域,她滋養并回護著中華文明,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并引領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長江經濟帶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其生態狀況切關大局,“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已成為長江文明建設的新共識。
(一)“從自然學習”——我們如何從大自然學習,以改進河流管理方案和環境技術
河流修復對人與河流關系重塑具有重要作用。生物多樣性是河流生態的重要指標,河流修復要保護好生物多樣性。路易斯·希沙羅(Luis Chicharo)指出,人和河流連接既是一種記憶,也是一種所屬感和歸屬感,更是價值體系體現。應將生態水文學作為工具,促進河流與生態融合。馬丁·布萊特勒(Martin Blettler)指出,河流塑料垃圾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利影響,應通過塑料再利用、使用可替代品等方式加以解決。馬克·葛卓特(Marc Goichot)、伊恩·坎貝爾(Ian Campbell)均以湄公河為案例,指出流域內存在魚類種類減少,沉積物變大增多等問題,建議要開展河道清淤、加大對低壩區域河流環境危害監測等。梅爾塞·馬里亞諾(Mercè Mariano)指出,目前河流面臨過度開發、魚類生物減少、環境污染等威脅,倡議政府、非政府部門和公眾等應聯合起來保護河流。
(二)“從過去學習”——在今天和未來,哪些地方文化可以復興或轉化為河流管理方法
河流會影響人類和自然的關系。因此,重新定義河流的價值和多元性,重新規劃河流與人類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艾琳·克拉弗(Irene Klaver)從哲學角度闡釋“蜿蜒運動和河流圈”原理,認為河流管理涉及物理、工程、意識形態等多個層面,要多維度看待河流與人文的關系。麗貝卡·薩爾姆(Rebecca Tharme)從社會學角度闡釋了環境流動對農業、工商業經濟活動以及民生福祉等方面的影響,認為應通過對環境流動的探索研究,加深對大河流域和文化、經濟等人類活動之間緊密聯系的認知。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與河流正在脫節,傳統文化正面臨消亡。應加強關于河流與人類社會、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探索實踐,進而更好地推動河流保護和文明傳承。安娜·塞拉-廖貝特(Anna Serra-LIobet)以昆卡地區為例,提出要從精神文化層面認識河流,重建人與河流的關系,加強河流保護的公眾參與和研究。安東尼·阿契瓦瓦提(Anthony Acciavatti)通過展示恒河沿岸城市圖片,指出不同河流匯聚代表著人類不同文化匯聚,要認真衡量環境變化新周期,更好地了解季風節奏及其如何影響河流流域的人類生活。帕爾塔·J.達斯(Partha J.Das)以布拉馬普特拉河流域為例指出,河流是一個整體的生態系統,環境污染、建筑物、低壩等都會對河流產生威脅,對水中生物、植物造成負面影響,因此要重新思考河流與人、文化的關系。阿卜杜勒·馬吉德·奧薩馬(Abdel Meguid Ossama)以尼羅河努比亞文化為例,闡釋了河流是如何作為交通要道來促進部落間的溝通和社會習俗的形成,由此佐證了河流與人、文化之間的重要關系。
大河是人類社會文化傳承延續的重要載體。張昌平借助對盤龍城出土青銅器的深度挖掘,揭示出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具有很強的文化共性。張廷皓論述了大運河在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發展歷史中,既是經濟保障帶、內河運輸帶,也是中國東部最重要的財富聚集帶、社會文化交流帶以及人們感情的心理紐帶。
(三)對未來的愿景:人類世界大河的管理
河流是多元化生態系統,保護大河就必須把保護生態系統放在重要位置。赫爾穆特·哈伯扎克(Helmut Habersack)提出,世界大河倡議具有科學性,旨在根據最佳實踐為大河可持續性管理制定創新戰略;要廣泛通過教育、知識傳播、學術研討等活動,提升人們對河流的關注度,加強生態保護。彭靜以長江為例,探討筑壩河流生態保護實踐,指出大河開發應杜絕諸如阻斷河流連通性、改變水文情勢、損害流域棲息地等不利影響,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多層次多舉措管理。馬賽厄斯·康多夫(Mathias Kondolf)指出,規劃建設堤壩要注重總體戰略性,不應建造效用不大且危害河流系統的堤壩、引發泥沙加速沉積的截流工程。
河流生態治理需采用更為科學的方法。洛朗·施密特(Laurent Schmitt)以萊茵河為例,介紹了河流管理相關經驗,認為要通過法律法規控制洪水、通航、農業等,保證河岸穩固,加強河流恢復整治。奧德·贊格拉夫·哈梅德(Aude Zingraff-Hamed)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了未來城市河流恢復應采用的方法,他倡議打造新的評價方法,多考慮生態目標,以期提高河流生態質量。德里克·沃爾默(Derek Vollmer)以珠江為例,認為可通過構建系統的社會生態測量指標,來測度河流以及淡水可持續發展,從而促進相關利益方專注淡水生態健康導向的集體行動。約瑟夫斯·瑪麗亞·布里爾(Josephus Maria Brils)提出,應將海洋學納入全球大河流域研究中,加大氣候變化、人類社會變遷對河流生態系統健康的影響及監測等研究,倡導大學、研究機構、企業家、政策制定機構等共同推動大河流域系統保護。
四、大河沿岸“水世界”——水博物館遺產記憶地域感
在主旨論壇中,埃里貝托·尤利西斯(Eriberto Eulisse)強調,要加強水博物館在全世界的可視性,發揮其連接河流和河流文化的作用,促進水文化回到人們生活中,進而更好地利用水資源,做好流域多樣性保護工作。安來順指出,要把到博物館參觀的公眾,界定為博物館消費者、水文遺產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利益相關方、重要貢獻者,突出他們在匯聚大河文明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水文類博物館必須擔當水文遺產記憶庫的職責、充分反映社會關注的水文議題。
(一)水博物館:講述河流生生不息和水文化復興的故事
現代社會背景下的水博物館,除去應具備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傳播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要以推動可持續性發展為目標,復興文化。張志榮指出,水博物館的關鍵作用是傳承,它既是把多樣地域文化傳播到異域空間、建立文化交流橫向網絡,也是把優秀文化遺產繼承和延續給后代子孫,形成跨越時空縱向渠道和“超級連接”。中國擁有世界規模最大的水利類博物館群落,日益成為國際合作的有力抓手和文化事業發展的創新平臺。張肖雯指出,創新是水文化傳播的關鍵。長江文明館堅持在創新中建設水文化傳播基地、打造水文化展示平臺、開展系列水情教育活動,為宣傳國家水情、展示水利文化、傳承水利文明作出貢獻。塔蒂阿娜·茲米娜(Tatiana Zimina)以伏爾加河為例,指出水博物館展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其傳承水文化復興的重要手段之一。
加快水博物館建設,必須堅持創新包容的理念和方法。雨果·格林菲爾德(Hugo Groeneveld)提出,創新是現代水博物館的重點,要以包容性、自然性為主的方案建設新的水博物館,以創新的手段方式向大眾講述河流可持續性,傳承文化復興,讓現代水博物館逐漸形成一個社交中心。阿爾伯托·埃爾南德斯—薩利納斯(Alberto Hernandez-Salinas)認為,不同地區水博物館具有不同資源與功能,應加強水博物館之間溝通協作,將水博物館之間交流互動上升到國際網絡層面,努力傳播國際水文化。馬西米利亞諾·塔迪奧(Massimiliano Tardio)指出,基于水資源基礎上建立的水博物館應是一個聯合團體,完整的水網絡是保證水博物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水博物館內外:社會河流流域地域感、沿河社區的參與和替代
社會流域反映了河流流域中人的參與,在范圍上不僅包括河流本身,還包括河流沿岸地區社區的參與。寶琳娜·亞烏拉吉(Paulina Jauregui)指出,研究社會流域,要從游客拓展到流域內的所有人和土地空間,要在水博物館中凸顯傳達一個理念——“我們在一個互相緊密聯系的整體中,每個人都應承擔責任”。薩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沙爾維·蘇曼(Shalvi Suman)指出,人在河流流域中的參與作用,人與人的互動、人與社會的互動、社會與社會的互動,都是水博物館應當展示出來的。鄭曉云提出,人類早期文明都是從大河流域產生的,人類受河流影響,其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以此為基礎建立,由此逐步發展為水文化;應建設覆蓋整個河流流域的水博物館,形成完整網絡體系,傳播水文化。莫娜·波拉卡(Mona Polacca)以原住民的視角對水和人的關系進行了闡述,呼吁控制污染,保護水資源。
(三)如何吸引觀眾?從博物館設計、生態旅游規劃,到沿著藍色走廊的休閑與福利
河流河道作為水博物館設計和生態旅游規劃的基礎,與其關聯性最大的是人類群體。馬吉德·拉巴弗·哈內吉(Majid Labbaf Khaneiki)以坎兒井為例指出,以隱形水渠為基礎設計的水博物館,其建筑實體的呈現與渠道方向緊密相關,這是因為水渠位置和走向是解讀城市文化的重要線索,能夠揭示出社會群體、社會階層的分布關系。艾倫·克拉索(Alan Krathaus)、菲奧娜·邁克杰提根(Fiona McGettigan)提出,觀眾參與度應是水博物館設計的目的和重要內容,要激發大眾意識,創造動態水博物館,將人類同當地水道更緊密連接起來。泰瑪·紹爾考伊(Timea Szalkai)指出,水博物館應具有自適應性,在不同展區布局不同教育展示內容;要創造水博物館自身的引導作用,讓觀眾可以在博物館里自我探索。瑪麗亞·羅莫(Maria Romo)以拉雷多水博物館為例,提出水博物館應針對不同人群,提供不同展示方式,以滿足他們的求知要求。
水博物館的設計和運營應采用更多新技術、新方法。阿比蓋爾·維克特(Abigail Wincott)提出,新媒體具有互動性好、空間導向性強等特點,不僅能改變博物館呈現形式,而且還有利于遺產知識在社群中傳播。瑪麗亞·卡里斯托(Maarja Kaaristo)指出,河道的共享價值是由河道居民、河道使用者與城市居民共同建立起來的;在這個共享價值創造過程中,數字媒體能夠吸引越來越多年輕人參與到博物館的建設和體驗中,同時引進更多新技術也會有助于形成水博物館所特有的歸屬感。
五、大河沿岸城市發展——重塑城市與河流的紐帶
在主旨論壇中,卡特麗·利茲斯汀(Katri Lisitzin)指出,任何旨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必須考慮生物多樣性與當地文化背景之間的相互關系;要站在全球高度,順應大城市發展趨勢,重視河流城市所有層面、所有維度的連接性,推動濱河濱水區域開發,讓大河沿岸城市成為重塑城市與河流關系的紐帶。
(一)尋回沿岸城市的傳統和身份認同
把握住大河沿岸城市的傳統和身份認同,對謀劃推進城市發展非常重要。韓鋒指出,沿岸城市身份主要體現在城市發展中展現自身傳統魅力和文化內涵,只有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才能更好地使沿岸城市在現代社會中秉承自身精神、重塑城市新發展。納普·普洛斯·可汗納(Nupur Prothi Khanna)以高止山脈為例提出,應將傳統文化元素注入到沿岸城市中,轉化為城市記憶、運用到城市設計和建設中。胡薩姆·馬赫迪(Hossam Mahdy)認為,河流變化會相應帶來沿岸城市的形態變化,隨著社會進步,河流身份喪失,逐步造成城市與河流的割裂;要在現代社會傳承中重構城市與河流的聯系,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城市歷史發展痕跡加以保護和傳承。陳同濱以良渚古城為例,介紹了以中為尊、追求高聳、濕地應城、臨水而居等城市規劃經驗,闡釋了黃河、長江對文明古城的作用原理,以此表明沿岸城市規劃發展應與傳統文明相呼應。
(二)河流與城市的互動是城市轉型的主要理念
在后工業化發展中,大河流域城市轉型的主要理念與動力來源于河流與城市的互動、依賴于河流的引導。烏韋·布蘭德斯(Uwe Brandes)指出,沿河區域的再生,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河流治理,推動人們有意識地修復沿河自然環境,有利于促進人與人、人與城、人與水更緊密地聯系;河流沿岸城市的規劃發展,應秉持包容心態,綜合考慮沿岸地區的整體發展,推動河流與城市的共生。齊格弗里德·恩德斯(Siegfrid Enders)以德國漢堡倉庫城為例提出,沿岸城市尤其是港口城市發展,要充分依托河流與城市的互動關系,通過城市設計和空間結構改造,傳承城市內在精神特質,為城市發展不斷增添新功能。阿提拉·杰爾(Attila Gyor)介紹了布達佩斯城重建過程中圍繞河流所做的工作,堅持維護城市古老形態,規劃建設更多橋梁以及藝術、科學、文化等河畔中心,增強城市和河流的互動性和匯聚力。索菲·阿列克林斯基(Sophie Alexinsky)以巴黎塞納河沿岸港口重建為例指出,將小港口能動地聯結起來,讓市民更多參與重建,有助于讓城市轉型達到最好效果。邵甬以上海黃浦江、蘇州河發展規劃為例,介紹沿江沿河城市治理做法,指出應堅持以人為本、文化與生態結合等理念打造城市濱水區,促進河流與城市融合發展。
(三)城市河流景觀綜合性開發手段
在城市快速擴張、環境惡化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城市河流景觀在迅速退化。制定實施統籌考慮河流與城市的綠色發展戰略,推動大河文化融入基于社區的城市河流景觀改造工程,是城市河流景觀綜合性開發的重要路徑。尼古拉斯·戈德雷特(Nicolas Godelet)提出,水生態直接塑造了城市生態景觀,讓水與城市、與人類居住區直接對話,將促進城市更加綠色、實現循環發展。米凱拉·普雷斯科特(Michaela F.Prescott)以印度尼西亞為例提出,社區參與城市河流景觀開發非常重要,這將利于促進城市居住景觀生態價值塑造及可持續性發展。
推動大河流域城市發展,需要采用更現代的理念、方法和技術手段。森通·略揚(Sengthong Lueyang)以瑯勃拉邦為例,分享了依托保育區、保護區、自然和景色區、實驗區4個功能區實現管理的經驗。林永生介紹了“真實進步指數”研究項目,分析真實進步指數框架中“水元素”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認為城市發展應倡導綠色可持續發展。陳進指出,在城市河流景觀開發中,綠色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它不僅可保證河流的可持續發展,更能為城市發展帶來新的動力。安娜·塞拉-廖貝特(Anna Serra-LIobet)將綠色基礎設施范疇拓展到水資源管理及綠色生態網絡方面。
六、通過“大河對話”平臺進一步開展協調交流與合作
與會代表和嘉賓通過廣泛交流探討,達成了以下后續行動方案及倡議:
大河流域是包含人類、自然和文化維度的復雜社會生態系統,要注重采用更加綜合的流域治理方法,把握好河流和海洋之間、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間的相互聯系,保護好自然和文化遺產;要以“大河對話”為平臺,堅持開放數據、聯合研究,推動國際層面理論研究、政策制定、實務操作等領域協商協調。
今后,將圍繞“2018大河對話”論壇確定的關鍵問題,以長江文明館“大河文明研究中心”為主體,遵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文化及環境項目合作框架,推動實現更多國際層面協同合作。主要包括:參與世界遺產公約、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名錄、創意城市網絡和傳統城市計劃,以及相關教科文組織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能力建設和培養計劃;參與國際水文計劃、世界大河倡議、生態水文倡議和相關人口統計,以及加入全球水博物館網絡等。同時,還將依托“大河文明研究中心”,建立國際科學顧問委員會,推動博物館與社會各界的探討與研究,促進河流城市和河流流域協同管理,確保城市和河流在其流域內更好地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