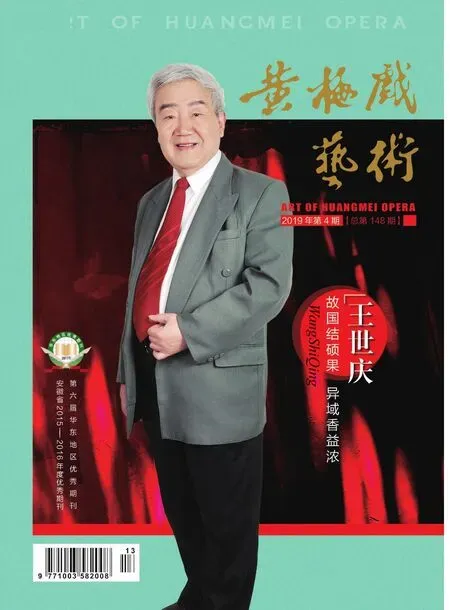此曲原為人間有—— 黃梅戲《玉天仙》觀后
□ 蒼 耳
筆者看過(guò)不少黃梅戲,但《玉天仙》一劇讓我眼前一亮,如見活潑健壯、清眸流盼之處子。我的興奮還有另外的原因。零八年我在《隨筆》第四期發(fā)表“草臺(tái)的命運(yùn)”一文,出乎意料地引起省內(nèi)戲劇界老專家的熱烈反響。該文反思了戲劇史上的“三改”,并對(duì)當(dāng)下戲曲越來(lái)越偏離民間和草根提出質(zhì)疑,提出回歸戲曲本體,回歸民間母體,回歸人性命題。柏龍駒先生從省城來(lái)安慶一定要見我,在東升賓館與我暢聊黃梅戲話題,建議《黃梅戲藝術(shù)》轉(zhuǎn)載這篇文章。一晃十一年過(guò)去了,黃梅戲在回歸的道路上似未見進(jìn)展,倒是看到不少精心打造的“大戲”,因流于說(shuō)教而難獲觀眾青睞。《玉天仙》的出現(xiàn),不妨說(shuō)是個(gè)例外。
《玉天仙》在“三回歸”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而重要的一步。在我看來(lái),回歸戲曲本體方為根本,回歸民間母體和人性命題乃必經(jīng)之徑。
所謂戲曲本體,便是戲曲之為戲曲的那個(gè)特性、程式和韻味,是戲劇性所生發(fā)、激蕩的本源。一部戲像不像戲,看完后直覺(jué)會(huì)告訴你,這個(gè)直覺(jué)便是“戲味”。這類似詩(shī)歌,好的詩(shī)歌必有詩(shī)味。戲味也可以說(shuō)是戲劇性的集中而直覺(jué)的體現(xiàn)。無(wú)戲味,此戲便失敗了,盡管它高大上,路子很正。一旦違背了戲曲之為戲曲的本體性,戲曲性蒸發(fā),戲味從何而來(lái)?經(jīng)典戲劇經(jīng)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注重戲劇沖突,巧設(shè)翻轉(zhuǎn),在劇情陡轉(zhuǎn)或空間并置的對(duì)比中,在雙重身份或雙重面具的張力中生成藝術(shù)傳奇;而在場(chǎng)與場(chǎng)的轉(zhuǎn)換中,唱念做打的細(xì)節(jié)是否精致合理,是否生動(dòng)詼諧,無(wú)不關(guān)聯(lián)戲曲性的強(qiáng)弱濃淡。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李爾王》《哈姆雷特》《奧賽羅》,中國(guó)古典悲劇《竇娥冤》《趙氏孤兒》,黃梅戲《天仙配》《女駙馬》《小辭店》莫不如此。恕我直言,當(dāng)下有些戲連基本的戲劇沖突都匱乏,沒(méi)有跌宕翻轉(zhuǎn)的劇情起伏,無(wú)花臉,無(wú)小丑,無(wú)噱頭,無(wú)風(fēng)土俚俗,一本正經(jīng),不好看不耐觀,戲味從何而來(lái)?
回歸戲曲本體,在當(dāng)下首先意味著去贅化、去繁化。最近三十年,附加在戲曲身上的“贅物”有增無(wú)減,被光電化、說(shuō)教化、美術(shù)化、高科技化,包裝過(guò)度,炫麗成風(fēng),演出成本超高,軀體越來(lái)越龐大、臃腫,不堪其重,戲曲之為戲曲的本體元素反顯暗弱了。僅舞臺(tái)上的布景、道具、燈光、戲幕不斷翻新,越來(lái)越繁復(fù)、奢華,喧賓奪主,且不說(shuō)令任何一個(gè)古代戲班望塵莫及,即便當(dāng)下縣鄉(xiāng)水平的劇院也望而卻步。新編黃梅戲《玉天仙》既無(wú)布景,也無(wú)須換“幕”,僅有兩根粗大而古老的麻繩,道具不過(guò)一桌六椅,場(chǎng)上樂(lè)隊(duì)僅六人。舞臺(tái)中央懸吊一根麻繩,打了兩個(gè)扣,令人驚心;臺(tái)上用一根麻繩圈定一方表演場(chǎng)域,令人意外。可以說(shuō),戲里戲外,角色互換,樂(lè)隊(duì)演奏,皆以繩圈為界。但“麻繩”達(dá)到的效果卻以一當(dāng)十,兼具布景、道具的功能,更有深化命題的象征意蘊(yùn)。同時(shí),該劇人物配置也簡(jiǎn)單,男女主角加上四個(gè)配角,配角兼串屠夫、媒婆和“七嘴”“八舌”等眾多角色,所有角色均不退場(chǎng),成了活的“布景”,讓人想到從前戲班演出的鮮活場(chǎng)景。
事實(shí)上,傳統(tǒng)戲曲和草臺(tái)戲曲之所以生命力旺盛,大受觀眾歡迎,正在于它們化育于民間,也流傳于民間。在現(xiàn)代背景下,戲曲何以要重提回歸民間母體?原因在于民間的豐厚淵深,不僅提供鮮活奇異的戲劇素材,更可以容納藝術(shù)的多元性和價(jià)值的多維性。巴赫金畢生研究中世紀(jì)民間文化及拉伯雷文本,他認(rèn)為,民間狂歡化“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獨(dú)特的‘逆向’‘反向’和‘顛倒’的邏輯,是上下不斷換位如(‘車輪’)、面部和屁股不斷換位的邏輯,是各種形式的戲仿和滑稽改編、戲弄、貶低、褻瀆、打諢式的加冕和廢黜。”說(shuō)白了,民間立場(chǎng)看取事件和事物態(tài)度不取單面、單一的價(jià)值判斷,而是在二元或多元之間保持多維、換位、互否的活力。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同體性,諸如舊和新、盛和衰、明和暗、上和下、丑和美、垂死和新生、靈和肉、始和終,均處于共時(shí)同在、相互循環(huán)的關(guān)系中。原初的傻瓜、小丑乃至魔鬼的形象基本是正反同體,內(nèi)外、智愚、高低、美丑之間的強(qiáng)烈反差并沒(méi)有偏廢一方,而是正與反保持張力,互證互否。愚蠢是反過(guò)來(lái)的智慧,大丑是倒過(guò)去的真美,瘋狂是清醒的極致狀態(tài),悖謬是真理的另類傳達(dá)。在官樣文學(xué)中,傻瓜、小丑乃至魔鬼的形象逐漸變成單面性的了,僅僅成了國(guó)王、君子、英雄的陪襯和插科打諢的工具。
《玉天仙》改編、移植于其他劇種,故事原型來(lái)自漢代朱買臣被迫休妻的野史記載,歷經(jīng)兩千年演繹、流傳,生成難以盡數(shù)的戲曲版本,昆曲、京劇、川劇、晉劇、梨園戲均有此劇目,如京劇《馬前潑水》,講的是朱買臣妻崔氏不甘于生活清貧,逼夫?qū)懴滦輹x婚,改嫁他人。后來(lái)朱買臣中第,出任會(huì)稽太守,崔氏乞求復(fù)合,朱買臣馬前潑水,讓他收起覆水就同意復(fù)合,崔氏因羞愧而撞死街頭。以男主角朱買臣的角度演繹這個(gè)故事,其妻崔氏被塑造成嫌貧愛富、逼夫休婦,最終自取其辱,為歷代所嘲笑、唾棄的可悲村婦。
《玉天仙》一劇拋棄傳統(tǒng)戲曲的單邊立場(chǎng),將男性敘事與女性敘事加以并置,從朱買臣和玉天仙的視角對(duì)等展開戲劇情節(jié),從而在精神取向和價(jià)值觀上形成張力;尤其玉天仙之獨(dú)特視角——通過(guò)她的唱與對(duì)白,痛述一個(gè)鄉(xiāng)村女性的內(nèi)在訴求,將因貧棄夫、改嫁夢(mèng)回、再遭羞辱,以致走向自裁的精神脈絡(luò)展露無(wú)遺,在世人面前揭蔽人性的悲劇尤其女性的悲劇,戲劇性由此得以升華。改編者從傳統(tǒng)倫理和男權(quán)視角解放出來(lái),回歸到多元和多維的民間立場(chǎng),在人性命題上深入挖掘,搔到引發(fā)現(xiàn)代觀眾共鳴的癢點(diǎn)和痛點(diǎn)。
在我看來(lái),這個(gè)癢點(diǎn)和痛點(diǎn),正是男女主角擺蕩于物質(zhì)欲求(物欲)與精神欲求(靈欲)之間的苦苦掙扎。舞臺(tái)上懸吊的麻繩打了兩個(gè)結(jié),可以視為物欲與靈欲的形象暗示。朱買臣和玉天仙并非懶墮、齷齪之人,夫妻倆是良善而勤勉的。然而,朱買臣飽讀詩(shī)書二十年仍無(wú)路受薦為官,食不果腹,衣不暖身,飽受嘲笑,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書生氣鬧出不少酸腐笑話;但面對(duì)赤貧和被離婚,他仍不墜青云之志,繼續(xù)苦讀求仕,這是他廣受同情的重要原因。《玉天仙》保留了這一有價(jià)值的成份。在朱買臣成為朱太守后,他要求從屠夫手中“贖回”妻子以便破鏡重圓,不論出自真心還是報(bào)復(fù),仍可以看出男主角擺蕩在物欲與靈欲之間的掙扎和扭曲。他竭力在世人面前證明自己,他做到了,但得到的無(wú)疑仍是苦果;玉天仙懸梁自殺后,苦果變成了悲果。然朱買臣并不能理解她何以死。正因?yàn)樗欢渌魉鶠榧幢愠鲇趷垡猓踩匀粚⒂裉煜杀粕狭私^路。可以說(shuō),朱買臣被離婚,玉天仙被懸梁,看似不該發(fā)生的發(fā)生了,不該悲劇的悲劇了。這是深層錯(cuò)位的悲劇,更是人性的悲劇。
再看劇作家對(duì)女主角的處理。該劇一反傳統(tǒng)戲曲中那個(gè)嫌貧愛富的“崔氏”形象,寄予這個(gè)弱女子以深切同情。玉天仙并非一心追求大富大貴,而是夢(mèng)想過(guò)上有靈有肉、溫飽而體面的生活。命運(yùn)偏偏讓玉天仙嫁給一個(gè)五谷不分的讀書郎朱買臣,在二十年做不了官的苦熬中,連溫飽也解決不了,以致她身上強(qiáng)烈的物欲摧毀了原本視為高貴的靈欲,逼夫休己實(shí)出于想活下去的萬(wàn)般無(wú)奈。這固然飽受不同時(shí)代觀眾尤其男士們的指責(zé),但玉天仙并非女中精英,她是一個(gè)有七情六欲、再普通不過(guò)的村姑,無(wú)法做到盡善盡美,而這正是人性的普遍弱點(diǎn)或特征。問(wèn)題是,當(dāng)她改嫁給一字不識(shí)的屠夫后卻陷入另一重困境:物欲滿足后,靈欲的饑餓接踵而至,與前夫的感情更是藕斷絲連。物欲和靈欲在她身上極端反轉(zhuǎn),讓人感受到命運(yùn)的戲弄帶來(lái)的戲劇性和強(qiáng)烈反嘲。這何嘗不是人類或者人的基本困境呢?當(dāng)朱買臣衣錦還鄉(xiāng),玉天仙再度被推到物欲與靈欲對(duì)峙的風(fēng)口浪尖。朱太守以豐厚的田產(chǎn),“迫”使后夫簽下休妻書,這讓玉天仙的身心再遭打擊和戲弄;前夫要求破鏡重圓,更讓這個(gè)弱女子處于被人指指戳戳、無(wú)顏立身的艱窘之境。顯然,位于物欲與靈欲之上的更有人格,更有人之尊嚴(yán)。玉天仙最后不是死于物欲得不到滿足,也不是死于靈欲得不到釋放,恰恰是死于得不到做人的尊嚴(yán)——一個(gè)弱女子本應(yīng)得到的起碼尊嚴(yán)。這才是人性的真正悲劇,自然引發(fā)觀眾的共鳴和思考。女主角的人物塑造,分寸拿捏準(zhǔn)確、得當(dāng),對(duì)人性的挖掘尤其對(duì)女性內(nèi)心的展示是成功的。據(jù)說(shuō),“玉天仙”之名并非新構(gòu),而是源自元雜劇《朱太守風(fēng)雪漁樵記》朱買臣之妻名。改編者用此名,大概不僅出于好聽,更為了與“崔氏”相區(qū)別,與女主角的命運(yùn)悲劇形成反諷吧。可以這樣說(shuō),舞臺(tái)上從懸垂著兩個(gè)結(jié)的粗繩開始,到眾人沉重地收攏繩圈終結(jié),該劇完成了一次劇情閉合,也完成一次思之騰躍。
小劇場(chǎng)戲應(yīng)該是介于大劇場(chǎng)戲和草臺(tái)戲之間的戲曲變種。它預(yù)示著未來(lái)戲曲發(fā)展的向度和路徑。小劇場(chǎng)戲固然是小制作,對(duì)創(chuàng)演者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創(chuàng)作上的獨(dú)到精粹和表演上的豐厚精致。《玉天仙》無(wú)疑是一個(gè)良好的開端。擺在戲曲家面前的難題是,遇古則易響,遇今則易啞。似乎一接觸當(dāng)下素材,便棘手了,戲也變味了。想想看,關(guān)漢卿寫《竇娥冤》難道不是那時(shí)的當(dāng)下素材?在我看來(lái),如何從豐富多變的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中汲取素材,打磨出無(wú)愧于時(shí)代的經(jīng)典作品,才是向偉大的戲曲傳統(tǒng)致敬的最好方式,也是加入這一偉大傳統(tǒng)的唯一方式。當(dāng)然,我們有理由期待下一個(gè)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