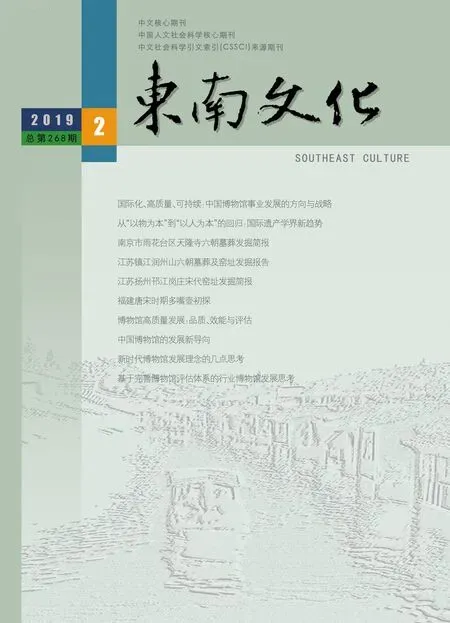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回歸:國際遺產學界新趨勢
馬慶凱 程 樂
(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 浙江杭州 310058)
內容提要:讓文化遺產活起來,是我國文化遺產事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國際遺產學界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探討,跨學科、有反思性的研究潮流正在興起。其總體特點是以人為本,對遺產的物質性與文化性進行整合思考,重新理解遺產,更加重視遺產發揮的作用。其研究主題包括遺產的再理論化、遺產價值、對遺產保護運動中忽視民眾的偏頗進行反思、對世界文化遺產再思考等。國內遺產保護與利用應與時俱進,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讓遺產活起來,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化遺產保護利用之路。
讓文化遺產活起來,是新時代對于文化遺產事業的總要求。習近平同志指出,“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1]。文化遺產活起來的困難在哪里?文化遺產如何才能活起來?遺產事業長期圍繞遺產的物質形態談遺產的保護,客觀上回避了從人本、文化等本質的層次上探討遺產的文化價值[2],遺產在社會中的作用也被限制了。在國際遺產學界,更全面地認識遺產的努力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遺產研究出現了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轉向,匯聚成了“遺產思辨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Critical一詞的含義接近中文里的“慎思明辨”,因此這一研究潮流是對傳統的遺產保護觀念的反思,是遺產研究的新發展。遺產研究不再局限于“如何保護”的技術化探討,為誰保護、為何保護,遺產與記憶和地方感的聯系、遺產的利用成為更受關注的課題。本研究對這一研究潮流進行較為全面的評介,并探討它給國內文化遺產事業帶來的啟示。
一、“以物為本”的遺產觀的形成
現代遺產保護源于歐洲,伴隨著歐洲現代性的出現而興起[3],其特征是“以物為本”,注重對歷史建筑、遺址、文化景觀等物質性遺存的保存。它的興起有其哲學基礎、政治背景、學術背景。
現代遺產保護的哲學基礎是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二元論[4]。這一觀念認為,物質與精神是絕對不同的兩種實體,對于物質,需要進行準確、客觀地研究,以抓住事物的真相。在其影響下,追求客觀性的科學觀念主導了現代遺產保護[5]。薩爾瓦多·穆尼奧斯·比尼亞斯(Salvador Mu ?oz Vi?as)指出,對遺產真實性的需求和對科學知識的依賴是遺產科學保護觀的兩個基礎[6]。前者指的是遺產保護“本質上是基于它的物質屬性和組成成分”[7],追求真實性,即保護的目的是“發現并保存物質對象的真實特性或真實狀況”[8],這是“物質至上主義”的觀念[9];后者意味著遺產保護僅與要保護的物質對象本身有關,需要通過科學原則和科學方法進行,“避免主觀印象、品味或喜好的影響,基于客觀事實和硬數據作出判斷”[10]。在這種觀點下,遺產保護僅與物質對象有關,與遺產相關的民眾被排除在外。
現代遺產保護出現的政治背景是19世紀后期民族國家的興起。文化遺產的觀念為各國提供了特定的起源與進化觀,支撐了它們的國家認同[11]。對此,丹尼斯·班敦士(Denis Byrne)有如下闡述:
過去的“真實的”物質載體被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專家認為有價值,其原因是它們為這幾個學科的研究提供了證據;它們被民族國家認為有價值,其原因是它們是民族國家的象征物。[12]
現代遺產保護的學術背景是,現代學科出現后,部分學科開始聚焦于遺產物質形態,進行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設置了知識生產的邊界,施加限定,塑造認同”[13]。勞拉簡·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指出,自19世紀末以來,考古學、建筑學等學科在歐洲形成后,形成了一套邏輯自洽的話語,認為歷史建筑、遺址等物質遺存具有內在的價值,遺產的價值蘊藏在遺產的物質形態中,遺產是脆弱的,需要掌握技術的專家來保護。這一話語在20世紀被推廣到全世界,一方面使許多文化遺產得以保存,貢獻卓著;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其他群體、其他文化對遺產的多樣化的認識、理解被邊緣化,對遺產的利用也被遮蔽了[14]。這種科學化的思考遺產的方式“把一個我們生活、相愛并且消亡在其中的質的可感世界,替換成了一個量化的、幾何實體化了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任何一樣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獨人失去了位置”[15]。
二、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回歸:遺產思辨研究的興起
進入21世紀后,國際遺產學界、遺產保護界對于遺產的認識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回歸。這并非指遺產的物質性不再重要,而是將遺產放在它所處的社會關系中,重新思考為誰保護、為何保護、遺產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什么作用等問題,對過去被忽略的遺產相關群體給予關注。例如,在遺產地附近長期生活的民眾以及來遺產地與博物館的觀眾,都與遺產密切相關。在“以物為本”的遺產保護范式下,這些群體常被忽視,或者被認為可能給遺產帶來風險。
在國際遺產學界,遺產思辨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正在興起[16]。它提倡具有反思性、跨學科的遺產研究以及不同的遺產實踐方式,關注遺產的產生過程、遺產發揮的作用、對各利益攸關方的影響以及不同群體與遺產的互動,其總體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人為本”。其背景是學者們發現當代遺產保護出現了幾種令人憂心的趨勢:
(1)遺產保護越來越脫離民眾,成為一個僅與遺產保護專家有關的狹窄領域[17]。
(2)遺產的敘事日益窄化,只有遺產是國家象征物這一個意義維度得到了突出強調,遺產對于民眾、地方的意義被邊緣化。本來具有多層次意義的遺產變得敘事單一化[18]。
(3)遺產事業中僵硬地堅持靜態的博物館式的保護,文化遺產保護與民眾生活、社會可持續發展呈對立狀態。
許多學者對這種現狀進行反思,對與遺產相關的多個主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以下分成五個主題進行評述:
1.對遺產再理論化,探索遺產的本質
長期以來,受實證科學的影響,遺產領域推崇實證、量化,追求客觀性,避免主觀性。20世紀下半葉以來,學者們開始認識到傳統的二元論哲學的不足,它將人的心靈與外部世界對立起來,割裂了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外界的物體與人們的心靈并非截然分開、二元對立,而是有內在聯系。“遺產并非預先存在,等待我們去發現的物質遺存,而是建構的產物,是我們的認識、觀念的產物,許多學科的知識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物質對象只有在進入人們的視野,被感知、被賦予價值后,才成為遺產,遺產本質上是一種人與物互動的文化現象。例如,中國大運河一直存在,可是自2014年起才開始被視為“世界文化遺產”。
學者們對于遺產的本質進行深入研究,對遺產進行了再理論化,揭示出這樣的原理:遺產不僅僅是物質遺存,更是與民眾密切相關的文化實踐。大衛·哈維(David C.Harvey)指出,遺產現象是一個動態的利用過去、影響當下的文化過程,應當被理解為一個動詞[20]。勞拉簡·史密斯指出,遺產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實踐,民眾在遺產地進行記憶傳承、地方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建構、塑造自我身份等文化實踐,遺產的物質載體、場所、空間發揮了重要的輔助作用。以澳大利亞昆士蘭(Queensland)地區的原住民為例,她發現,遺產地被原住民珍視,是因為它們是傳承、接受文化意義、文化知識、文化記憶的場所,對遺產的利用使其成為遺產。社會各個群體與遺產都有密切的聯系,遺產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許多作用[21]。這兩種思想在遺產思辨研究中有突出的影響力,在其啟發下,遺產研究從關注“遺產是什么”轉向“遺產發揮什么作用”。這些思想也符合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例如在山東曲阜孔廟、鄒城孟廟等遺產地,其價值體系中最重要的是利用這些場所祭祀圣賢、傳承儒家文化的動態實踐,建筑、場所則為祭祀與教化提供了一個必要的空間。
2.對遺產價值重新思考
對遺產價值的認識是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基礎。學者們發現,遺產的價值并不是內在地蘊藏在遺產的物質形態里,而是人賦予的[22]。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指出,事物存在于一個特定的空間、時間中,圍繞該事物有各種關系。一件事物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存在于這一關系網絡中[23]。朱迪·喬伊(Jody Joy)通過敘述其家族三代人珍視一枚獎牌的故事,指出獎牌對于其家族三代人都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它與作者的祖父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緊密相關,而非獎牌本身具有內在價值[24]。遺產的價值因人而異,對同一遺產,不同群體往往有多樣化的理解[25]。因此,遺產的保護與利用需要了解各利益攸關方對于遺產的理解與認知。
3.對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反思
對世界文化遺產的反思是當前遺產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學者們指出,當代遺產管理存在著西方文化霸權,本質上是歐美國家把源于歐美的對物質性的熱衷推廣至全世界;中國等亞洲國家原本的擁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在此過程中逐漸受到壓制[26]。世界文化遺產的概念“推崇源于西方的對遺產物質性的熱衷,要求全世界不同文化都采取同樣的對物質性的態度,是西方文化觀念的全球化推廣”[27]。世界文化遺產評估遺產的方式熱衷于對遺產物質性的評估,遺產地的民眾與遺產的聯系在這種框架里被邊緣化[28]。圍繞世界文化遺產的評選與管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中心等組織變成了跨國的“遺產王國”[29]。
4.對遺產保護運動中忽視民眾的偏頗現象進行反思
學者們意識到遺產保護成為一個由保護專家圍繞遺產的物質遺存開展保護的狹窄領域,遺產對于民眾的意義和價值被邊緣化,人們面對的是被剝離了情感的遺產[30],遺產保護變成了“對表象的熱衷”[31]。其他社會群體對遺產的理解、認識很少有表達的機會。遺產機構、保護專家形成了“思維共同體”[32]。
“誰的遺產”被作為一個核心問題提了出來。艾瑪·沃特彤(Emma Waterton)以英國一處文化景觀為例,分析遺產管理過程中漠視當地民眾和社區對于這處文化景觀的情感的原因是遺產管理采用的是技術化、科學化的方式[33]。道格拉斯·修奇(Schoch)分析了德國易北河谷(Dresden Elbe Valley)被《世界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List)除名的案例,指出當地民眾對于在河谷修建橋梁有實際需求,然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中心的專家執著于易北河谷的美學價值,二者的沖突導致了易北河谷被除名這一結果[34]。
遺產與權利成為另外一個重要主題。林恩·梅斯克爾(Lynn Meskell)指出,“世界文化遺產”通常使用“普遍權利”“普遍價值”的話語表述,壓制了遺產地居民對于“什么是遺產”“如何保護遺產”的理解,本質上是歐美文化以“普遍價值”的話語維持其文化霸權。以阿富汗為例,歐美各國表現出要拯救阿富汗遺產的姿態,卻很少考慮阿富汗民眾的命運。因此,遺產界需要反思遺產的知識基礎與遺產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問題[35]。威廉·羅根(William Logan)近年來倡導一種新的遺產保護與利用路徑,即遺產保護與利用需要以保護民眾權利為基礎[36]。然而由于傳統的遺產知識框架的局限性,考古學家及其他遺產管理者基本不擅長發揮遺產的經濟、社會效益,不容易擺脫自身的學術框架、身份、審美趣味的限制[37]。
5.對靜態保護的反思
傳統的靜態遺產保護不斷被反思。在諸多類型的遺產中,有相當一部分依然是活態遺產,民眾與這類遺產有緊密聯系,遺產原有功能依然在延續。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CROM)自20世紀末以來開展了一系列運用“活態遺產法”(living heritage approach)保護和利用此類遺產的項目。約安尼斯·鮑里斯(Ioannis Poulios)歸納總結了“活態遺產法”的創新之處:它將與遺產有緊密聯系的核心社群(core community)視為遺產保護與利用的主體,賦予核心社群主要權力,遺產保護專家發揮必要的輔助作用,雙方以該社群的遺產與文化的延續為目標;把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將遺產的物質載體看作是可再生的,致力于在保護物質載體與發揮遺產的功能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必要時優先考慮遺產功能的延續[38]。通過這幾個層面的創新,遺產保護與利用成為民眾擁有、民眾參與、民眾共享遺產保護與利用成果的事業。
三、國際遺產組織對遺產認識的變遷
與此同時,國際遺產保護界也在發生范式的變遷,對遺產思辨研究等潮流作出回應。不少遺產保護者認識到,保護的服務對象是主體,即與遺產有關的民眾,遺產的物質載體的保存是手段而非終極目標。當代保護理論首要關注保護主體,而非遺產的物質對象[39];社會對遺產物質對象的保護不是因為對象本身,而是因為其具有的無形象征性對人們有影響[40]。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前任主席古斯塔夫·阿羅茲(Gustabo Araoz)指出,一個新的遺產保護范式正在興起,傳統的遺產知識的解釋力在下降。對于同一處遺產,不同社會群體可能會賦予不同的價值,遺產的價值不僅僅在物質載體上[41]。可見看出,古斯塔夫·阿羅茲在維持遺產的物質載體具有內在價值這種傳統認識的前提下,力圖拓展對遺產價值的理解,接納其他群體對同一物質載體可能賦予的不同的價值。以往遺產保護專家僅關注遺產的物質性,而如今與遺產密切相關的“人”成為遺產事業的中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國際遺產組織發布的指導性文件的表述中,民眾的權重地位在逐漸上升。
《威尼斯憲章》(Venice Charter)的重心在于對遺產物質性的管理,而《奈良真實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把重心轉向了文化價值的多樣性,把民眾和社區引入到全球遺產管理中,探討遺產對民眾和社區意味著什么[42]。2005年,《奈良真實性文件》的精神被寫入了《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從此檢驗遺產“真實性”的標準不再局限于對遺產物質載體的考察,而是包括了遺產的“外形與設計、材料與實體、用途與功能、傳統技術與管理體制、位置與環境、語言及其他非物質遺產因素、精神與感覺等”[43]。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3年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其中涉及到“人”的表述如下:
第15條 締約國在開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時,應努力確保創造、維護和傳承這種遺產的群體、團體、個人的最大限度的參與,并吸收他們積極地參與有關的管理。[44]
該公約第15條顯示,群體的參與、民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作用被提到了較重要的地位。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關于歷史性城市景觀的建議書》(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該建議書提出了對于遺產的新的理解,包括社區參與、對多種遺產價值的承認、對城市變遷的接受[45]。2017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印度德里(Delhi)的會議上發布了《德里宣言》(Delhi Declaration),文中提出,遺產和民主是“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的關鍵要素[46]。
縱觀上述變化,國際遺產組織也在從“以物為本”逐漸轉向“以人為本”,重新思索遺產與民眾的關系,在新的框架下推進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國內有學者注意到了這一變化。宋新潮指出,“作為文化遺產的管理者,不僅要具備扎實的專業能力,更需要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不僅是傳承文化遺產的物質形態,更重要的是關注文化遺產保護,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47]。
四、對國內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啟示
中國有利用文化遺產進行社會教化的傳統。從20世紀上半葉開始,文化遺產的保護成為一種事業,形成了遺產保護群體,與19世紀后期歐洲遺產保護興起的背景有相似之處。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我國文物大量外流,也是促使遺產保護意識形成的歷史背景[48],“以物為本”由此成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特征。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遺產現象的認識不斷加深,國家期待文化遺產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等事業中發揮更大作用。面對這些重大變化,國內遺產保護與利用應與時俱進,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讓遺產“活起來”,發揮更大的作用。國際遺產界出現的“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范式變遷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
1.《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有待完善
現代遺產保護運動中,各國紛紛出臺法律法規,對于歷史建筑、歷史名城、考古遺址等都有相應的保護條款,以控制對遺產可能造成的影響。然而對于文化遺產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即文化遺產對于社會大眾的價值,卻沒有相應條款予以保障[49]。《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自從1982年制定以來,已經經歷了五次修改,但對于與遺產密切相關的“民眾”著墨甚少,仍然將“民眾”定位為被動的受教育者。
2.國家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中應注重保護與利用的結合
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編制保護規劃已經成為我國文物保護管理的共識。但是目前保護規劃的編制過程中,絕大部分篇幅用于保護方式的確定,包括“兩劃”范圍內高度、密度、風貌、業態、施工規范、開發強調等一系列控制方式,對于未來的利用卻著墨不多。盡管2017年編制完成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編制要求》進一步強調了要“正確處理好文物保護與經濟建設的關系,文物保護與合理利用的關系,促進文物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但在價值認定時,依然局限于“對文物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及其類型特征進行辨認”[50]。這使得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中社會參與匱乏,淡化了對遺產的利用。實際操作中,對遺產的保護風貌、材質、工藝等要求往往比較到位,但是一旦涉及到如何利用的問題,由于與文化遺產的價值相距“比較遠”,專家們往往陷入不同理解方式的爭論中,最后難以落實。筆者認為,今后在國保單位的保護規劃中,對于國保單位的價值評估應借鑒國內外遺產學界的研究成果,注重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以及不同社會群體與文化遺產的聯系,為探討文化遺產的利用這一問題留下更多空間。
3.加強跨學科合作,改進對文化遺產的價值評估方式
由于傳統的科學保護觀長期影響了文化遺產事業,遺產評估往往依靠“歷史”“藝術”“科學”三大價值類型去評估遺產。在《巴拉憲章》(Burra Charter)的啟發下,21世紀初國家文物局制定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增加了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兩種價值類型。它們是本質層次上的遺產的文化價值,是我國文化遺產事業中研究得非常不充分的價值類型[51]。因此,未來需要創新遺產相關學科的定位,改進考古學等學科的人才培養方式;加強與歷史學、人類學等傳統上關注民眾與文化價值的學科的跨學科合作,改進遺產價值評估方法,豐富對遺產的社會、文化價值的認識。這對于通過遺產闡釋我國悠久、獨特的文化傳統具有根本意義。
4.文博單位要加大開放、利用的力度,重建與民眾的聯系
在傳統的科學保護觀念中,文化遺產往往被認為面臨著風險,民眾往往被視為風險的一部分。實際上這是一種觀念的約束,在此影響下,文化遺產往往很少被展出。“遺產面臨風險”的說法是一個非常有伸縮性的、非常依賴主觀性判斷的說法,以此限制對遺產的利用并不合適[52]。文化遺產只有與民眾接觸,在其價值得到傳播并被欣賞時,才會發揮其作用。因此,各級文博單位應當破除傳統觀念的束縛,加大文化遺產展陳、利用的力度,使之與民眾共享。此外,要廣泛運用各種媒介手段,加大對文博單位及其文化遺產信息的傳播。各級文博單位的考核應當注意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并重。
五、結語
本研究通過梳理國際遺產學界的研究文獻,指出了“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轉換這一趨勢。文化遺產長期被視為科學保護的對象,客觀上忽視了遺產是人與物互動的文化現象。遺產處于社會關系中,與民眾密切相關,文化遺產事業不等于對遺產物質對象的靜態保護。只有確立“以人為本”的理念,讓文化遺產“活起來”,才能“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53]。當文化遺產與社會大眾連接起來時,文化遺產才會“活起來”,并在當代中國各項事業建設中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
[1]習近平:《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新華網[EB/OL][2013-12-3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
[2]段清波:《論考古學學科目標和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
[3]Holtorf C.,Fairclough G.The New Heritage and re-shapings of the past.A González-Ruibal(ed.)Reclaiming Archaeology:Beyond the Tropes of Modernity.London:Routledge,2013.
[4]Byrne D.Counterheritage: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Asia.New York:Routledge,2014:50,52.
[5]同[4]。
[6]〔西〕薩爾瓦多·穆尼奧斯·比尼亞斯(Salvador Mu?oz Vi?as)著,張鵬、張怡欣、吳霄婧譯:《當代保護理論》,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2頁。
[7]同[6],第72頁。
[8]同[6],第81頁。
[9]同[6],第76頁。
[10]同[6],第80頁。
[11]Holtorf C.The Changing Contribu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o Society,Museum International,2011,63:1-2.
[12]Byrne D.The past of others: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Unpublished PhD Thesi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4:14.
[13]Foucault M.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New York:Pantheon,1972:224.
[14]Smith L.Uses of Heritage.London:Routledge,2006.
[15]陳嘉映:《哲學科學常識》,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106頁。
[16]SmithL.Editorial.InternationalJournalofHeritageStudies,2012,18(6).
[17]a.Smith L.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2004:86;b.Winter T.Post-Conflict Heritage,Postcolonial Tourism:Culture,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at Angkor.London:Routeldge,2007:13.
[18]Byrne D.Love&loss in the 1960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3,19(6).
[19]Kuutma K.Cultural Heritage:an Introduction to Entanglements of Knowledge,Politics and Property.Journal of Ethnology and Folkloristics,2009,3(2):6.
[20]Harvey D.C.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temporality,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01,7(4).
[21]a.Smith L.Uses of Heritage.London:Routledge,2006;b.〔澳〕勞拉簡·史密斯(Laurajane Smith)著,張煜譯:《遺產本質上都是非物質的:遺產批判研究和博物館研究》,《文化遺產》2018年第3期。
[22]a.Tainter J.A.,Lucas,G.J.Epistemology of the significance concept.American Antiquity,1983,48(4);b.De la Torre,M.Values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Heritage&Society,2013,6(2).
[23]Heidegger M.The thing.Heidegger,M.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
[24]Joy J.Biography of a medal:people and the things they value.Schofield,J.,Johnson,W.G.and Beck,C.M.(eds.)Material Culture:The archaeology of twentieth century conflict.London:Routledge,2002.
[25]De la Torre M.Values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Heritage&Society.2013,6(2).
[26]Byrne D.Western hegemony in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History and Anthropology,1991,5(2).
[27]Meskell L.Negative Heritage and Past Mastering in Archaeology.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2002,75(3):569.
[28]Rao K.A new paradigm for the identification,nomination and inscription of properties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0,16(3).
[29]Willems W.J.H.The Future of World Herita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 Heritage Regimes.Heritage&Society,2014,7(2).
[30]Byrne D.A Critique of unfeeling heritage.Smith,L.and Akagawa,N.(eds.)Intangible Heritage.London:Routledge,2009:231.
[31]同[4],第52頁。
[32]Holtorf C.,Hogberg A.Contemporary Heritage and the Future.Waterton,E.,Watson,S.(eds.)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eritage Research.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5:511.
[33]Waterton E.Whose Sense of Place?Reconciling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Community Values:Cultural Landscapes in Engla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05,11(4).
[34]Schoch D.Whose World Heritage?Dresden’s WaldschloBchen Bridge and UNESCO’s Delisting of the Dresden Elbe Valle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2014,(21).
[35]Meskell L.Conflict heritage and expert failure.Labadi,S,Long,C.(eds)Heritage and 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10.
[36]Logan W.Heritage Rights-Avoidance and Reinforcement.Heritage&Society,2014,7(2).
[37]Hodder I.Cultural Heritage Rights:From Ownership and Descent to Justice and Well-being.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2010,83(4).
[38]Poulios I.Discussing strategy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as an example of strategic innovation.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4,4(1).
[39]同[6],第129頁。
[40]同[6],第141頁。
[41]Araoz G.F.Preserving heritage places under a new paradigm.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1,1(1):59.
[42]Holtorf C.,Kono T.Forum on Nara+20:An Introduction.Heritage&Society,2015,8(2):139.
[43]UNESCO: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Paris,2005:21.
[44]張松:《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國際憲章與國內法規選編》,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1頁。
[45]Araoz G.Conservation Philosophy and its Development:Changing Understandings of Authenticity and Significance.Heritage&Society,2013,6(2):153.
[46]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德里宣言——遺產與民主》,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網站[EB/OL][2018-01-18]http://www.icomoschina.org.cn/news.php?class=451.
[47]宋新潮:《文化遺產永續傳承》,《人民日報》2018年4月15日第7版。
[48]鮑小會:《中國現代文物保護意識的形成》,《文博》2000年第3期。
[49]同[45],第153頁。
[50]國家文物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編制要求(修訂稿草案)》,國家文物局網站[EB/OL][2018-01-15]http://www.sohu.com/a/216853828_170361.
[51]段清波:《論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52]Rico T.Heritage at Risk:The Authority and Autonomy of a Dominant Preservation Framework.Samuels K.L.,Rico T.(eds.).Heritage Keywords:Rhetoric and Redescrip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Boulder: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2015.
[53]國家文物局:《關于促進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見》,國家文物局網站[EB/OL][2016-10-18]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8/content_51211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