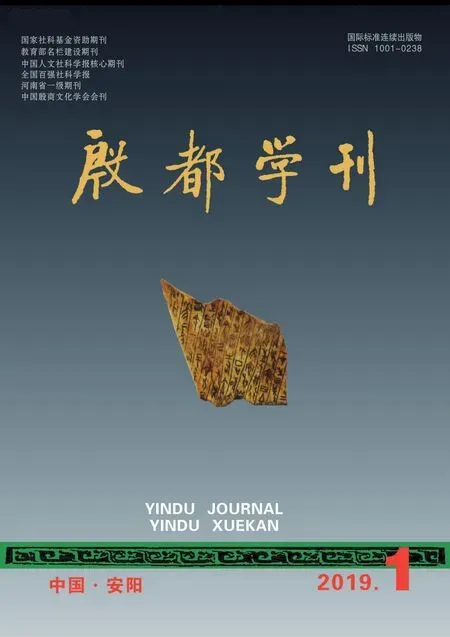《甲骨卜辭七集》序言
白瑞華(著),郅曉娜(譯)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致 謝
1937年初在多倫多,明義士教授和我一起通讀摹本,并提供了各種幫助,尤其在辨別偽刻和疑似偽刻上提供了很多意見。亨利·盧斯先生提供了印刷經費;盧斯家庭和方法斂家庭在濰縣是多年的鄰居。我的朋友和前學生房兆楹夫人杜聯喆,書寫了扉頁上的文字。金璋先生為本書提供了幾方面信息。T的相關信息由郎曼主任提供;S的相關信息由吉卜生先生提供;B的相關信息由Paul Chalfant Bergen先生提供;P的相關信息由都格博士提供;W的相關信息由衛德明博士、魯道夫·施特赫林先生和魯雅文博士提供;R的相關信息由D.M.F. Hoysted上校提供。
我還要感謝方法斂夫人和Edward N. Chalfant先生,把方法斂先生的遺稿、相關的書信和論文都交由我整理。
白瑞華 紐約 1938年
二、簡稱表
B Bergen Collection 柏爾根藏品
C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庫方藏品
H Hopkins Collection 金璋藏品
M Menzies Collection, in 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 Shanghai 1917 明義士藏品,著錄在1917年上海出版的《殷虛卜辭》中
P Princeton Collection 普林斯頓大學藏品
R Royal Asiatic Society Collection 皇家亞洲文會藏品
S Shanghai Museum, N.C.B.R.A.S., Collection 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上海博物院藏品
T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Collection 天津新學書院藏品
W Wilhelm Collection 衛禮賢藏品
X Sun Collection 孫氏藏品
三、前 言
本書著錄的31頁甲骨摹本,是從1914年方法斂先生去世后遺留的手稿《甲骨卜辭》(Bone Inscriptions)中進一步挑選出來的。我們從這部遺稿中選出132頁甲骨摹本,1935年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第一版很快脫銷,兩個月內就出了第二版。鑒于中國古文字學界和金石學界對摹本固有的偏見——與拓本相比——,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學科領域里,這些20多年前的成果還能引起如此關注,這對方法斂來說著實是更加令人矚目的致敬。
方法斂經手和研究了除庫方藏品以外的很多商代甲骨刻辭。庫方藏品是經他手的5宗甲骨收藏中最大的一宗。他摹寫了所有經他手的甲骨,還根據甲骨稿本摹寫了那些他未親見的甲骨,并把所有這些一手資料編為《甲骨卜辭》第一卷,一共423頁摹本。
正如庫方藏品一樣,本書著錄的小宗甲骨藏品中,也有不少甲骨在摹寫后的這些年里慘遭丟失、錯置、斷裂甚至毀壞。24片已確定丟失,書中都有標注。可能還有其他一些甲骨,這里的摹本成了目前唯一的記錄。在重新綴合碎片和解讀破損卜辭時,這些摹本就極有價值。
圖版5—16是方法斂最早的摹本,與他后期的摹本,如圖版22—25衛禮賢藏品和尚待出版的金璋藏品相比,摹寫的熟練程度相對欠缺。圖版1—4和圖版32是方法斂根據他人所做摹本重新摹寫的例子,自己并未親見這些甲骨。與S和P這兩宗尚存的甲骨實物,以及明義士對B這宗甲骨的直接摹寫相比,方法斂的摹本并無太多可修正之處,即使有也不值得重視。方法斂使用非常厚的不透明紙進行摹寫。有時他在用墨水摹錄之前會先把甲骨放在紙上用鉛筆勾勒其形。他用金屬鋼筆和液體油墨徒手摹錄文字。在手稿《甲骨卜辭·導言》第五頁,他寫到:
“起初,照相被認為是復制刻辭最好的手段,但后來我發現,甲骨的形狀很不規則,刻字的顏色與骨面的顏色極為接近,以至于文字無法看見或者模糊不清,所以并不容易進行拍照。另一個困難在于,需要拍照的甲骨數量很大,沒有設備齊全的工作室,拍照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基于以上這些原因,我決定用鋼筆和墨水進行摹寫,并盡其所能地復現甲骨的形狀和刻辭的原貌。這種方法會由于字形模糊不清造成的錯誤理解而出現摹寫失真之處,但我已經竭盡努力把這種風險降到最低。讀者應該會注意到,甲骨碎片邊緣有一些顯而易見的殘字,缺失的筆畫我在甲骨邊緣用圓點虛勾了出來。”
方法斂沒有提到墨拓這種形式,不過他對中國人偏愛的這種方法相當熟悉。《甲骨卜辭》中有63頁圖版,是他摹寫了《鐵云藏龜》的全部拓本(序言1903年,出版于1904年上海)。1935年6月飛爾德博物館歸還給方氏家庭的方法斂遺稿中,有很多墨拓的銅器銘文和陶器銘文,但甲骨拓本只有本書27頁著錄的那8版。
殷墟遺址的早期發掘,對于商代研究者來說不僅僅是一種好奇的興趣。方法斂在《殷虛卜辭》中這樣敘述甲骨的發現:
“甲骨是一些人在田地里私自挖掘偶然發現的。確切發掘地尚未披露出來。……甲骨發現于1899年。商販們自然把北京當作兜售這些奇特文物的最好市場,但發現北京因義和團亂作一團,其中一些古董商販就轉走山東,把許多甲骨和護身符處理給偶然遇見的購買者,并最終把一小部分甲骨賣給了濰縣一位古董商,這位古董商在1903年秋把它賣給了庫壽齡和我。”
在1906年匹茲堡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字考》(Early Chinese Writing)第30頁,方法斂指出這位古董商是“一位本地商人。這位中國紳士,是作者的一位朋友。”《殷虛卜辭》手稿所附的信件和筆記中,經常提到方法斂從一位“李先生”手中購買甲骨。至于這位“李先生”的全名,《殷虛卜辭·參考目錄》第29條有所提及,可能是一個人,也可能不是一個人:“未出版手稿,著錄了很多銅器銘文,山東濰縣李茹賓編纂,送于本人”。無論“李茹賓”是否就是古董商“李先生”,我們都可以把《殷虛卜辭》和《中國古代文字考》中提到的這位“李先生”稱之為“古董商……本地商人……中國紳士……作者的朋友”。
然而,根據1937年董作賓、胡厚宣在上海出版的《甲骨年表》(詳細信息請參看1—2頁),趙執齋是向方法斂出售甲骨的濰縣古董商,范維卿是向方法斂出售甲骨的古玩小販。無論趙執齋還是范維卿,他們的名字都不曾在《殷虛卜辭》及相關資料中出現過。“李先生”或許是趙執齋的同伙,也或許是趙執齋的同行經銷商,作為趙執齋的中間人和方法斂對接。
極有可能的是,范維卿經手了T和S這兩宗甲骨,見圖版1—12。范維卿是濰縣人,一位旅行經銷商,常在收藏家和盜墓者之間牽線搭橋,并把田野接觸作為私有信息,當被問起文物出土地點時故意散播錯誤信息。1899年,不知在什么情況下,他把一些甲骨從河南帶到北京呈給端方,據說端方非常高興,以每字2.5兩銀子的價格收購。1899年秋他以每片2兩銀子的價格賣給王懿榮12片。1900年春又賣給王懿榮800片左右。等他再次攜帶一批新甲骨去往北京時,北京因拳亂被封鎖,他轉而去了濰縣,并把部分甲骨轉給了朋友趙執齋。
毫無疑問,范維卿是第一個把商代甲骨作為考古文物、而非藥材進行兜售的人。他可能獨自發現了這些遺物,也可能在聽說北京藥鋪出售龍骨后才注意到這些遺物。1899年,作為王懿榮的門上客,劉鐵云在被作為藥材弄碎的龍骨,即龜殼上發現了一些古文字。意識到這是一種未知的古文字資料,他們到出售龍骨的菜市口達仁堂藥店進行詢問。據說,王懿榮以每字1兩銀子的價格購買了部分帶字龍骨。劉鐵云遍訪藥鋪,收購了所有帶字的甲骨碎片。在接下來的4年時間里,劉鐵云收集了約5000片,包括一些偽刻。他在《鐵云藏龜》中公布了1058片甲骨拓本,是中國古文字學和金石學領域里第一部大型甲骨刻辭著錄書。
起初的高價立刻導致了私掘和造假。壟斷新生意的渴望,造成了出土地點的混亂。居住在彰德府(安陽)的明義士牧師,雖然離發掘地僅2英里,并且自己就是甲骨收藏者,在1909年4月20日回復方法斂詢問的信中還說,聽說最近新出了一批甲骨,但他花了大約一年時間也沒有打探到任何信息。在后來的一封信里,他也說了同樣的話,并把這稱為“商販的緘默”。
本書圖版中的偽刻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非卜骨上作偽,這些骨上通常不會有刻辭,比如骨鏃S1、S2、S3和B1、B2、B3;一種是在完全空白的卜骨殘片上作偽,比如P76、P77,或者在部分空白的卜骨殘片上作偽,比如B48、W5、W11。方法斂提到的護身符,形狀和刻辭皆是偽造。B和P中的護身符已被剔除,另外5宗藏品中沒有護身符。
本書12片上有偽刻,3片值得懷疑。在得出這個判斷之前,明義士教授查看了S和B尚存的全部甲骨實物,筆者查看了S和P尚存的全部甲骨實物。我們沒有查看T、B[注]此處“B”應為白瑞華筆誤,前面已提到明義士教授查看了“B”柏爾根藏品的甲骨實物,未經查看的應該是“W”衛禮賢藏品。、X和R這4宗的甲骨實物,其上有無標注只是根據摹本上的字形和內容進行的判斷。明義士教授在鑒別甲骨真偽上非常專業,但也可能存在一些完全抄錄真刻辭的偽刻,是根據摹本、甚或拓本和照片也無法鑒別出來的。這樣的偽刻非常少,作偽者更喜歡在原刻上增字,比如W5、W11。就一片偽刻而言,忠實的抄錄或許對閱讀卜辭無害,但對統計信息出現的頻次有害。對古文字形,尤其是不常見字形的細節進行精細研究時,不能只依靠摹本。
這7宗甲骨都是在殷墟發掘早期購買的,現分散在中國、歐洲和美國。每宗甲骨的具體信息請看本書第4頁和第5頁的內容。
四、甲骨來源情況說明
T,天津新學書院藏品。圖版1—4:共25片,骨24片、甲1片。來自王懿榮舊藏,因此購于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之前。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王懿榮在8月自殺。他的大部分藏品被兒子王翰甫出售,其中甲骨刻辭大多被劉鐵云購得。天津新學書院創始人赫立德在任期間,各種各樣的藏品被學校借展。后來,部分展品被挑選出來贈予學校。這25片甲骨就含在贈品之中,但1904年學校博物館開館時還沒有這批甲骨,甲骨在大約一年后即1905年才進入博物館。1907年天津總領事金璋摹寫了這批甲骨,方法斂在沒有見到原物的情況下,根據金璋的摹本做了摹本,即現在書中的這部分。在赫立德的請求下,金璋先生著文對這批甲骨進行了釋讀,發表在1908年的校園期刊College Echoes上。
S,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上海博物院藏品。圖版5—12:共195片,其中14片原骨已丟失。這是方法斂1903年在濰縣購買的第一批甲骨。有一點無法解釋之處是,方法斂在《中國古代文字考》第31頁,以及庫壽齡在1914年發表的論文(JNCB XLV.66)中均提到上海博物院有400片甲骨。博物院于1904年2月10日購得這批甲骨,由當時的主席霍必瀾先生慷慨出資。許多年來這批甲骨都無人關注,后來才被蘇柯仁重新發現。1934年上海博物院考古部榮譽保管員吉卜生把這些甲骨放在展柜里展覽,并制作了摹本,1934年12月以縮小的形式在會刊上發表(XXI No.6)。吉卜生先生是少數研究商代文字的西方學者之一。方法斂《中國古代文字考》第30、33頁發表了S1、S2、S3、S7的摹本。
B,柏爾根藏品。圖版13—16:共79片甲骨,現原骨遺失2片。保存在山東濟南齊魯大學廣智院(Whitewright Institute)中。這批甲骨由方法斂在濰縣購買,可能是1904—05年間所獲1800片中的一部分[參看《中國古代文字考》第31頁]。在1905年2月15日方法斂返回美國之前,這批甲骨已經轉到了柏爾根手中。柏爾根是濰縣山東聯合大學文理學院的校長,這所學校后來搬到濟南,和山東基督教學院合并,即現在的齊魯大學。這批甲骨存放在濟南府研究所博物館——后改名為廣智院中,被粘在展柜里進行展覽。蜘蛛以粘甲骨之面糊為食,蝕穿骨面,幾乎毀了這些藏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明義士教授,用酒精稀釋過的漂白蟲膠(西洋白漆皮)作為固定劑,阻止了這些毀壞。他以拓本和摹本的形式出版了這批藏品,并附有漢語釋文、導言和注釋,發表在1935年《齊大季刊》第6期和第7期上。1936年廣智院出版了單行冊,有摹本、漢語釋文和導言,英文標題為The Oracle Bones of the Shang Dynasty (Tsinan Institute Collection)。明義士版本著錄了74片甲骨,其中B22、B36現已丟失,骨簇刻辭B1、B2、B3被剔除。方法斂《中國古代文字考》第30,34頁公布了B1、B2、B3、B41、B49的摹本。
P,普林斯頓大學藏品,普林斯頓,新澤西州,美國。圖版17—21:共119片,甲95片、骨24片,其中2片原骨已丟失。這批甲骨由方法斂在濰縣所購,可能是他1906年11月20日從美國返回中國后不久所購。多年來這批甲骨為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濰縣山東聯合大學教師Harold Whitcher所有。1927年Whitcher先生把這批甲骨賣給都格教授,都格教授又于1928年把它和古幣藏品一起借給普林斯頓大學,1934年贈給普林斯頓大學。現存的117片甲骨,已經在兩冊實驗小冊子里以照片或拓片、或兩者并有的形式出版:白瑞華《殷虛甲骨相片》(1935年紐約)著錄了102片;白瑞華《殷虛甲骨拓片》(1937年紐約)著錄了另外15片,并重復著錄了其他幾片。皮其萊教授對P29和P48上的顏料進行了分析,并把顯微照片發表在1937年3月15日《工業機械化學雜志》上。同時,沒有插圖和技術信息較少的版本發表在1937年3月《哈佛亞洲研究雜志》上。
W,衛禮賢藏品。圖版22—25:共72片甲骨,其中甲55片,骨17片。收藏地:70片在瑞士巴塞爾民族藝術博物館,一片W11在德國法蘭克福中國研究所,一片丟失(?)。這批甲骨屬于德國傳教士漢學家衛禮賢博士,可能是他在青島購得。(威爾茲藏品,280片,現藏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據說共711片,1909年購于青島)。1911年夏方法斂在青島度假期間摹寫了這批甲骨。與本書其他早期摹本相比,方法斂摹寫商代刻辭的水平逐漸提高。后來,衛禮賢把W11這片甲骨贈給法蘭克福中國研究所,其余甲骨賣給了伯賴斯維克·薩拉辛牧師,伯賴斯維克·薩拉辛又于1914年把它們贈給巴塞爾民族藝術博物館。W1、W4、W5、W9這幾片甲骨的描述和照片由伯賴斯維克·薩拉辛進行過發表,題為《巴塞爾民族藝術博物館藏中國甲骨》,發表在《弗里茨·薩拉辛教授60華誕考古學、人類學、史前史論文集》(1919年12月3日)第59—64頁上。
X,孫氏藏品。圖版26—31:31片。現藏地不詳。方法斂在《殷虛卜辭》中寫到,這批甲骨“為山東臨淄孫氏所藏”。孫氏全名可能是孫文瀾,是寫在甲骨墨拓紙頁上的簽名,見圖版27,X8。另外,《殷虛卜辭》參考目錄第28條也提到過臨淄人孫文楷,是一本未出版手稿的作者,由于“孫先生的慷慨”而使方法斂有了一份抄本。方法斂在到布道站傳教的過程中經常訪問臨淄。這31片甲骨可能購于1907年之前,那時孫先生似乎有100片左右甲骨。
R,倫敦皇家亞洲文會藏品。圖版32:共6片,原骨已失。這幾片甲骨為皇家亞洲文會一名會員所有,后借給另一名會員Blagden先生,1910年Blagden先生把摹本寄給金璋,金璋又把摹本寄給方法斂,方法斂據此重摹了一份。皇家亞洲文會理事會備忘錄中有相關記錄,最后的記錄見于1925年10月6日。1937年進行了徹底的研究和咨詢,仍未找到原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