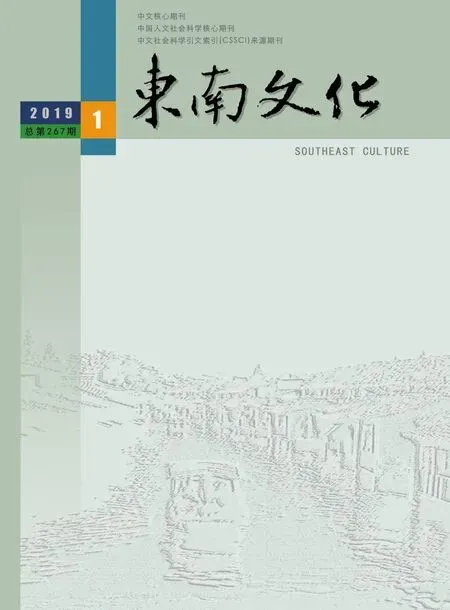價值凝練與價值呈現:從中國土司遺址申遺看考古學理論方法新變化
郭偉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長沙 410008)
內容提要:中國土司遺址申遺,是考古學積極參與文化遺產保護的一次成功嘗試。世界遺產視角下的考古工作,從田野發掘操作到文物保護與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點,考古學在此過程中的實踐,也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考古學理論、技術與方法。實踐證明,考古學與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在新時代的文化建設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015年7月4日,以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遺址和貴州播州海龍屯遺址為代表的中國土司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List),這是考古工作參與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的一次成功實踐。在此過程中,考古學與文化遺產學在理論與方法上發生了深度交流、碰撞與融合。申遺的成功,不僅為新時代考古學的發展拓展了新方向,也為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描繪出新藍圖。本文結合考古學實踐,主要以湖南老司城遺址為例,談一點筆者在中國土司遺址申遺過程中的心得和體會。
一、考古學在土司遺址申遺中的作用
(一)土司制度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表現考古學文化的實物遺存[1],這些實物遺存嚴格說來就是人類的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是人類社會歷史和文明的見證,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全人類而言,都是不可估價且無法替代的財產。因此,國際社會對此極為重視,為了盡可能地保證對世界遺產的確認、保護、保存和展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于1972年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見證不僅有浩如煙海的文獻史料,更有散落在遼闊大地上的無數文物古跡,這些都是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產。確認、保護、保存、展示這些文化遺產,并將其代代相傳是全人類的歷史責任。1985年12月2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決定,批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土司制度是一項非常特殊的制度,體現了我們祖先在國家治理上獨特的政治智慧。這種制度脫胎于上古時期的“五服制”,進而發展到中古時期的“羈縻制”,完善于元明時期的“土司制”,是中國文化多元一體和中華民族多元一統歷史發展的重要制度體現[2]。土司制度曾經對我國社稷安定、疆域穩固發揮了積極作用,土司文化遺產對于認識和了解土司制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我國陸續公布了一批關于土司遺存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但是,對于土司文化遺產特別是土司遺址的全面了解和認識,一直以來都比較模糊,亟待開展系統的考古工作。
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位于湖南永順縣靈溪鎮老司城村,是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在1995、1996年曾經進行過規模較小的考古發掘,考古工作并不系統[4]。因此,為了進一步了解該遺址的文化面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0年向國家文物局申報主動性考古發掘。正是這一次考古發掘,拉開了中國土司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序幕。
(二)聯合申遺旨在提供較全面完整地揭示中國土司遺址的考古學案例
2010年老司城遺址考古發掘取得了重要成果。通過調查與勘探,考古工作者基本上厘清了城址各個功能區的分布情況:生活區與衙署區處于城址的中心,其周圍分布有街道區、宗教區、墓葬區、休閑區等功能區;在城址的河流兩端,分別是具有軍事護衛性質的軍事城堡。生活區為歷代土司及貴族生活居住區,共有四門,大西門為正門,西北角、西南角、東南角各有一門。西城門之門道的情況經過發掘呈現如下:門道由卵石砌成的路面、臺級與紅石條砌成的路面、臺級組成;下接右街的卵石街道,上與生活區內的道路相接;門道兩側的城墻以紅砂巖錯縫平鋪疊砌包邊,內側發現有排水溝。西北部城墻保存完整,最高處高達6米,大西門左側還發現一處門樓建筑,盡顯土司宮城的恢宏氣勢。通過發掘南城墻區域的后期廢棄堆積,清晰的城墻、卵石環城道路、環城墻內側排水系統、水溝上的石橋、城內建筑的保坎等豐富的遺跡呈現出來,這一區域城址的基本結構也基本被厘清。發掘的材料可以分四期:第一期以生活區城墻下、卵石道路下的堆積層為代表,包含物中有明代早期的青花瓷片。這表明,建城之前老司城已有人居住,年代下限為明代初,上限年代還不能確定。因此,從南宋至元代,老司城是否已經建立了司治,這個問題的解答還有待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第二期以生活區城墻、道路及排水設施等遺跡為代表,其建筑年代約在明代早期。第三期以生活區發掘的建筑及其保坎、溝等遺跡為代表,其建筑年代約在明代中晚期。第四期以生活區晚期建筑及其他大量晚期遺跡為代表,其年代上限為改土歸流的清雍正六年(1728年),老司城作為司治從此廢棄。除了城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還對被當地稱為“紫金山墓地”的土司墓葬進行了發掘。紫金山墓地位于老司城東南郊,是明代永順土司的家族墓地,已探明墓地面積約1500平方米,有土司及其眷屬墓葬三十余座,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中暴露于地表、已遭盜掘的八座墓葬進行了發掘清理。整個墓園的地表由墓葬封土、拜臺、“八”字山墻、花帶纏腰過道、南北神道及石像生、照壁等遺跡組成,這一發現對于復原明代土司家族墓園整體面貌具有重要意義。發掘的彭世麒夫妻合葬墓制作精致、裝飾華美,堪稱明代土司墓的精品之作。彭世麒、彭宗舜、彭翼南祖孫三代土司都是永順土司中功勛卓著的人物,他們曾帶領土兵抗擊倭寇,立下過赫赫戰功,是土家族的英雄。墓地出土的彭世麒、彭宗舜、彭翼南及一些土司眷屬的墓志銘,也是研究土司社會的珍貴史料。除考古發掘外,考古工作人員還對永順土司遺存分布區域開展了專題調查,發現土司時期各類遺址達六十多處,包括烽火臺、軍事關卡、土司莊園、古墓群、宗教遺址、石刻題銘等,對永順老司城相關遺址的內涵和空間分布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2010年永順老司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入選當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考古新發現”,同時也入選“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老司城遺址的重要價值和文化內涵隨著考古發掘成果的公布而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也對它的文化和旅游價值給予了高度關注。受老司城遺址發掘的啟發,貴州海龍屯和湖北唐崖土司遺址隨后開展了主動性考古發掘,也獲得了重要成果。海龍屯遺址的發掘獲得了“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唐崖遺址也取得了很大的收獲。在這個基礎上,以老司城遺址為龍頭的中國土司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呼聲越來越高,經過多方努力,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遺址和貴州播州海龍屯遺址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獲得業內專家和國家文物局的認可,中國土司遺址于2012年11月獲準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三地聯合申遺的目的并非“捆綁搭車”以增加遺產的數量,而是因為這三處遺址能夠互相彌補相關遺產內容,形成體現中國土司遺產真實性與完整性的整體框架。從地域來說,三處遺址同處武陵山片區,這是中國歷史上漢族文化區域和西南少數民族文化區域的交界地帶,海龍屯遺址所在的古播州地區更是深入西南地區腹地,是多民族共生融合的典型區域。從民族文化面貌來看,永順土司和唐崖土司是土家族的分布區,海龍屯是苗族分布區,周邊還分布有不少其他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分布地區。從土司層級來說,老司城與海龍屯屬于宣慰司,是土司行政級別中最高的層級;唐崖土司屬于長官司,是土司行政系列中較低的層級。這樣就可較為完整地體現土司制度體系。從地理環境和文化景觀方面來說,三處遺址雖然都是山城,但其周邊環境卻有明顯差異:唐崖遺址山勢略緩,遺址邊河流迂回,較為開闊;老司城靈溪縈繞,山勢高峻;海龍屯乃是一軍事城堡,山勢險要,易守難攻。三處遺址各具特色、互為補充,較好地體現了當時西南地區特別是武陵山區土司社會的特點。因此三處遺址聯合申遺能夠完整地反映中國土司遺址和土司制度的特點。
(三)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務在于揭示遺址的布局與文化內涵
考古遺址申遺的前提是考古工作的開展,考古工作是在當今前沿考古學理論、方法指導下的田野實踐。以前中國土司遺址的考古田野工作做得很少,并未積累多少經驗,但總體而言,應該成為歷史時期城市考古的一個門類。因此,制定科學合理的考古工作計劃非常重要。為此,2010年在老司城遺址考古工作開始前,我們制定了詳細的考古工作計劃報國家文物局批準,以后幾年的考古發掘都按照考古工作計劃開展,確保田野工作有序進行。在工作中,貫徹聚落考古理念,從空間和時間上首先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探,大體了解遺址的堆積情況和分布范圍,選擇關鍵性地點進行考古發掘。作為一處城址,我們首先對城墻、城門、道路和排水系統進行解剖,從空間布局上把握這座城的整體面貌;其次,厘清其他細節,如街巷、建筑基址的空間關系;再次,從時間的角度把握各遺存的動態變化過程。這樣由點及面、由表入里的工作模式,將一座廢棄了數百年之久的古城層層揭剝,次第打開這本“無字地書”。與此同時,圍繞中心城址,我們還對周邊土司時期遺存開展了系統調查,覆蓋范圍達數百平方千米,舉凡與土司活動有關的遺存全數納入調查視野,調查工作也是由點及面地進行。通過這樣的工作,我們不僅對老司城周邊與城址相關的墓地、宗教建筑、哨卡、行宮別苑有了基本了解,也對與此有關的城堡、要塞、烽火臺、村寨、古道、碼頭、石刻等進行了全面摸底[5]。海龍屯和唐崖遺址的考古工作也是大致如此。通過這樣的方法,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極大地豐富了土司遺存的文化內涵。
(四)價值凝練是考古學參與申遺的關鍵工作
考古揭示出來的遺物、遺跡,是當時人們生產、生活行為所遺留,這些已經成為“死”的遺存。考古學就是要通過對這些遺存的揭示、分析與研究,達到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目的;要通過這些物質遺存來探索歷史的發展規律,這是考古學最終需要解決的問題。數代考古學人奮力探索,創設了多種多樣的理論與方法,從文化歷史主義到過程主義、后過程主義,從歸納到演繹,從器物類型學到碳十四測年,無非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考古學的目標與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取向一致,《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以下簡稱“《操作指南》”)強調:突出普遍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是指罕見的、超越了國家界限的、對全人類的現在和未來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的文化或自然價值。因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是遺產的價值標準。按照《操作指南》的要求,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包括:(i)作為人類天才的創造力的杰作;(ii)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人類價值觀的重要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iii)能為延續至今或業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iv)是一種建筑、建筑或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人類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v)是傳統人類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當它面臨不可逆變化的影響而變得脆弱;(vi)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活傳統、觀點、信仰、藝術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聯系。總之,世界文化遺產的OUV要站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高度,在世界范圍內對比和研究遺產是否具有人類發展進程中的普遍規律。考古發掘的遺物、遺跡如何與上述標準來對照,提煉出土司遺址的OUV,是考古學者和文化遺產學者共同面臨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展開多學科合作,突破學科藩籬,互相融合,取得共識。
然而,問題并非可以被輕易解決。眾所周知,考古學與其他學科一樣,有自己的局限性:它比較適合開展物質層面的研究,而不太擅長精神層面的研究;比較適合長時段的歷史時空研究,而不太適合短時段尤其是精準時空的研究。考古學的進步就是不斷突破學科局限性的過程,這也是所有學科的追求目標,因此,“透物見人”便是朝這樣的目標邁進。考古發掘的土司遺存,如老司城遺址所體現出來的是城墻、城門、道路、排水溝、建筑基址以及破碎的生活器皿和動物骨骼等,這些至多可以反映當時土司生活的大致情況,但無法重建當時社會的全部,更難以重現當時人們的精神信仰。而土司遺址申遺,主要在于土司制度,這是一種政治制度,在社會形態上是屬于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則屬于精神文化領域。要通過考古遺存來體現一種制度,則要完成從考古學到歷史學的轉換,完成從物質文化研究到精神文化研究的轉變,亦即讓那些沉默的磚石瓦塊變成文字“開口說話”,這何其艱難!對照《操作指南》的標準,都指明要闡釋“價值觀”“文化傳統”“范例”“觀點、信仰”等等,這些價值標準恰恰屬于精神文化領域,考古學要完成這一目標,必須對發掘出土的遺物、遺跡進行精準的價值判定,以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認定標準。
既然土司遺址代表的是土司制度,那么我們就應該對土司制度有準確的認識。我們通過全面研究土司制度,最后提出這樣的觀點:土司制度反映了中央政權與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傳承和國家認同方面的價值觀交流;見證了古代中國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對西南多民族地區獨特的“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這是土司制度的核心價值或者說就是土司遺產的OUV。但是,這還無法讓考古遺存與土司制度聯系起來,我們還要從考古遺存里去尋找“價值觀”,并讓相關遺存反映出“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按照這一邏輯去對照《操作指南》的標準ⅱ,申遺文本中大致作了這樣的闡述:三處遺址是中國西南多民族地區土司制度的代表性遺址,它們在選址方式、整體布局和建筑風格上,體現了官方文化與地方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和價值觀交流,同時也是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政治治理和社會制度的表達。這樣就將遺址的地理位置、周邊環境及相關遺存的布局、建筑風格、裝飾圖案等方面進行歸納和提煉,以符合《操作指南》的價值標準ⅱ。對照《操作指南》的標準ⅲ,即遺產“為延續至今或業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這一標準關鍵在于見證價值,實際上與前一標準大致雷同,就需要對土司制度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深度概括。遺址出土的墓葬、墓志銘、石像生以及體現土司存在的牌坊、建筑、宮殿和所在的時空背景亦均可作為土司制度的反映。對照《操作指南》標準ⅵ,即遺產“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活傳統、觀點、信仰、藝術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聯系”,則同樣要在“齊政修教、因俗而治”這一核心理念上作解釋,且與現存的相關民族信仰及非物質文化等聯系起來。因此,土司遺址與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延續至今的典型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有直接的關聯,與土司制度有直接的關聯。這一標準涉及延續至今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習俗問題,并將考古發掘的遺存與之關聯。固然,土司時期也有一系列風俗傳統,土家族現存的擺手舞、茅古斯、織錦等均具有這樣的特點。在對土司遺址的價值展開研究時,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即突出普遍價值是對全人類的歷史和全人類的發展都具有普遍的價值。因此,這樣的OUV不單是獨特的,更應該是普遍的,要從全球的眼光來看待遺產價值,要將土司遺產價值放到世界范圍來審視,要從世界各地與之類似的其他國家與地方的政治治理與民族認同等更廣的角度來觀照土司制度和土司遺產的價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理論是如此,民族性也應該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并能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范例。因此,我們也先后考察了數個類似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同類文化遺產地,以期為跨文化的價值比較研究提供基礎材料。
通過這樣的努力,考古學與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進行了深度交流,為文化遺產的價值表達搭建了一個更加寬廣的平臺,也同時為編制世界文化遺產申報文本提供了基礎。
二、考古學理論方法的新變化
(一)價值呈現:考古發掘與本體保護展示的對接
老司城遺址的考古工作首先要根據城址考古或聚落考古的要求編制考古工作計劃,這一考古工作計劃是根據考古學本身學術目的而設計的。在考古發掘實施過程中,申遺才提上議事日程。換言之,在原來的考古工作計劃里,并未將申報世界遺產作為考古工作的目的,待2012年土司遺址列入申遺預備名單以后,考古工作才由原來的常規學術訴求變成配合申遺的工作范式。在此情景之下,考古工作的形式與方法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考古工作必須圍繞揭示遺產的OUV這一目標,也就是要突出遺址的重點,而遺址的重點就是遺址中最重要的遺物和遺跡,這當然也是考古工作的要求。不過,因為申遺的要求,這些發掘出來的遺存必須立即加以保護和展示,除了供編制申遺文本之需,還要接受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專家的實地考察評估,更要在申遺之后成為長期開放的場地以供民眾參觀。保護展示遺跡就是呈現遺產價值,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呈現遺產的價值,在將遺產的精華全部呈現出來的同時,還要考慮呈現的方式和途徑,這就需要考古與文物保護、展示工作的全面無縫對接和深度融合[6]。這種模式下,考古發掘在某種程度上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圍繞保護、展示而開展,或者說,考古發掘現場同時也成為文物保護、展示工程施工的現場。這對于考古與文物保護、展示來說,更是多學科、多門類和多行業的協調、碰撞與融合。
實際上,在考古發掘的田野操作部分,我們就遇到了新的問題——土司遺存的特殊性。這類遺址雖然大多數遺跡已成為廢墟而深埋地下,但也有一部分遺跡并非完全入地,而是呈現殘垣斷壁的狀態或多或少地兀立于地面,比如城墻、排水溝、道路、建筑基礎等。在田野考古操作中就遇到一個問題,即這些遺跡如何編號、記錄和測繪。比如城墻,老司城貴族生活區的城墻基本保存下來,但也有不少地段和基礎部分坍塌后被埋,針對這城墻的測繪和記錄本身就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即使分段測繪,也有區分側重點、如何取舍的考慮。此外,道路是體量巨大的遺跡,從城內通到城外,還經過城門臺階和城外街巷。從完整性與連續性上而言,道路是無限延長的,那么,這樣的道路在編號、測繪與記錄上也有取舍標準的不確定性問題,排水溝也有同樣的問題。這類地上地下結合在一起的遺跡單位都應該編入考古發掘報告中。但是,從考古地層學而言,道路是重要的地層界面,也是當時的地面,在地面之上建造房子、打破地面修建排水溝,按照層位學的理論,至少道路、房子、排水溝屬于三個有疊壓打破關系的不同堆積單位。如果在遺址發掘中,應理所當然地認為它們屬于不同的時間階段,而現在它們卻是共存的。亦即,一條道路可以對應多個時期的建筑單元,但我們卻沒有能力將與不同時期建筑單元對應的道路一一揭示出來,這樣的例子實際上是為考古地層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另外,在類似于城墻、城門及其相關遺存的發掘中也有重新樹立田野考古理念方面的問題。比如,城門在使用過程中雖有改造或者重建,但它與道路一樣,在空間布局上是大致固定的,城墻與城門擁有完全不同功能和性質,城門之上的城門樓也應該是不同性質的建筑,城門一側的門亭又是另外的建筑遺存。這些是構成考古情景(context)的重要遺存單元,但是,它們究竟是同一個遺跡內的不同堆積單位還是不同的遺跡單位?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圓其說的理由。這讓我們反思田野發掘的某些準則問題,如考古地層學的理論方法如何在這樣的發掘中得到正確體現,《田野考古工作規程》所提倡的考古系絡圖如何執行。這些都需要發掘者在遵循學術規范的同時,能積極主動地開展技術方法上的探索創新。
由于考古發掘與文物本體保護、展示工程同步進行,這兩項工作對于文物本體信息的提取雖然理念相近,但方法卻有一定的差異。在實際工作過程中,考古從文物保護那里借鑒到了不少理念和方法。按照規范,文物保護工程實施的事前必須有現狀勘察,現狀勘察是對文物保存的現狀進行的調查研究,為保護工程的實施提供基礎資料,如同醫生治病前對病患的診斷和分析檢測。文物保護的現狀調查研究包括賦存環境研究和多維信息提取,涉及面非常廣,從遺址保存環境動態監測、空間測繪與識別、本體制作工藝與材料、本體病害探測等方面入手,舉凡環境地貌、地質水文、氣候與溫濕度、黏土礦物、土壤、巖性和吸水率、動植物和生物病害、文物材質的質地與成分及病害、風化與侵蝕機理分析、埋藏環境等,均是文物保護現狀勘察需要開展的基礎性研究工作,這實際上也是考古發掘現場對文物信息提取所需要的,但是《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并未作出如此明細的規范性要求。考古發掘現場出土文物的保護是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具有發現文物和保護文物同步進行的特點。考古發掘是揭露遺跡、遺物并全方位提取信息的過程,不可否認,這個過程也會導致對古代遺存埋藏在地下相對穩定的平衡保存狀態的破壞,平衡狀態一旦被破壞,各種遺存現象及出土的文物瞬息之間便可能發生變化而受到損壞。因此,考古現場出土文物的保護是整個文物保護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是后期實驗室保護處理的關鍵,文物保護工作必須從田野發掘現場做起。但是,過往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實踐中,由于考古發掘現場普遍存在信息采集設備落后、保護裝備缺乏、文保科技介入程度不足等情況,客觀上造成了考古發掘現場文物保護工作的缺失和珍貴考古信息遺漏的問題,給后續文物保護和研究工作帶來嚴重影響。注重考古發掘現場的文物保護實際上是將考古實驗室前置于考古發掘的第一現場,這對于考古信息的提取和文物保護所產生的良好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中國土司遺址申遺過程中,老司城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與文物本體保護高度融合所積累的經驗,已經成為我們建設考古移動實驗平臺的基礎。
(二)遺址化過程研究
考古工作重在揭示遺址的文化內涵并解釋其文化價值,從這個角度而言,考古學有一套系統的田野操作技術與方法。考古學家對于遺址的認識依賴于這個遺址的全部考古學文化遺存堆積,揭露和研究這些堆積的性質和特點,了解它們之間的關系,才可以重建當時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這一點,也是世界遺產價值凝練的基礎,二者完全一致。但世界文化遺產對于OUV的要求還要了解后堆積時代發生了什么,也就是遺址化過程研究,亦即遺址的價值所蘊含的人類情感和族群記憶,并由此而考察這樣的價值體系如何進入后世人群的文化傳統之中。因此,遺址化的過程研究乃是一個被重點關注的對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遺址本體的遺址化過程,二是遺址對于后世的作用和影響。對于第一個問題,實際上需要通過考古工作來完成。因為考古從揭去表土開始,就開始了考古遺存的堆積過程研究,或者說埋藏過程研究。揭示遺址各堆積單元的形成過程是遺址化研究的關鍵,遺存堆積單位形成過程的埋藏學研究必須堅持精細化考古和多學科合作的原則,需要開展考古信息的精細提取和分析工作。但是,正如前述,考古學本身有局限性,并不是人類社會的所有信息都能進入遺址,即使所有信息都進入了遺址,也面臨著如何認識和解讀的問題。所以,考古學要做的工作就是盡可能地精細化操作、多學科合作,以提取盡可能多的考古信息,然后盡可能地開展研究以逼近歷史的真相。對于第二個問題,需要更多地從人類學、民族學與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亦即通過研究將遺址發掘出土遺存與地方文化傳承和晚期社會結合起來,以了解文化遺產與后代的聯系,了解有哪些遺存所表達的文化及其觀念成為當地的傳統和價值觀,并進入到后人的情感記憶中。從現在認識過去,讓過去告訴未來,這是世界遺產在人類社會進程中的重要使命和擔當。人類歷史的過去,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從物質形態上找到,另一部分則是非物質的,是觀念、信仰與傳統習俗等。通過人類學的調查,遺址化過程和文化傳統形成過程的一些具體形態與細節大致能夠被重建。因此,我們對土司遺址的考古工作除了田野發掘之外,還對現存村落進行了系統調查,針對當代村落的布局、建筑的形態、墓地的安置、農事與手工業、商貿往來、婚姻家庭和社群關系、禁忌信仰、風俗禮儀、音樂舞蹈、口頭傳說與地方戲曲等進行了系統調查,并了解其與土司遺址所見的各類遺存的關聯性。通過這樣的工作,我們不僅加深了對考古發掘出土遺存的認識和解讀,也為延續至今的文化傳統找到了根源,為文化認同和族群情感記憶找到了一條可以勾連的紐帶。所謂利益攸關方的情感認同或許就能通過這樣的工作得以實現。我們通過這樣的工作,將老司城遺址周邊的大量非物質文化傳統與土司遺存關聯起來,發現如趕年、哭嫁等民俗,以及擺手舞、茅古斯、梯瑪神歌、西南卡普等民間藝術都延續著古老的文化基因,這些民俗與民間藝術因此也成為具有重要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心得與體會
1.申遺過程中的考古發掘方式的調整
與申遺緊密相關的考古學實踐與傳統意義上的考古發掘并沒有本質的不同,但因工作關注點要求不一樣,因此在發掘操作上有一定的差異。傳統的考古發掘需要將遺跡、遺物全面揭露,探方要發掘到生土,并在生土之后繼續發掘若干深度。但申遺過程中的考古發掘因配合遺產保護、展示的需要,發掘方式要有所調整:一是不能向生土進軍,遇到重要遺存必須停止發掘,實施現場保護;二是還要實施“非完全發掘模式”,即盡可能地避免大規模發掘,以保護和保持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強調微發掘或微損、無損發掘[7]。就當前考古學科的發展水平而言,雖然多學科合作已經較為普及,但考古發掘現場的文物保護和多維信息提取過程并未完善,考古發掘勢必導致文化遺產信息的流失。申遺工作面臨的狀況是,發掘出土的重要遺存要馬上實施現場保護、展示,不能打包和搬遷,因此也不能采取將重要遺跡搬回室內進行實驗室考古的方法。這樣一來,就遇到一些問題:一是考古如果不能完全揭露重要遺跡之下的遺存,就永遠無法了解遺址早期遺存的情況,無法重建遺址的完整過程;二是考古發掘現場要實施保護、展示,勢必造成考古與文保人員之間因理念不同而產生的沖突,如何協調和配合,也需要思考解決。
2.考古發掘要研究發掘出土文物的價值
考古發掘現場的多維信息提取包括賦存環境的研究,是文物保護工作的現狀調查和病害分析等基礎性研究的重點,這與考古發掘中的信息采集工作有相同點,也有一定差異。相比較而言,文物保護現狀調查所做的工作有很多經驗值得考古借鑒,比如賦存環境研究不僅是對環境考古學的補充,更是對于文物本體的全面分析測試。遺址化過程研究不僅僅涵蓋了埋藏學的內容,還要注重人類學、民族學的調查;另外,值得重視的是遺產價值研究,這是評估世界文化遺產標準的重點,而這往往并不為考古學家所重視。我們若不認真研究遺產的價值,就無法給遺產一個準確的定位,就不能究明遺產在人類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從考古角度而言,考古發掘若不研究出土文物的價值,考古的意義同樣無從談起。
3.新時期考古工作的價值和意義
考古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是當今考古學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考古學應該為當代以及未來國家、社會、區域、社區乃至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等方面提供富有建設性的啟發、思考以及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理論支撐。考古學應當成為通過對古代物質遺存的認識來研究不同時期天、地、人之間相互關系及人類社會發展演變規律的一門學科,因此,考古工作者要對遺產的價值凝練起主導作用[8]。同時,考古學的任務是認識古代,而認識古代的目的是為了現在的發展,并為未來提供可借鑒的經驗。因此,考古的成果不能成為少數人的專利,我們不能將其束之高閣或藏于深宮,而應該向廣大民眾傳遞相關信息,這是知識的呈現方式,是文化的情感表達,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延續與傳遞。以老司城為代表的土司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后,其所帶來的文化、社會與經濟效應相當可觀,文化與旅游的融合為助推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日趨明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明顯感受到考古成果能為新時代的國家文化建設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考古工作者能在考古遺產的價值研究、本體保護、展示利用及價值呈現等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古學的使命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目的就達到了一致。
[1]張忠培:《關于考古學的幾個問題》,《文物》1990年第12期。
[2]湖南永順現存五代溪州銅柱上《復溪州銅柱記》銘文曰:“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
[3]已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土司遺存除了永順老司城、唐崖土司城址、海龍屯之外,尚有15處。包括湖北容美土司遺址,貴州大屯土司莊園、開陽馬頭寨古建筑群,云南儂氏土司衙署、孟連宣撫司署、南甸宣撫司署、兔峨土司衙署、葉枝土司衙署、納樓長官司署、隴西世族莊園,廣西莫土司衙署,四川卓克基土司官寨、沃日土司官寨經樓與碉樓、直波碉樓,甘肅魯土司衙門舊址等。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永順老司城發掘報告》,《湖南考古2002》,岳麓書社2004年。
[5]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處等:《老司城遺址周邊遺存調查報告》,岳麓書社2013年。
[6]價值呈現的另一種方式是發掘出土可移動文物的保護與展示,這一部分的任務是在博物館內完成的,本文略去。
[7]杜金鵬:《試論考古與遺址保護》,《考古》2008年第1期。
[8]段清波:《考古學要發掘遺產的文化價值》,《光明日報》2015年7月22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