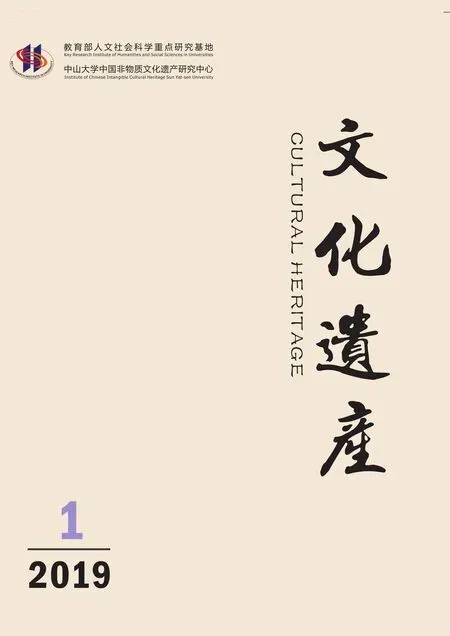從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看清晚期地方士紳的風(fēng)俗觀*
周連華
引 言
中國古代的文人很早就有記錄鄉(xiāng)土風(fēng)俗的自覺意識與歷史傳統(tǒng)。目前,民俗學(xué)界對于中國歷史文獻中風(fēng)俗類著述的研究已多有涉獵,較具代表性的有蕭放關(guān)于《荊楚歲時記》的研究*參見蕭放:《地域民眾生活的時間表述——〈荊楚歲時記〉學(xué)術(shù)意義探賾》,《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0年第6期;《歲時生活與荊楚民眾的巫鬼觀念——〈荊楚歲時記〉研究之一》,《湖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4年第6期。,張勃對《北京歲華記》、《帝京景物略》等歷史民俗文獻的解讀*參見張勃:《〈北京歲華記〉手抄本及其歲時民俗文獻價值》,《文獻》2010年第3期;《〈帝京景物略〉中的歲時民俗記述研究——兼及對當(dāng)代民俗志書寫的一點思考》,《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等等。這些研究多以著作本身為基礎(chǔ)展開,通過對文本的細致剖析,揭示作品蘊含的風(fēng)俗價值與歷史意義;相對而言,對著作者及其生活世界關(guān)注不夠,如此便很難洞悉著作背后幽微曲折的歷史真實,以及作者隱藏在字里行間的風(fēng)俗觀念。有鑒于此,本文以清晚期魯中知名士紳王培荀及其風(fēng)俗著作《鄉(xiāng)園憶舊錄》為研究對象,從王氏的個人生活世界切入,分析他在《鄉(xiāng)園憶舊錄》中所描述的地方社會生活,并以此解讀清晚期地方士紳階層在記述鄉(xiāng)土民俗的過程中所呈現(xiàn)的書寫策略與民俗觀念。
一、 異鄉(xiāng)漂泊與鄉(xiāng)愁安頓:王培荀與《鄉(xiāng)園憶舊錄》
王培荀,字景叔,號雪嶠,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生于魯中淄川縣窎橋莊。窎橋莊位于縣域東北,此處自古科舉之風(fēng)盛行,莊西南方向的黌山之上即有鄭公書院,相傳為漢代大儒鄭玄所建。王氏先祖于明初遷居窎橋莊之后,耕讀傳家,自五世祖王崇義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及第開始,其后百余年間王氏子弟一百四十余人取得科舉功名,可謂盛極一時。清康熙之后王氏宗族日趨衰落,到十五世王培荀出生的清晚期,窎橋王氏登科出仕者已是鳳毛麟角。雖然此時王氏宗族的政治地位已漸趨式微,但王培荀還是深受科舉世家的文化熏染,其自幼勤勉好學(xué),飽讀詩書,以期像祖輩先賢那般出仕為官、施展抱負。
但王培荀的仕途之路充滿坎坷,屢次赴考,皆落孫山,直到道光元年(1821),近四十歲時才考中山東鄉(xiāng)試恩科第四名,領(lǐng)得鄉(xiāng)薦資格赴蒲臺、長山等地設(shè)館授學(xué),但仍未出仕為官。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已過半百之年的他才通過專為落榜舉人開設(shè)的大挑考試,獲一等功名。后被分發(fā)至四川,先后出任豐都、榮昌、新津、興文、榮縣等縣知縣。道光二十九年(1849),因年事過高,官務(wù)力不從心,遂解甲歸田,返還故土養(yǎng)老,時年六十六歲,其前后在川為官十四載。咸豐九年(1859),卒于故里,時年七十七歲。
縱觀王培荀的一生,其生在齊、仕在蜀,是一位心懷志向的地方文人。他雖出仕較晚、官職不高,但無論身居何處,始終以讀書為性命,筆耕不輟,著述頗豐,有回憶錄、隨筆、日記等十幾部作品流傳于世,總計達三百多萬字。特別是為官蜀地的閑暇之余,常與友人悠游于山野勝境之間,情之所至,即吟詩作賦。后結(jié)集整理成書,因完成于榮縣縣衙之內(nèi)的聽雨樓之上,故題名《聽雨樓隨筆》。正是此書勾起了王培荀對淄川故土的無限思念之情,促其提筆寫就《鄉(xiāng)園憶舊錄》。“予游蜀已十年矣,生平釣游所經(jīng),典型所仰,歷歷形諸夢寐,憶之恍如前生。父老所傳述,又恐其久而或忘,故隨意筆之,以慰鄉(xiāng)土之思云爾。”[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11年,第5-6頁。可見該書是作者記述故鄉(xiāng)淄川風(fēng)土人情的回憶性隨筆之作,聊慰其內(nèi)心深處的思鄉(xiāng)之情。
《鄉(xiāng)園憶舊錄》全書包含一千一百多篇文章,共為八卷,傳說、史實、建筑、物產(chǎn)、人物等民俗事象皆有涉及。書中描述諸多故土事物,力求其全,篇幅長短不一。該書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冬始竣,初刻六卷,續(xù)刻兩卷,共八卷。1993年蒲澤校點版由山東齊魯書社出版發(fā)行,2011年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又重新再版。與王培荀既為同僚亦為好友的樂山知縣茹金在為此書撰寫的前序中言及:“回環(huán)莊誦,竊嘆其富麗以立言也,如適海市;其錯落以敘事也,如灑珠泉;其同條而共貫也,如合洙泗之源流;其考異而辯歧也,如別淄澠之真?zhèn)巍V劣谝磺鹨慧直厮哑淦妫辉佉挥尾贿z其美,則又陟三戶、游四舍,而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焉。"[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4頁。溢美之詞,可見一斑。山東籍古典文學(xué)教育家嚴薇青先生也曾評論此書:“誠以王著于我魯山川風(fēng)物、明賢耆舊以及詩文掌故,凡所記憶,悉筆于書,而文辭雅馴,頗有可觀。”[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2頁。《鄉(xiāng)園憶舊錄》一書實則是了解清晚期淄川乃至山東地區(qū)真實風(fēng)貌的重要地方史料文獻。
二、書寫“民俗”:《鄉(xiāng)園憶舊錄》所描述的地方社會生活
從唐宋時期的士族大家到明清時期的地方士紳,士(精英)階層不斷地從中央政權(quán)向地方演化,并逐漸在清代確立起把持地方社會的局面。正如陳鏗所言:“上層士紳把持地方的現(xiàn)象起于明代,盛于有清,流延乃及民國,甚至于清之后十多年。”[注]陳鏗:《從〈醒世姻緣傳〉看明清之際的地方士紳》,《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84年第4期。可以說,地方社會的士紳階層在各種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作為魯中淄邑沒落望族的后裔,王培荀雖然未能像先輩那般成為入京為朝的一品大員,其更多時候只是為官一方的七品縣令。但恰是地方士紳的長久生活促使他貼近民間社會,并借此創(chuàng)作出大量風(fēng)俗類著作。《鄉(xiāng)園憶舊錄》中作者即不惜筆墨,力求完備的將故土社會風(fēng)貌記錄下來,其中涉及傳說、史實、景致、物產(chǎn)、賢士人物等。開卷閱讀,字里行間顯露出清晚期淄川地方社會的生活圖景。
1.地方傳說
《鄉(xiāng)園憶舊錄》中記載有諸多的傳說故事,且皆與淄川當(dāng)?shù)氐臍v史文化密不可分,更是當(dāng)?shù)厝藗兩钆c思想的現(xiàn)實反映,書中所涉?zhèn)髡f故事大致可分為四類。
其一,關(guān)于闈中異事的記載。卷六篇多次提及科舉應(yīng)試過程中發(fā)生的異事。此類異事傳說或是發(fā)生于科舉開考之前,士子多通過夢境或高人指點預(yù)驗登科高中,如《夢驗》[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57頁。篇。或是科舉應(yīng)試之中,士子多被鬼魂纏身,舉止異常,如《闈中報怨》[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57頁。篇。又或是科舉應(yīng)試之后,考官閱卷及揭榜之異事,如《燭三爆》[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60頁。篇。書中記載如此之多的有關(guān)科舉應(yīng)試的異事,充分說明了此地科舉之風(fēng)的興盛,淄川地處魯中腹地,古時臨靠齊魯兩國邊境,深受儒家學(xué)說影響,文人大都期望通過科舉出仕以實現(xiàn)政治抱負。明清之際,淄川縣考中進士榜者達七十八人之多,為周邊縣域之最。并且崛起了包括王氏、高氏、畢氏、韓氏等為主的科舉世家,也出現(xiàn)了名噪一時、入京為官的王崇義、王鰲永、畢自嚴、高珩等人。由此,書中多處記載有關(guān)科舉入試的傳說故事也就不難理解。
其二,關(guān)于地方孝行義舉的傳說記載。孝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維系中國古代家庭關(guān)系的道德準(zhǔn)則。書中關(guān)于孝的傳說主要集中表現(xiàn)于孝子及孝婦故事。孝子傳說故事多展現(xiàn)子雖少亡,多不忘孝心,附魂或還魂侍養(yǎng)雙親,如《張大美》[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68頁。篇記載諸生張大美病歿,魂知已死,痛哭。遇關(guān)帝,問何哭之痛。曰:“母老子幼,無人侍養(yǎng)故也。”帝憫之,令其還魂養(yǎng)母。孝婦傳說故事多為侍親孝行感天動地,如《孝婦之室》[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13頁。篇記載濟寧有婦與老姑、幼子共處茅廬,忽起大火,婦先救姑后保子,子竟無恙。
其三,關(guān)于神、妖、鬼類的傳說記載。淄川是清初著名小說文學(xué)家蒲松齡的故里,蒲氏在名著《聊齋志異》一書中通過對現(xiàn)實生活的所見、所聞、所思書寫鬼魅世界,展現(xiàn)出反抗封建禮教的深刻思想,其對后世影響頗深。蒲氏之后,鬼神體裁的故事表現(xiàn)在淄川文人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了繼承與保留,尤其是蒲松齡本人還曾于康熙年間在窎橋王家做過短暫的私塾先生,由此,王培荀自然受到了蒲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影響。《鄉(xiāng)園憶舊錄》中記載的神靈故事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地方神靈成仙過程的故事敘述。如淄川城東舊有雹神廟,香客之女晨時感召入廟,氣絕而成雹母娘娘[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90頁。。另一類是有關(guān)靈異或靈驗的故事傳說。如《關(guān)帝顯靈》[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82頁。篇記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臨清王倫作亂,攻打東昌府,忽金鼓震地,大隊軍馬,中軍高飄帥旗,金書“關(guān)”字如斗,乃帝君顯靈,叛賊抱頭鼠竄。妖怪故事大都表現(xiàn)出危害人事的一面,狐貍、長蛇、蝙蝠等物,或化作人形,迷惑人心,或現(xiàn)于戶中,預(yù)示禍端。如《大蝙蝠》[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05頁。篇記載焦家橋袁薰,室中忽現(xiàn)一大蝙蝠,垂簾閉窗,以桿逐之,瞥然不見。后家中頻出異事,終衰落矣。鬼怪故事涉及兩篇,簡明意賅,《鬼僮》[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03頁。篇載一小兒,“歿而魂留,有形無質(zhì)也。”白日現(xiàn)形而毫不畏人。《鬼語》[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04頁。篇載濟南鵲華山處,月黑風(fēng)高,常聞鬼語。相較于蒲松齡鬼怪故事浸透出的強烈批判性,王培荀筆下的神、妖、鬼傳說故事則更顯平和,他善于通過直敘的方式將清晚期淄川當(dāng)?shù)厝藗兊恼鎸嵕裆顮顟B(tài)呈現(xiàn)出來。
其四,關(guān)于民間異能之士的記載。古代中國除了居于上層正統(tǒng)的“政治精英”之外,鄉(xiāng)土社會實則還存在著為數(shù)眾多的“民間精英”,而其中部分精英就是通過異于常人的技能獲得村落生存的空間。《鄉(xiāng)園憶舊錄》中記載有淄川眾多具有一技之長的能人,他們或力無窮,《淄川村民某》載:“淄川村民某,兩足牛蹄,有力。每春秋,與牛同耕。冬,以小車運炭八百斤,不履不襪。常睡道側(cè),有人遠而望之一大花牛,近視乃某也。”[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74-375頁。或能祈雨,《范神仙》載:“吾邑耿家莊,有范姓,善祈雨。置書蛙口中,壓砧下。移日啟視,蛙無矣。作法拘之出,視口中書信,有雨則許,若無雨,不能強也。云使蛙于龍。號“范神仙。”[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75頁。或能通靈,《袁姓瞽者》篇:“袁姓瞽者,……自言五、六歲時,目尚無恙,每室中無人,然鬼紛然出,驚而號。”[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94頁。所以,當(dāng)掌握文字系統(tǒng)的地方士紳進行基于地方社會觀察的文學(xué)書寫時,勢必離不開對于民間精英的關(guān)注,王培荀當(dāng)然也不例外。
2.地方景致
《鄉(xiāng)園憶舊錄》中記載有諸多關(guān)于山東地區(qū)的名勝古跡,而游歷山水景致正是地方士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書中所述古跡主要集中于四個區(qū)域。其一,以淄川為中心的私家園林,書中卷四提及淄川園林達十多處,如窎橋王氏園、暢然園、王載揚園,韓氏仙洲園,高氏載酒園,趙氏因園,張氏漪園,畢氏石隱園等。如韓氏之仙洲園篇載:“邑韓氏,累世貴盛,第宅巨麗,別墅、園亭隨在多有,而莫盛于仙洲園。”[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209頁。其二,舊時濟南府的名勝古跡,集中展現(xiàn)于名泉、大明湖及千佛山等處,趵突泉、黑龍?zhí)丁⒄渲槿v下亭等皆有描繪。如《佛峪》篇載:“入深壑,綠樹蔽天,拾級而登。僧房依石壁。壁陡立,萬棱千竅,縱橫無紀律,疑鬼斧神工鑿削而成。”[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242頁。其三,有關(guān)“五岳之首”泰山歷史名跡的記載,卷五記敘泰山古跡多達二十處,太廟、桃花澗、石經(jīng)峪、五大夫松等景致的描繪皆語言精煉、引人入勝。如《岱宗形勝》篇載:“自回馬嶺過快活三里、高老橋,一路坡坨。及澗忽轉(zhuǎn),有水簾洞,飛瀑從西北來,凈如匹練,洞口藏簾中。”[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283頁。此篇用近五百字的言語將泰山勝景娓娓道來,絕無拖沓冗長之句,非王培荀親身游覽不可以有如此精妙之描繪。其四,對儒家圣地曲阜的名跡記載,作者不惜筆墨展現(xiàn)曲阜古跡近四十處,孔府、孔廟、孔林皆細致描繪。長久以來,地方文人樂于結(jié)伴悠游于山林勝跡之中,借景抒情賦詩,展現(xiàn)內(nèi)心真實心境。王培荀即在卷四開篇中言及:“(豪貴公子)約先至某寺,次至某水、某園,后會某山坳,席地笑語,歌呼相聞。”[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209頁。此等境界才是文人士大夫們歸園田居般的理想生活狀態(tài)。
3.地方名賢
《鄉(xiāng)園憶舊錄》中記載了大量有關(guān)于王培荀所熟知的地方名人逸士的傳記,古今人物皆有指涉,且以精煉的語言加以呈現(xiàn)。
書中人物概括可分為三類。其一,以淄川為中心的歷史名士,同時延展到濟南、曲阜、臨清、濰縣、諸城等周邊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區(qū)域。如書中記述有窎橋籍王崇義、王曉、王君賞、王樛、王敷政等王氏族人。同時,還有對淄川望族月莊高氏、西莆畢氏、韓家洼韓氏等地方名仕的記載。而且桓臺新城王氏同為明清享譽淄博地區(qū)的名門望族,書中對王季木、王士禎、王象乾等人也皆有論及;此外,濟南籍的李滄溟、李清照,諸城籍的劉統(tǒng)勛、劉墉等名賢也都有所涉及。其二,做官于山東的外省籍名仕,他們多祖籍江南地區(qū),這也從側(cè)面顯示出明清兩朝江南地區(qū)科舉入世之風(fēng)的興盛。如徐咸清官至山東巡撫,祖籍浙江上虞縣;武進士王來聘,奮勇殺敵解登州之難,祖籍安徽懷寧縣;黃鉞兩次典試山東,祖籍安徽蕪湖。其三,外省籍名士,他們大多游歷于山東之境(如泰山、三孔等),驚嘆折服之際留下了諸多文人墨跡。如四川崇慶籍何明禮,登泰山,游歷下,悵然抒懷。安徽歙縣籍羅聘,游泰山,賦詩句,做丹青。
書中著眼于魯中地區(qū),呈現(xiàn)出清晚期以濟南府為中心的山東仕宦人士,為了解清代山東地方社會官員的個人生活以及彼此間的相互關(guān)系與聯(lián)系提供了最為直接的史料。
4.地方物產(chǎn)
《鄉(xiāng)園憶舊錄》中關(guān)于清晚期山東地方物產(chǎn)的記載頗豐,進而將當(dāng)?shù)厝藗兊恼鎸嵣钍澜绯尸F(xiàn)出來。
此類文章可劃歸為兩類。一類是名揚山東乃至全國的地方特產(chǎn),如淄川淄硯、青州名酒、德州羅酒、博山琉璃、東阿阿膠等,如《淄硯》篇載:“余村(窎橋莊)五、六里,穴崖取石為硯,足供山左數(shù)郡用,名曰‘淄硯’。”[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61頁。清代著名文學(xué)家紀昀就收藏有兩方淄硯,“其淄水石硯銘云:‘淄水石,含密理;小馮君,贈紀子。’”[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61頁。另一類是關(guān)于淄川地方的鄉(xiāng)味,山蘑菇、蕨菜、榆錢、冰魚、銀魚、同蟹、呱呱雞、杏核等皆有描述,如《鄉(xiāng)味》載:“余鄉(xiāng)幽巖深林,生菌大如銀盤,次如盞,小者比雞卵。烹而食,清香沁脾,諸品皆在下風(fēng)。”[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86-487頁。地方特產(chǎn)凝聚著一方水土人們的創(chuàng)造力,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社會生活標(biāo)志物,也是久居于外的游子思念故土?xí)r的追憶物。正如王培荀客居蜀地十余載,久念故鄉(xiāng)時言:“余窶人,生平不識珍錯,而遠游則鄉(xiāng)味每不能忘。”[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86頁。
5.地方史實
《鄉(xiāng)園憶舊錄》中關(guān)于地方史實的記載主要體現(xiàn)在天災(zāi)與人禍。而對重大地方史實的記載,是人們對過往生活的一種重要時間記憶,這種記憶一旦在民眾腦海中固化,就會不斷傳衍下去,并成為地方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書中一方面是對淄川地區(qū)所發(fā)生的較大規(guī)模自然災(zāi)害的記述。如清道光十七年(1837),“夜大雨,淄川西關(guān)外,河水陡高數(shù)丈,門外石牛漂去數(shù)里,崩雉堞,壞廬舍。”[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134頁。此類記述多與王培荀生活年代相吻合,應(yīng)為其親身經(jīng)歷之后的真實記錄。另一方面是對地方所爆發(fā)的戰(zhàn)爭、叛亂事件的記載。一類是由于朝代更迭所引起的地方抵抗戰(zhàn)爭,如《血戰(zhàn)濟南》:“崇禎十一年,我(清)大兵之破居庸入山東也。……相持六十日,須發(fā)盡白,守城者面皆生瘡。明年正月二日,公(宋學(xué)朱)與巡道周公之訓(xùn),夜灑酒城頭,握手唏噓泣下,誓共死。”[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70頁。一類則是地方社會中的農(nóng)民叛亂。如清初爆發(fā)于淄川城的謝遷之亂,《謝遷陷淄》載:“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國初,淄本無寇,釁起微渺。一旦城破,殺戮殘不可言。貴家世族男女,殉難者甚眾。”[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20頁。此類戰(zhàn)亂記述多發(fā)生于明末清初之際,應(yīng)為王培荀根據(jù)縣志、通志等史料整理寫就而成。
綜上可知,寄予著王培荀深切思鄉(xiāng)之情的《鄉(xiāng)園憶舊錄》將淄邑清晚期地方社會生活全方位、多層次的呈現(xiàn)出來,從鄉(xiāng)野傳說到地方史實,從鄉(xiāng)賢名人到村中莽夫,從建筑景觀到特色物產(chǎn),既有高雅的詩文,又有口述的故事,事無巨細,無所不含,雅俗同載,盡收其中,生動地再現(xiàn)了地方社會的風(fēng)俗風(fēng)貌,韻籍著地方士紳的獨特風(fēng)俗觀念。
三、禮俗互參:地方士紳階層的風(fēng)俗觀
對于地方風(fēng)俗文化的書寫是士紳階層所處生活心境的反應(yīng),更是凸顯其地方話語的一種傳達方式。王培荀善于將鄉(xiāng)土中的各類風(fēng)俗生活與官方正統(tǒng)經(jīng)典相結(jié)合,進而體現(xiàn)出禮俗互參的寫作視野。《鄉(xiāng)園憶舊錄》一書中不但記載有豐富多樣的地方民俗事象,也將王培荀所代表的地方士紳階層有籍于鄉(xiāng)土情結(jié)的風(fēng)俗觀念展現(xiàn)無遺。
首先,鑒賞雅玩的著述觀。士紳階層往往是仕途不順的一類特殊群體,他們或久考未中,或出仕未久,或終身未仕。因此,官場失意的士紳階層只能寄情于鄉(xiāng)野山水之間聊以慰藉。王培荀本人即是如此,年過半百才出仕為距故土千里之遙的蜀地縣令,自感升遷無望后,即將性情投射于山水之間。《鄉(xiāng)園憶舊錄》中牽涉淄邑及鄰境篇多為王培荀親歷有感所述,其余篇多為摘錄《山東通志》、郡邑志以及地方士紳的詩文集及詩話、說部集之而成。書中王培荀并沒有嚴格的寫作規(guī)范,多以自己的記憶、興趣愛好為主,選材隨意,體裁廣泛,博采眾長。恰如“凡例”中所言:“此編系刻成《聽雨樓隨筆》后暮秋纂輯。為時甚迫,隨手付梓,先后都無倫次,字句亦未暇修整。聊資談助,不復(fù)成書。”[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7頁。縱觀全書八卷,前三卷皆述名人逸士,第四五卷描繪魯?shù)鼐爸拢诹矶鄬憘髡f故事,第七卷回歸人物著述,第八卷著述人物及物產(chǎn),地方史實的記載則散落于各卷之中。由此可見,作者在寫作此書之時根本不拘章法,更多的顯現(xiàn)出地方士紳鑒賞雅玩的恬適之境,王培荀實則在開篇自序中就已言及:“故于千百,略志一二,公余以此消遣,名之曰《鄉(xiāng)園憶舊》”[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6頁。此外,《雪嶠日記》、《聽雨樓隨筆》、《鄉(xiāng)園憶舊錄》等著作,均秉持了這種寫作方式,其中留下了大量他游歷鄉(xiāng)間村野的所聞、所見、所感、所思。而這種無所拘束的著述方式,充分顯示出王培荀賞鑒雅玩的風(fēng)俗態(tài)度與視野。
其次,眼光向下的取材觀。《鄉(xiāng)園憶舊錄》一書中記載有大量山東地區(qū)的民間傳說、民間故事以及民間史實,甚至對于鬼怪精靈的鄉(xiāng)語怪談也悉數(shù)收錄。王培荀之所以能夠選取如此貼近鄉(xiāng)土社會的題材進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與其成長環(huán)境密不可分。王培荀生于清晚期,他的父親王思樞為地方私塾老師,祖父王相符以務(wù)農(nóng)為生。此時“一縣科甲、半出王門”的昔日望族早已沒落不堪,科舉出仕者更是鳳毛麟角。即便如此,祖、父輩依舊對王培荀寄予厚望,從小就對其嚴加教育,以期他能像先輩那般一朝中舉、光耀門庭。王培荀雖天資聰穎、讀書勤奮,無奈仕途多舛,無法及早步入官場,施展人生報復(fù),可以說是王培荀終其一生的憾事。但可幸的是長時間的地方生活經(jīng)歷造就了王培荀對各種風(fēng)土事物的熟稔,所以他可以輕而易舉的將傳說故事、地方史實投入到作品寫作當(dāng)中,而且諸多故事或史實正是基于他親耳聽聞或親身感受的生活經(jīng)歷寫就而成。同時,王培荀的傳說故事寫作還深受同邑蒲松齡的影響,蒲氏小說多是基于現(xiàn)實生活的志怪故事演繹。王培荀曾在開篇自序中提及:“而蒲柳泉《志異》,搜奇索怪,幾于家有其書。”[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5頁。這充分表明清晚期社會蒲氏小說已廣為人知,尤其是在淄邑更為人推崇。《鄉(xiāng)園憶舊錄》卷一中即載有蒲松齡的個人傳記,其所言:“(蒲氏)所著《聊齋志異》,人服其才學(xué),而未知其生平心術(shù),故略錄梗概焉。”[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23頁。可見,王培荀十分認可蒲松齡的學(xué)識,并且在自己的故事寫作中也呈現(xiàn)了諸多的地方傳說故事,其中也不乏狐、鬼、妖類的志怪故事,同樣折射出地方社會生活的真實境況。
再者,寄情于俗的書寫觀。《鄉(xiāng)園憶舊錄》記載了故土社會的諸多人、事、物,實乃作者以舊物之描繪寫時下之心境。王培荀常年在外做官,遠離故土與親人,孤寂思鄉(xiāng)之情在所難免,家鄉(xiāng)風(fēng)物的回憶性寫作則成為他寄托個人情感的最好載體。而《鄉(xiāng)園憶舊錄》的成書過程恰是慰藉了王培荀遠離故土的思鄉(xiāng)之苦,“予游蜀已十年矣……父老所傳述,又恐其久而或忘,故隨意筆之,以慰鄉(xiāng)土之思云爾。”[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5-6頁。王氏個人生平著述達三百多萬字之巨,尤其是他的隨筆、日記、閑錄類著作多是有感而發(fā)、隨性而成,不拘章法,通俗易懂。他善于在行文中展露最為真實的情感,如卷四開篇《淄川民俗》一文中他感嘆世事變遷,今時“科名漸衰,諸先輩之勛業(yè)文章,藐焉莫睹。降而求之名園甲第、舞臺歌榭,第索之故紙堆中。父老不能言,子弟茫莫知乎!”[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209頁。寥寥數(shù)語即將清晚期淄川社會往昔勝景的衰敗境況展露無遺。《鄉(xiāng)園憶舊錄》一書在描述風(fēng)俗的過程中,隨處可見作者心心念念的思鄉(xiāng)之情、有感而發(fā)的人生思索。所以,在王氏的觀念中,風(fēng)俗既為載體,又為工具,是聊慰思鄉(xiāng)之情的重要對象。縱觀歷代文人的風(fēng)俗志著作也莫不如此,實則在有關(guān)地方風(fēng)俗的描繪中或多或少的寄予著作者對于家鄉(xiāng)的脈脈深情。
最后,辨風(fēng)正俗的教化觀。窎橋莊地處魯中地區(qū),自古儒學(xué)盛行、科舉重仕。乾隆《淄川縣志》卷七“藝文志篇”中記載有元代趙孟頫至元三十年(1293)題寫的《重修先圣廟記》,其中言:“孟頫竊謂公之用心可謂仁矣。其所以宣圣明之化,有功于孔子之道,可謂大矣。況般陽實古齊地,去魯不遠,吾夫子遺風(fēng)流俗,猶可興起。”[注]陳漣遠、白相房主編:《淄川縣志匯編》(全四冊),淄博市新聞出版局準(zhǔn)印2010年,第735頁。明末清初之際窎橋王氏宗族即是通過科舉傳家逐漸崛起為地方望族。王培荀自幼就在家學(xué)文化及儒學(xué)經(jīng)典的影響下成長起來,書中自序中言及:“我國家定鼎二百年于茲矣,德化淪浹之深,度越千古,猶必燔柴泰岳,升馨闕里;詩書弦誦以為習(xí),魚鹽桑麻以為富,觀風(fēng)問俗,煌煌乎匯為巨典,播諸金石。”[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5頁。身為官紳與文人,王培荀理所當(dāng)然的試圖通過儒家正統(tǒng)思想規(guī)范地方社會的鄉(xiāng)風(fēng)民俗。《鄉(xiāng)園憶舊錄》卷六兩則傳說故事亦可顯現(xiàn)王培荀辨風(fēng)正俗的教化觀。歷城石氏婦,性情暴悍,婢有過錯,打其至死。石氏病之,陰間受審,充徒三年,“婦疾頓瘳,別無所苦,惟倆足顛蹶,不利于行,手腕亦拘攣,如負縲紲狀。”[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384頁。濟陽艾孝廉,“能記前生為副榜,捶一婢死。繼母花燭之夕,家人聚觀,某一見大驚,謂形容與婢無異。母遇之酷,某唯唯順從。”[注](清)王培荀:《鄉(xiāng)園憶舊錄》,蒲澤校點,第412頁。此類故事雖為民間傳說,據(jù)實無考,但作者恰是通過虛幻傳說隱喻社會現(xiàn)實,此類行徑絕不可取,希冀地方社會實現(xiàn)與人為善、仁之相處的人際關(guān)系。除此之外,書中不但多次提及闈中之事,且所涉名士,或書功名、官職,或書赴考、履職經(jīng)歷,無不顯示出以積極出仕為內(nèi)在精神的儒家思想。而且,書中有關(guān)地方孝子、孝女、孝婦故事的展現(xiàn),更是王培荀力圖通過樹立典范人物教化民眾,以此推行地方社會德治的表現(xiàn)。
概言之,《鄉(xiāng)園憶舊錄》一書中所記載的民俗事象,既不是文獻輯錄,也不是游歷時的即興敘事,實則為作者在異變的環(huán)境中對之前親身感受的鄉(xiāng)村生活諸多事象的懷舊之作。作者王培荀既是一位飽讀詩書的文人,又是管轄一方的父母官,更是告老還鄉(xiāng)的地方士紳,多重身份的人生閱歷注定了他的文人性格與做派,著述取材更偏隨意,各類事物盡收其中,又借鑒古代志書的編撰范式,在書中設(shè)有景觀、名賢、物產(chǎn)、史實等諸多條目。同時作為地方社會的實際控制階層,他在書中記述了大量的道德教化內(nèi)容,意在提倡儒學(xué),辨風(fēng)正俗,維護正統(tǒng),實現(xiàn)地方社會穩(wěn)定。但是,另一方面,文人士紳對家鄉(xiāng)民俗的書寫又與其自身的成長經(jīng)歷密不可分。《鄉(xiāng)園憶舊錄》一書所載風(fēng)物,或為親身見聞;或為父老言傳,這充分說明王培荀雖然貴為官宦,代表著儒家正統(tǒng),但是他始終離不開鄉(xiāng)野之“俗”,是淄川的鄉(xiāng)土與文化養(yǎng)育了他,這種鄉(xiāng)土文化伴其一生,潛移默化,成為他客居異地聊以自慰的精神載體,所以我們不難理解他的作品中為何收錄如此多的民間軼事與鬼怪傳說。
綜上所述,古代士紳階層具有社會身份的兩面性,既為“鄉(xiāng)土之人”,又為“朝廷之人”。游走于官民之間的特殊身份促使他們成為上下互動、禮俗互動的重要實施者,正如張士閃所言:“以儒學(xué)思想為本的中國知識精英,向來是文化建構(gòu)與生活踐行并重,在生活中建構(gòu)文化,以生活踐行為文化根本。”[注]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王培荀及《鄉(xiāng)園憶舊錄》即是如此。
結(jié)語
地方士紳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層,他們經(jīng)過科舉入試的嚴苛洗禮,獲得了不同等級的官職與功名,成為國家維持地方社會有序運轉(zhuǎn)的中堅力量,在國家-地方上下互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士紳階層熟稔文字書寫,且利用禮俗互參的寫作方式留下了數(shù)量極其豐富的類似于《鄉(xiāng)園憶舊錄》的地方民俗歷史文獻,這是一筆有別于正史與地方志的文獻遺產(chǎn)。
縱然,以現(xiàn)代的學(xué)術(shù)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此類文人士紳寫就的風(fēng)俗類著作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民俗志書寫,但它們在客觀上詳細記錄了大量的民間風(fēng)俗,再現(xiàn)了當(dāng)時的地方社會生活,是我們了解過去鄉(xiāng)土歷史,尤其是歷史上的家族家風(fēng)、風(fēng)土教化、社會組織等真實景況的重要窗口。而且,著作中生動呈現(xiàn)出來的士紳關(guān)于風(fēng)俗的書寫心態(tài)與策略,透露出士紳階層的風(fēng)俗觀念,體現(xiàn)了士紳階層的社會角色與社會責(zé)任,隱藏著中國社會禮俗互動的文化景觀。概言之,地方士紳關(guān)于鄉(xiāng)土風(fēng)俗的書寫,是研究地方民俗史、地方社會史的珍貴史料,理應(yīng)成為現(xiàn)代民俗學(xué)重點關(guān)注的領(lǐng)域。事實上,地方士紳寫就的風(fēng)俗類文獻一直是民俗學(xué)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對這些至今仍散落在民間的文獻進行搜集整理研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