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中船”:時代與現實中人之“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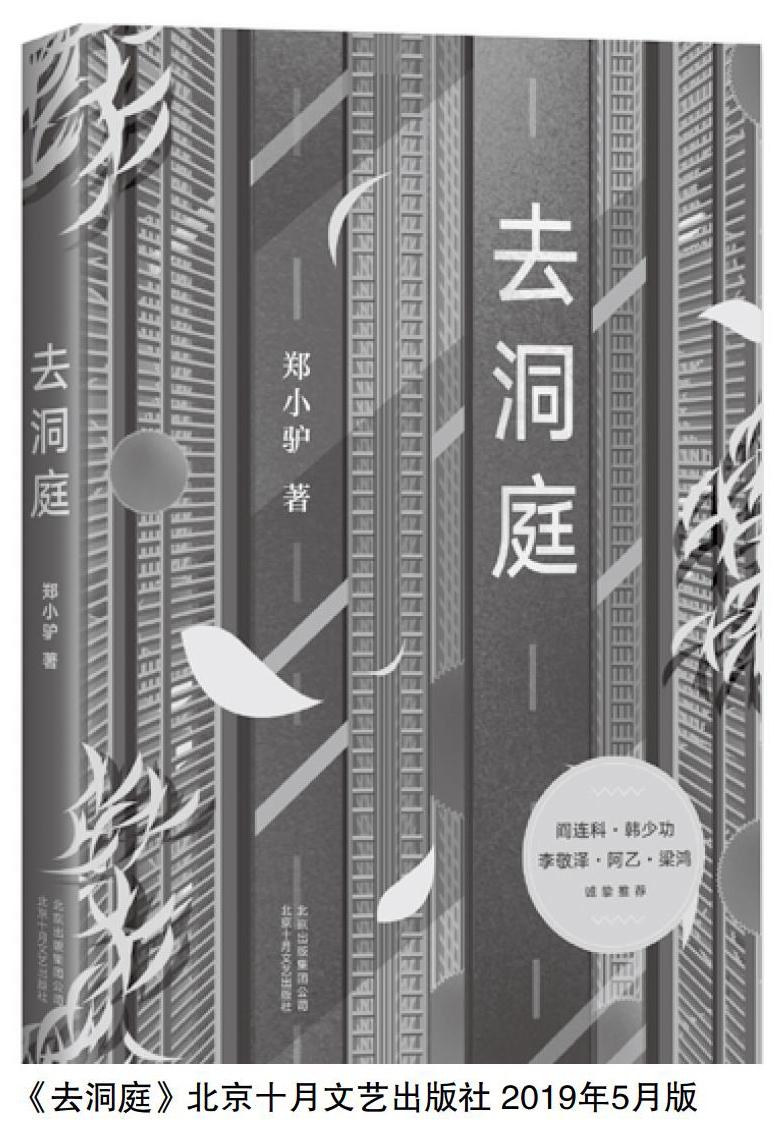
1
小說中有一節,小題為“壞人”,是寫耿直追岳廉,追得急了,“岳廉說,我干什么事了?我沒干對不起人的事。我不是壞人。小耿說,這個世界上誰是壞人呢?我也不是”。這兩個人的對話,讀后令人十分震驚。這兩個人的對活,仿佛在與上帝對話,也仿佛在與所有閱讀這部小說的讀者對話,更仿佛是與每一個人自己的內心深處對話。
小說正是寫的這樣五個自以為“我沒干對不起人的事”“我不是壞人”“這個世界上誰是壞人呢?我也不是”的人,正在“去洞庭”的故事。小說單行本的書名就是《去洞庭》,這個書名直奔目的地,但他們在“洞庭”的時間并不長,漫長的是“去洞庭的途中”,這是《十月·長篇小說》2019年刊發時的題名。這個題名似乎著眼的是去的“途中”。五個人的“途中”自然不一樣,而且十分復雜,但似乎又有些十分的類似。其實,現代人在現代性過程中遭遇大都如此。這部小說的意味或許也在于此。
大齡未婚女青年張舸碩士畢業,北上京城,邂逅東北小伙褚健,因無法在京購房愛情潰敗委地,又被假冒軍官騙色騙財,在現實中屢屢受挫,以致精神分裂,帶著心愛的鸚鵡,準備獨自遠走他鄉,卻遭意外綁架,正在“去洞庭的途中”;家境貧寒,父親又患上重病亟需錢的青年耿直,因為一念之差,鋌而走險,綁架一女人,驅車在“去洞庭的途中”發生意外車禍,為了能獲得一筆重金,被昔日的公司老板受雇去捉拿一人,始終不明白自己“去洞庭”的目的何在;中年商人史謙順風順水,家有嬌妻愛女,卻因自己生性風流,婚姻解體,幸遇佳人顧燁,生下小孩卻被檢測為非由己出,加之艷照風波,深感恥辱,在雇人捉拿情夫的同時,不動聲色地踏上了“去洞庭”的復仇之路;愛慕虛榮的女畫家顧燁,嫁給了比她大二十歲的商人,卻“厭惡丈夫的親吻”,一直在追尋“一個有趣的靈魂”,與一位青年作家出軌,數次與情人在洞庭湖和京城幽會,艷照傳出,沸沸揚揚,慶幸丈夫毫不知情,卻渾然不覺丈夫和她已經開始了“去洞庭”的最后旅程;青年作家岳廉在京城“陸續獲得了一些文學的名聲和關注”,自以為就是“天才”和“希望之星”而風流不羈,花人家的錢,玩人家的情,竟還給人家生下“骨肉”,在和情人在洞庭幽會的時候,沒有想到自己也會像自己寫偷情的小說《沉尸》一樣,沉尸湖底。洞庭湖本來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地方,但是,他們都沒有想到,這里會成為他們最后的死亡之地。正如小說中所寫,他們“自然是不想去洞庭的”,洞庭于他們而言,“是張巨大的網,是潮濕的沼澤,是危險的隱喻”。(《十月·長篇小說》2019年第1期,第230頁)
是的,這肯定是一個隱喻。寫作與世界的關系從來就不僅僅是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而應該是隱喻與象征的關系,這也正是小說之所以有意味和價值的原因。更有意味的是,鄭小驢的《去洞庭》釆用的顯然是一種可以稱之為“提喻”的藝術手法。按照海登·懷特的說法,與“換喻”和“隱喻”相比,“提喻則沿著另一個方向運動,它將所謂顯然是個別的現象整合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的性質使我們相信,可以將個體理解為一個宏觀總體的微觀世界,而這恰恰是一切有機論解釋系統的目標所在”。([美]海登·懷特:《話語的轉義》,董立河譯,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頁)
《去洞庭》不正是如此嗎?
2
小說的最后一節為“瓶中船”,寫大齡女青年張舸一共躺了三百零五天后,終于在某天下午醒了,“她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就像做了一場漫長的夢,一覺醒來,換了人間”。在夢中,她夢到“圖們”褚健,夢見“和他回東北老家。她穿著艷紅的婚紗,走在雪地上,咯噔咯噔的脆響不絕于耳,呼出的白汽迅速消散。他帶她去圖們江上溜冰、砸魚,教她做小雞燉蘑菇。她快活極了。她終于和他在一起了,無論貧賤與否,發誓永不分離”。但這終歸是一場夢,是被她輕而易舉放棄了的“一晌夢”。其實,誰的人生歷程不是“一晌夢”啊?但是,不知道為什么,誰也不好好去做這“一晌夢”,來個“一晌貪歡”。于是,“她還夢到其他許多的人。歡樂的,悲傷的,隱痛的,絕望的,那些模糊的黑影,他們是律師、lT程序員、文學青年、公務員、教師、蜂鳥外賣……與她在夢中擦肩而過,消失于陌生的街道,各自踏上不同的歸途”。文中遠方寄來的那個“瓶中船”,“用鹽水瓶裝著,里面臥著一艘精致的白色帆船”。父親說是東北寄來的,“我跟你媽研究半天,也沒搞明白這船是怎么塞進去的。你說瓶口這么小,哪兒裝得下這么大的船?太不可思議了。” (《十月·長篇小說》2019年第1期,第236、237頁)
張舸當然是不說話,“望著帆船發呆”。她知道這是“圖們”給她寄來的。她想起她和“圖們”在北京的那些快樂的日子。“他按照1:700的比例,制作了一艘木制帆船模型”,“他小心翼翼地拼裝龍骨,鋪甲板,拉繩索,掛帆,最后加上火炮、三眼滑車,甲板上還立著幾排栩栩如生的士兵,拉上國旗”。圣誕節那天,“他把這艘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制作而成的船模當圣誕禮物送給了她。她捧在手上,沉甸甸的,心里頓時一熱”。(同上,第183頁)可惜。她被現實所壓迫,又愛慕虛榮,沒有珍惜。“大吵過幾次,有一次她把他送的圣誕禮物,那艘花了他很長時間制作的船模摔了個粉碎。摔完了她后悔了,為了掩飾自己的懊惱,她朝他歇斯底里地吼,企圖激怒他。”(同上,第185)這就是現代人的命運,為了那些充滿光環的虛幻的東西,自己充滿活力的生命裝進了鹽水瓶里,成為“霧中花”“夢中人”。現在.張舸當然“好奇的不是它怎么進去的,而是怎樣出來。對她來說,它被困在里面了”。(同上,第237頁)可惜,現在一切都有些晚了,“她摩挲著瓶子,眼淚一下就下來了”。(同上,第237頁)
這當然是我們這些被時代與現實壓彎了腰的現代人人生的真實寫照,或者是一種比喻和象征。正如小說中那位青年作家岳廉所寫的,“不管在世界的何方,我短暫的一生都未曾真正快樂過。世界囚禁著我,我同樣囚禁著世界。我呼吸,我冷漠,我幻想,人死燈滅,每天都和死亡和欲望的使者搏斗”。(同上,第215頁)顧燁,還有好多女人,可能就是上帝給他派來的“死亡和欲望的使者”。岳廉又何嘗不是上帝給她派來的“死亡和欲望的使者”?“他是喜歡帶著她。以業余畫家和他女朋友的身份,各種場合都參加。她也樂于進入他的生活,人生百態,粉墨登場,在北京巨大的舞臺上,各自表演。導演、作家、演員、制片人、出版商、編輯、主持人、騙子、綠茶婊,眼花繚亂。有次在酒桌上還碰到一位當紅流量小生,一起玩殺人游戲到天亮。當然見得最多的,是一個個作為‘外省青年的漂泊者,有點才華,又不安于現狀,帶著夢想,來到北京,被這座巨獸般的城市一天天磨掉銳氣,喪失意志,最后泯然眾人矣。”(同上,第189頁)就是這樣,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年年地衰老是既成的事實。我依然單身,我駐守著空蕩,年輪是攫取我靈魂的怪圈。我渇望有一個地方,在死后收納這具空蕩的皮囊。那里有陽光,有鮮花,有泉水,有清澈的空氣。”“在冥想的世界里,那兒有真實的愛情,真實的花裙,真實的呼吸,真實的歡愉,真實的自由,我是我的王。”(同上,第215頁)
但是,我們在現代化的科技進步和社會變化不斷加速,越來越緊密地被捆綁到時代與現實當中,無法自拔,以至于與過往的空間、物、行動、時間、自我和社會不斷地物化或異化,都成為“有病的人”。對于一切人都向往的美好而自然的事物,只能成為“孤獨的囈語”。“我窮盡一生,追求黑暗之光,仍然被黑暗吞沒。”(同上,第232頁)
3
“這個世界,才華與野心之間,存在著一層微妙的關系。”(同上,第231頁)小說就是要呈現與揭示每一個人都存在的這“一層微妙的關系”。這是一部真正讓時代感凸顯、并且真正把時代事件拉入小說使它成為故事推力和?手的小說。這也是鄭小驢這十年多來寫得最有分量、完成度最高的一部小說。它最大的獨特性,不僅在于讓那些罹患現代性綜合癥的各色人等在同一時空中交錯匯聚,而且還在于這里面寫盡了作家對同時代人極為切身的痛楚感受,以及一個年輕而敏感的寫作者用盡身心之力試圖尋找答案的決心。《去洞庭》寫的都是一群某種意義上的失敗者和失意者。小說的核心人物史謙與前妻汪靈本來是“天作之合”,幾經打拼,兩人的事業和生活都漸入佳境。但史謙出軌了,因此離婚后,又找上了比自己小二十歲的文藝女青年顧燁。他能給了她相對富足和安穩的生活,卻給不了她充滿激情的生活。她竟然多次去和那位青年作家偷情并懷上了他的骨血。這一切讓史謙感到自己失敗了;準備用小說成就自己的岳廉,以為自己遇到了生命中貴人,除了給他帶來生活的激情,還給他帶來生存上的資助,直到最后他想回歸一份發自肺腑的情感的,已經為時已晚,被人送上了沉湖的不歸之路。這自然是一個失敗者;那個名叫耿直的小耿本來成績不差,憧憬考個好大學,從父母苦難的命運中脫胎換骨,卻因父親身患絕癥,缺錢就醫,只好放棄夙愿,打工謀生,典型的一般窮人孩子早當家的精神圖譜,沒想到被雇捉人,也走上了失敗者的道路;在北京經歷了一次次情感挫折,甚至被假冒軍人騙了的女碩士畢業生張舸,變得神經兮兮的,也是一個失敗者。但是,這些失敗者和失意者并不是天生的壞人,都認為自己并沒有做什么壞事,只不過是他們實在不甘于現實的庸常,卻又經不起云霧一樣的誘惑。這種時代與現實的迷失與悵然,讓他們的人生出現了不由自主的失控。買兇捉人的史謙,其實并不真想要妻子情人的命;愛上人妻的青年作家岳廉,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淹死在洞庭湖中,冥冥之中演繹了自己的小說情節。或許身處情惑漩渦中的文藝女青年顧燁最后因車禍昏迷算是幸運,但可能要面對終生靈魂的內疚自責。小耿失控了,他在瞬間的情欲涌來之時,強暴了張舸,很迅速地進入到了小說的縱深地帶,在小說的最后,他又失控把岳廉送進了他宿命般的洞庭湖。“小耿抬眼望了望天空,天空全是這些幻滅般的碎片,仿佛正在重新編織他的人生,讓人無法看穿,一時竟呆住了。”(同上,第236頁)
不是小說中的人物很容易失手和失控,而是所處的這個“野心時代”的人們,都容易被現實追趕得因慌慌張張而失手,甚至失控。人一旦失控,造成不可挽回的錯誤之后,就不再擁有自主權了,就很可能會沿著迷失自我的岔道,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推向了更深的絕境。這或許就是《去洞庭》這部小說通過這幾個因失手而人生失控的失敗者的故事要警醒我們的。正如作家在小說的“后記”中所言:“我相信筆下的這些故事和遭遇,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漩渦,或被礁石拍碎的瞬間。它們與我們的現實處境血脈相連,心靈共鳴,從而具有普遍的意義。這些迷霧制造者,在通往洞庭途中各自人生軌跡已悄然改變,此時的洞庭,已不僅是現實所指,也暗含了人生豐富的隱喻。” (同上,第239頁)
4
余華曾在《長篇小說的寫作》一文中說過:“與現實簽訂什么樣的合約,決定了一部作品完成后是什么樣的品格。因為一開始,作家就必須將作品的語感、敘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確立下來。也就是說,作家在一開始就應該讓自己明白,正在敘述中的作品是一個傳說,還是真實的故事?是荒誕的,還是現實的?或者兩者都有?”(《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頁)這種“簽約說”,其實就是作家與現實生活的一種清醒而又創作主體意識極強的寫作關系。為什么我們在一些所謂的現實主義小說中,既看不到我們所處時代的表征性生活,也看不到這個時代與現實中所有人的精神狀態。盡管這些小說跟生活一樣的真實,真的就是生活的翻版一樣,但就是讓你從中感受不到一點時代與現實中的活潑潑氣息和人活生生的感覺。真正的現實主義小說,總是作家與生活有一種最緊密而有效的“簽約”關系。他不是去鏡子般的寫實現實生活,而是找到了小說與生活最恰當的一種隱喻與象征的關系,他用虛構的偉大力量與想象翅膀寫出了現實生活最實在而真切的感覺和經驗。他在揭示和表達生活的復雜性和人性的多樣性方面,給我們提供了獨特而新鮮的經驗。他在注重藝術“意味”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對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心靈世界的真切關懷。《去洞庭》就是在試圖通過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從而揭示出隱含于表象背后的人的復雜性與人性的復雜性。它在極強的結構意識和敘事能力中,用一種瓷器般的敘述美感,寫出了我們所處的當下時代的人活生生的生存經驗與內在感受。
在小說“旅行”一節中,作家在寫到史謙與顧燁貌合神離的生活狀態時,是這樣寫的:“半夜,他酒醒,一陣窸窣,將手探入她睡衣,沒有征得她同意,一把按在身下,粗魯地對待她。黑暗中,她聽見他一直喃喃自語,嘴里吐出連串‘賤貨‘婊子‘蕩婦的字眼。她深感驚訝。他從未在她面前說過如此粗鄙的字眼。很快,他從她身上翻了下來,房間又恢復了黑一般的寂靜。沒過多久,她聽見一陣低沉的鼾聲。她卻再無睡意,頓時感到四肢百骸一陣虛空。繼而,恐慌和失措攫取了她。她惱羞地擰開床頭燈,猛然瞥見男人正睜眼望著她。”(《十月·長篇小說》2019年第1期,第221頁)這讓我想起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那部著名小說《沒有個性的人》中的一段描寫:“有一天晚上,狄奧蒂瑪和丈夫圖齊在一起睡覺時,又陷入到了對阿恩海姆的思念之中。熟睡的丈夫隱約聽見了妻子‘無限遙遠的哭泣聲,便突然從睡夢中驚起,在床上坐直了身子。他知道妻子醒著,就輕輕地呼喚著她的名字,并試圖撫慰她。他扳過妻子的頭,看到了妻子黑暗中的那張臉:她正惡狠狠地望著自己,露出悖逆的神色,甚至毫不掩飾自己的哭泣。他當然知道妻子的哭泣與情敵阿恩海姆有關。但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外交官,他知道安穩的睡眠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也是自己的主要美德。因此,他決定對妻子的痛苦不予理會,‘怒氣沖沖地一直睡到天亮。”(羅伯特·穆齊尓:《沒有個性的人》,張榮昌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頁)“同床異夢”的生活古今中外都有,但我以前覺得誰也沒有羅伯特·穆齊爾大師寫得真切而生動的了。可是,現在讀了《去洞庭》之后,覺得鄭小驢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寫得更符合我們當下這個時代與現實中人的真實感受。因為我們畢竟所處的時代不能和羅伯特·穆齊爾所處的20世紀上半葉相比,沒有那時的人含蓄而有教養,文明而有耐心,卻比那時的人粗魯而直接,缺乏愧疚而毫無羞恥感。
人,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種高級動物!
【作者簡介】馬明高,山西孝義市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在全國性文學報刊發表有小說、散文、文學評論六百余萬字。創作的電視劇《田野的風》《柳鎮細雨》《百歲老人侯佑誠》《酸棗坡》《黃土歌謠》等在央視與各省衛視播出。出版著作20余部,榮獲全國優秀電視劇獎、全國優秀電視藝術節目一等獎,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山西省文藝理論評論獎和趙樹理文學獎等10多個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