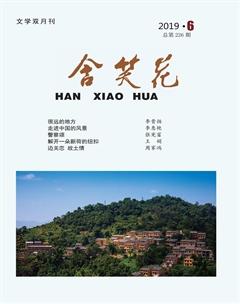詩人的天職是還鄉
楊鳳金
詩人荷爾德林步入其詩人生涯以后,他的全部詩作都是還鄉……
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接近極樂)。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這種對本源的接近,決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鄉才可親近本源,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為如此,那些被迫舍棄與本源的接近而離開故鄉的人,總是感到那么惆悵悔恨。既然故鄉的本質在于他接近極樂,那么還鄉又意味著什么呢?
還鄉就是返回與本源的親近。
認識周祖平老師應該近10年了。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而且當時我因為所在的單位也不是文藝部門,所以只是在業余時間寫點東西。但是,卻能得到周祖平老師的青睞,在文學創作上不斷鼓勵和支持,讓我逐步走上文學這條路。在此,再次感謝周老師這些年來的關心和幫助。
周祖平老師的作品在許多報刊、雜志都可以看見。而且在一些大型晚會都可以聽到有人朗誦到他的詩!我縱觀他的部分詩集,他的詩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對故鄉永不放棄的愛家、愛國、愛民意識。比如《親近南高原》《守望南高原》《南高原放歌》《山情》《山戀》等等,都是對家鄉對馬關的難割舍之情。唯有這樣的人方可還鄉!
周祖平老師在他鄉工作已很久,備嘗在異鄉的艱辛,現在又歸根返本。因為他在異鄉異地已經領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還鄉時得以有足夠豐富的閱歷……
海德格爾曾經說:“詩人的天職是還鄉”。自古以來,鄉愁、詩人、詩歌似乎有一種冥冥注定緊密相連的關系。從古代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到現代余光中筆下“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這些詩歌無不表達了一個主題,那就是故鄉情結。情結是一個心理學術語,指的是一群重要的無意識組合或是一種藏在一個人神秘的心理狀態中,強烈而無意識的沖動。故鄉情結作為人類情結的一個具體表現,是人對故鄉潛意識里的強烈情感。故鄉情結在漂泊在外的詩人筆下更顯得那么深刻,那么濃烈。
詩人的天職是還鄉,還鄉使故土成為親近本源之處。周祖平老師在他的詩集開篇就用了一首《說到馬關》的詩作為題頭,就是“致親人”的獻辭。他這樣說到:“說到馬關,暖流涌進心里,亞熱帶東部型季風/從老君山徐徐吹來,東來的紫氣輕撫馬關大地/馬關,紫氣輕撫的家鄉,地靈天杰,英雄輩出——馬關,中國草果之鄉,無論我走多遠/我的根依然在馬關,無論我飛多高/我的心依然在馬關,我心。在馬關飛翔——/馬關,我心靈的居所、我精神的守望”。讀到這樣的詩句,何以不讓我將詩吟誦給那些歷來生息于故鄉的人們?還鄉的詩人受到家鄉人急切的歡迎,他們似乎是親人,但他們又并非是親人,就是說,不是他——詩人的親人。
故鄉中的“故”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原來的;從前;舊的”,故鄉也就是相對于新的,現在生活的“鄉”,是一個人離開過的地方,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故鄉既是指離開,進入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祖先棲居父輩代代耕種的家園在城市文明的擠壓下,慢慢荒蕪起來,越來越多的鄉下人丟下父輩傳下的鋤頭,走出世代耕種的家園,紛紛涌上滿地是金子的城市,詩人也加入這個浩浩蕩蕩的隊伍中。周祖平老師在詩中這樣寫道:“這是個特別的日子/這是我人生的拐點 ?喜從天降/幸福說來就來 ?一紙調令/把我從學校調到支前辦——那是一段難得的經歷/那是令人回味的時光——”(《1989年8月:改行》),詩人崗位變動,離鄉背井,留給記憶的是家鄉每一座山、每一條河、每一棵樹、每一株草、每一寸土地……,在潛意識里,這種記憶勢必是深刻而刻骨的。在周祖平老師的詩中,他對城市的日新月異的變化,甚至是異化,始終懷著平和的心態去對待,正是因為這份冷靜,他執著近乎固執的認為自己是穿行在城市里的一個外鄉人。“所有漂泊在外的彝家漢/重回打開山門的彝山/定會和我一樣/耳邊轟響一個雄渾的聲音/——莫白喝彝山的水/白吃彝山的糧/枉為彝山漢”(《彝鄉之夜》)。從此可看,周老師一直沒有放棄自己是一個農家孩子,一個實實在在的彝家漢子!然而,詩人生活在這個被他肉身認可、精神背叛的城市。精神與肉體的分離實際上是鄉村與城市兩種文化的沖擊碰撞,這種碰撞不可避免地造成詩人身份的游離和復雜矛盾的尷尬處境。盡管他在城市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時刻受到城市的精神壓迫,心靈時刻在流浪,這就是周組平老師不停地在還鄉的原因。
周祖平老師牽掛著故鄉的一切,妙音天成的馬灑儂人古樂,激情狂歡的花山節,歌聲流淌的三月三、紙馬舞、弦子舞,都觸動著他的心靈,是他放之不下的故鄉——南高原!你看,在他筆下的風景:“太陽停止了旅行/棲息在西山那邊/勞累了一天的彝鄉/隱進了桃林/桃林撐一張月弓/篩落月光斑駁的碎影/阿黑錚錚的弦子聲/從夜空飄來/撩撥得阿乃的心直癢癢……”(《彝鄉之夜》);他寫家鄉,“關于五月 ?關于五月的家鄉馬關/有一首抒情詩已在構思/正在生長……”(《五月的家鄉》);他寫當年與同伴一起的日子,“想當年與興貴一起/暢游馬鞍山水庫/在水庫留下青春的印記/如今 ?我們已雪染雙鬢/馬鞍山水庫風采依舊/令我感慨不已——該留的留 ?該去的去”(《馬鞍山水庫》);他寫云海,“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云海上面是古林箐/云海下面是健康農場/乳白的海變換不停/一會兒海浪滔天/一會兒風平浪靜……令你喜歡令你憂”(《大吉廠云海》);他寫古碉樓,“烽火 ?狼煙 ?流血 ?陣亡/一切都好像離我們遠去/卻又好像就發生在眼前”(《叩問馬關石丫口古碉樓》);他寫國門,“用石塊壘就國門的人/早已作古/可他們壘國門的故事/卻常青常綠”(《茅坪國門》);他寫花山節,“不用號召不用吶喊/咪多咪彩笑意寫在臉上/擁向豎有花桿的地方/擁向花山擁向花桿/蘆笙舞 ?舞出苗嶺雄風/花山調 ?唱出苗嶺欣喜”(《何時去苗嶺》)。讀著這些讓人怦然心動的詩句,不期然想起一位攝影人的尋思——為何異鄉的美麗不能令你顫栗?只緣精神不在,故鄉不在啊。
周祖平老師摯愛著故鄉,疼痛著故鄉。他將一己的喜怒哀樂融入到故鄉的山川風物、命運歡悲、人情冷暖當中,如他自己所言:“說到馬關,撩撥得我的心直癢癢”。面對“以遙遠的村寨為家”的父老鄉親,面對他們在“卑微、艱辛的日子”所經歷的“俗世的痛和活著的傷”,他們“懷想、展望/抑或陷入深深困窘”的“疲憊、澀苦、艱辛”,以及“對于命運/無言的順從和堅忍”,詩人傾注著深切的關注、關愛、體恤與悲憫之情。詩集里有一首描寫水電工人的詩:“選擇了這職業/便選擇了孤寂與韌性/與山為伍/練就了你山一樣的性格/與水為伴/心與水一樣澄明。”寥寥幾筆,就勾勒與濃縮了無數家鄉人的艱辛和古樸。這不僅僅是故鄉人的寫照,也把詩人自己這些年來的堅持和秉性表達出來!
詩要么被視為一樁虛浮無聊之舉或者被視為向幻境的逃遁而遭拒絕,歸入不可知的領域,要么就被當作文學的一部分。文學作品的有效性,是由當時的現實性衡定的。詩是真正讓我們安居的東西。但是,我們通過什么達于安居之處呢?通過建筑?通過風光?還是通過詩人身邊的每一個人?我看來,應該都是,也都不是。我們面臨一種雙重的要求:一方面,我們由安居的本質來思被稱作人的生存這回事;另一方面,我們將思作為一種“故居”,即作為一種,也許甚至就是此種,獨特種類的建筑的詩的本質。如果我們循此尋求到詩的本質,也就把握到返鄉的本質。
詩人對故鄉的抒寫一方面是對在物質欲望熏染下的城市的本能拒絕,另一方面是詩人的精神臍帶仍然和自己的故鄉血脈相連。周祖平老師用真誠和良知堅守詩壇,表現了他們那一代“異鄉人”游離在城市與鄉村兩種身份認同的矛盾與尷尬,抒寫對城市異化下他們對故鄉情感的蘇醒和精神的復歸。也許他們是城市喧囂里的寂寞者,但一個“內心裝著故鄉行走的人”,他們的靈魂是不孤獨的,我們堅信周祖平老師會一直倔強的帶著故鄉行走,終究會抵達靈魂深處的故鄉。
“回頭問路,回鄉尋根”。這是我在上次評論周祖平老師的詩集《南高原放歌》的時候說的一句話,現在,用在這里也對!周祖平老師是一個懂得感恩的詩人。他詩歌的故鄉情結是對故鄉最好的感恩,是周祖平老師作為詩人個體最直接的感恩方式。
此愿,周祖平老師回故鄉的路越來越平,越來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