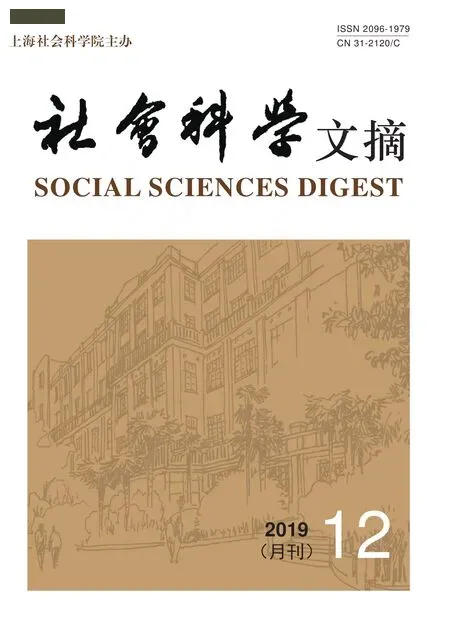新中國70年人權(quán)研究歷程及理論面向
文/劉鵬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jié)》篇末總結(jié)道:“思辨在多大程度上離開哲學家的書房而在證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德國人的理論興趣,只是在工人階級中還沒有衰退,繼續(xù)存在著。”“相反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以上論斷指明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使命”“科學研究目標”“工人主體地位”,這一論斷激發(fā)了社會主義理論在世界范圍的研究和實踐,引導了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國人權(quán)理論研究便是經(jīng)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立足國情,以人民的實質(zhì)平等為邏輯起點的探索,經(jīng)由人權(quán)理論的批判和深化,復歸人民的美好生活實現(xiàn)的辨證發(fā)展過程。在歷時性語境中,我國人權(quán)理論研究也得益于人權(quán)成為“全球道德思想的通用語”這一外在形勢。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quán)理論仍面臨著新時代的新需求,“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權(quán)”為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的自我塑造和闡釋提供了新的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世界治理秩序的闡發(fā),促使學界在國家之間、國際人權(quán)對話和交流中不斷地深入研討。新中國70年中,人權(quán)理論研究呈現(xiàn)出怎樣的發(fā)展脈絡?它具有怎樣的學術(shù)意義?哪些因素驅(qū)動著這些研究?未來研究應有哪些新的轉(zhuǎn)向與突破?這些人權(quán)理論命題在不同的視閾中得到不斷地反思與追問。
實質(zhì)平等到目標背離:革命話語中人權(quán)研究的消解與遮蔽(1949—1977)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變革意識形態(tài)和上層建筑提供了契機,而嚴峻的外部環(huán)境和內(nèi)部舊社會遺毒的存在,使得這一時期的人權(quán)理論研究相對于革命話語呈現(xiàn)脆弱性特征。20世紀中國思想界最宏大的現(xiàn)象,莫過于革命話語的興起與泛濫。革命法制的中心地位在理論研究中帶有深深的印記。這一時期,從人民享有廣泛的當家作主權(quán)利的法制奠基,到帶有鮮明意識形態(tài)特征的“三座大山”人權(quán)遺毒批判,再到后來“人權(quán)口號的徹底否定”,隨著革命話語的蔓延,人權(quán)理論研究逐步被遮蔽。
這一時期,起始于實質(zhì)平等人權(quán)為價值追求的理論研究,一方面促使人權(quán)基本命題得以奠基,另一方面在革命話語影響下逐步遭受了非理性批判。人權(quán)理論研究受這種“左”的思潮影響極大,并逐漸擴散至社會方方面面。搞建設讓位于更激進的革命,中國人權(quán)理論研究遭受了巨大的波折,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quán)利遭到嚴重侵害,教訓極為沉痛和深刻。在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沖擊下,以憲法為核心的基本權(quán)利體系的建構(gòu)初衷并沒有被堅持,“根本法”和“基本權(quán)利”功能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貫徹。這種主客觀之間的偏離,使得學界對“階級斗爭的作用”“基本權(quán)利與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問題的態(tài)度呈現(xiàn)出“左”的傾向,權(quán)利理論研究逐步被遮蔽。
解放思想到遮蔽破除:改革話語中人權(quán)研究的反思與確立(1978—1991)
20世紀70年代,我國主動融入國際社會,帶動了人權(quán)理論研究的興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了理論界思想遮蔽的破除,鄧小平“南方談話”擺脫姓“資”姓“社”的爭論。前一次是從哲學理念上突破,后一次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突破。人權(quán)研究在“中西之爭”的觀念破冰中反復追問,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人權(quán)觀念。高舉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的旗幟,理直氣壯地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權(quán)理論,在理論論爭中成為共識。隨著1991年我國首部人權(quán)白皮書《中國的人權(quán)狀況》發(fā)布,人權(quán)理論研究進入第一次高潮。這一時期,學界對于世界人權(quán)理論的引介、馬克思人權(quán)基本原理探究、公民基本權(quán)利來源、儒家與人權(quán)關(guān)系等命題的深入分析和理論研究,為社會主義人權(quán)的理論建構(gòu)提供了質(zhì)料基礎。人權(quán)的抽象性和具體性關(guān)系、理性批判與辨證分析、人權(quán)的傳統(tǒng)性和現(xiàn)代性反思,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成為重要思想進路,生存權(quán)成為我國的首要人權(quán)和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從白皮書到人權(quán)入憲:學術(shù)爭鳴中人權(quán)研究深化與擴展(1992—2003)
我國首部人權(quán)白皮書發(fā)布后,學術(shù)界的思想禁錮逐步打開。在人權(quán)理論的諸多問題上,新舊觀點不斷碰撞,人權(quán)思想的交鋒無論是深度上、廣度上,都超過了此前爭論,多個重要的社會主義人權(quán)基本命題借此達成階段性共識。這些論爭主要涵蓋五個方面:第一,人權(quán)性質(zhì)的爭鳴;第二,個體人權(quán)與集體人權(quán)爭鳴;第三,人權(quán)與主權(quán)的位階爭鳴;第四,人權(quán)的正當性爭鳴;第五,傳統(tǒng)性與現(xiàn)代性爭鳴。
思想解放帶給學界極大地研究熱情,學者搜集了大量的資料,為研究的深入和擴展起到了支撐作用。20世紀90年代,董云虎等編寫了《世界人權(quán)公約總覽》《總覽續(xù)編》《叢書》等七卷,近一千萬字,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逐步在爭鳴中形成了以生存權(quán)和發(fā)展權(quán)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人權(quán)理論進行哲學思辯、政治哲學思考、法社會學與人類學分析,積極探討社會主義人權(quán)的法治實現(xiàn)路徑。這些理論的深入研究,推動了“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首次載入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其后,不論是對國家人權(quán)外交政策發(fā)布、人權(quán)白皮書的撰寫,還是對國家人權(quán)計劃的制定,均產(chǎn)生了積極地影響。
憲制保障到命運共同:中國特色人權(quán)論域擴展及交流互鑒(2004—2019)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相繼被寫入憲法和黨章,開啟了人權(quán)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憲制體系下部門法人權(quán)理論研究與人權(quán)理論研究逐步呼應。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面臨著新議題:(1)舉旗定向,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的研究深化;(2)立足本土,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的觀念審視;(3)論域擴展,中國特色人權(quán)憲制理論深化與制度擴展;(4)交流互鑒,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闡釋和對外表達。
新的命題呼喚科學理論新的解釋力,理論界面臨著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體系持續(xù)優(yōu)化、新的環(huán)境中人權(quán)理論主客觀統(tǒng)一和具體命題研究等問題。人權(quán)理論研究在法治進程中,既形成了體現(xiàn)中國特色的宏觀理論和話語研究系統(tǒng),又在具體命題中不斷優(yōu)化著具體命題的微觀體系。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需要持續(xù)回應中國化和民族化諸多新命題,從而“以人民為中心”,漸次實施人權(quán)行動計劃,實現(xiàn)“美好生活”。世界范圍人權(quán)問題的協(xié)同治理,促使理論界更多地關(guān)注理論之于世界問題的整全性和融貫性方案,以及溝通和對話中的話語闡釋力。
新中國人權(quán)研究的理論面向
新中國70年中,中國人權(quán)理論經(jīng)歷了以實質(zhì)平等為目標,尋求民主和法治保障,到法治保障下實質(zhì)平等具體命題逐步展開和深入的研究歷程。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的中國化和民族化,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研究體系和古今中外人權(quán)思想歷史淵源構(gòu)成了人權(quán)研究的三大支柱。學界的持續(xù)追問歷經(jīng)主體覺醒、應然建構(gòu)和對話協(xié)作,理論研究學派初露端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人權(quán)問題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好”的追尋使得諸多命題仍然在不斷深化:如人權(quán)命題元認知與分析框架、學術(shù)自覺與理論體系、目標與方法的統(tǒng)一、議題追問與文明互鑒等。源自哲學、政治學、法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交叉,使得各學科理論研究逐步擴展和縱深,將人權(quán)研究基本命題置于廣闊的視閾中。“歷史是一張無縫隙的網(wǎng)”,由于樣本的龐雜性、解析問題角度和深度缺陷,全樣本分析和趨勢性判斷難以企及,希望借以下三點,總結(jié)并展望人權(quán)理論未來的發(fā)展。
1.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的中國化和民族化研究是中國特色人權(quán)研究不斷深入和擴展的理論面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quán)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研究校準,以中國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為導向,推進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思辯貫穿于理論批判和制度建構(gòu)各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學者便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封建舊制、西方人權(quán)虛偽性,因此,以憲法基本權(quán)利為基礎的理論研究得以奠基;改革開放后,學界圍繞馬克思主義論述評析爭鳴,破除了思想遮蔽;20世紀90年代,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貫穿理論爭鳴,推動著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的深化;2004年后,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又成為交叉學科命題研究中的思辯源泉。新時代人權(quán)研究逐步形成融貫的體系,即“以人民為中心”之主體性,“美好生活”之價值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世界關(guān)懷。人權(quán)理論也逐步由哲學和政治命題逐步向?qū)嵺`命題擴展,從建構(gòu)與西方不同的哲學和政治話語,到學術(shù)和大眾話語全面融貫鋪開,人權(quán)理論從“人的解放”提升到“實現(xiàn)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fā)展”這一人類終極目標。
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為人權(quán)研究的逐步深入提供了方法論指導。人權(quán)法哲學無疑為這一學科交叉的主題、方法、目標提供了重要方向和檢視工具,在批判和建構(gòu)中極大地改造著學術(shù)界。人權(quán)理論的問題導向及持續(xù)檢省深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民族化理論研究。首先,人權(quán)理論現(xiàn)代性思考成為人權(quán)命題中國化的一條進路。無論是人權(quán)基本原理中仍然存在爭議的問題,還是中國新時代人權(quán)理論研究和制度創(chuàng)新中的新的論域,均需以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哲學原理反復追問。實踐中秉持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對面臨的具體問題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從而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選準歷史與現(xiàn)實、理論與實踐結(jié)合的角度,分析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現(xiàn)代化的條件與機制、問題與對策,探究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中國化的生發(fā)理論與模式選擇。其次,人權(quán)理論的傳統(tǒng)性成為人權(quán)命題民族化的另一條進路。中華文明有著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和生成機理,有著諸多與區(qū)域相宜的人權(quán)觀念和制度資源。對歷史意蘊的深入挖掘是彌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斷裂的重要路徑,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人權(quán)理論探求真理和實現(xiàn)揚棄的內(nèi)在要求。對民族精神、風土人情和傳統(tǒng)文化在內(nèi)的問題的持續(xù)解析,是在發(fā)展現(xiàn)代人權(quán)理論與保持民族特殊性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使命。
2.“以人民為中心”是黨帶領(lǐng)人民實現(xiàn)中國特色人權(quán)的理論生成和實踐路徑的根本保障。從共同綱領(lǐng)和1954年憲法的基本權(quán)利的初心設定,黨和國家?guī)ьI(lǐng)學界對人權(quán)理論研究和實踐便成為我國自主發(fā)展人權(quán)事業(yè)的重要經(jīng)驗。從1954年憲法的大討論到反右擴大化中鄧小平同志的論斷;從“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研究破冰到人權(quán)“中西”理論定調(diào),“理直氣壯講人權(quán)”推動了人權(quán)理論研究的高潮;自1991年《中國人權(quán)狀況》首部白皮書問世,人權(quán)理論爭鳴推動了人權(quán)的憲制保障并載入黨章,人權(quán)理論研究實現(xiàn)了共識達成、新題涌現(xiàn)到人權(quán)元認知反復追尋的歷程;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美好生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闡發(fā),代表著主體、價值、秩序的人文關(guān)懷,以“生存權(quán)”和“發(fā)展權(quán)”為支柱的中國特色人權(quán)理論體系也在積極地融入世界。在這一進程中,獨立自主和實事求是理論研究的基本前提,解放思想是破除遮蔽和禁錮的重要武器。新時期,新的人權(quán)命題仍考驗著國內(nèi)外學界對人權(quán)理論研究的批判力、解釋力和建構(gòu)力。同時,在尊重文明的普遍性和多樣性前提下,理論界還面臨著命運共同體建構(gòu)過程中溝通與對話、闡釋和表達,以滿足復雜形勢下的世界治理中對人權(quán)理論的創(chuàng)新的需求。
70年來,黨領(lǐng)導人民推進依法治國是人權(quán)理論研究的重要保障,“人民的美好生活”成為人權(quán)理論研究的重要面向。“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是對既往人權(quán)保障經(jīng)驗的總結(jié),也是對“美好生活”的制度承諾。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人權(quán)入憲帶來了規(guī)范法學理論發(fā)展契機,人權(quán)理論研究對部門法研究的指導、國內(nèi)外法律淵源的統(tǒng)合、部門法研究的協(xié)同、部門法中的人權(quán)問題成為深化人權(quán)理論研究的重要基礎。黨的十七大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fā)展的權(quán)利。”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報告中載明,“加強人權(quán)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quán)利和自由”。黨的十九大報告以“美好生活”開篇,以為“美好生活”奮斗結(jié)尾,構(gòu)成了新時代“美好生活”的政治敘事,也是理論界持續(xù)深入研究的基本面向。人權(quán)白皮書、人權(quán)行動計劃、北京人權(quán)論壇、南南論壇等多種形式的交流,與人權(quán)國際論壇的參與共同搭建了“請進來、走出去”雙向互通的研究體系。面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人權(quán)多樣命題,理論界合作攻關(guān)、協(xié)同研討,極大地豐富著人權(quán)理論研究意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quán)”揭示了人權(quán)的本質(zhì)和真諦,反映了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的根本要求,集中體現(xiàn)了我們黨全部政治主張和實踐活動的初心與追求。
3.古今中外歷史淵源為人權(quán)理論研究提供他山之石,世界文明交流互鑒迫切需要中國人權(quán)特色理論的自我塑造和話語表達。雖然人權(quán)理論在西方有著較為深遠的研究基礎,但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世界人權(quán)理論研究熱潮發(fā)端于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話語的代際爭取中。我國的研究便是在這一歷史時代中,主動與國際社會融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理性甄別和自主選擇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對西方人權(quán)思想的探索和詮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求同存異原則下共同探討和互相交流的成果。溝通和對話加深了命運共同體下的人權(quán)理論研究,理論研究的深入推動了我國人權(quán)理論的學術(shù)自覺和自我塑造。我國學界對人權(quán)與文化、社會、道德等問題的跨學科研究,為人權(quán)制度化研究和實踐開始提供了智識支持。徐顯明指出,在人權(quán)理論上,我們已完全可以與西方國家進行對話,在一些本原性的問題上,我們有重大的貢獻。
人權(quán)研究是一個持續(xù)發(fā)展并不斷深入的進程,人權(quán)領(lǐng)域不同思想觀點的論證,說到底是價值理念和制度模式的交鋒,人權(quán)理論研究面臨著自我塑造、文明互鑒和闡釋表達的重要使命。首先,人權(quán)標識性術(shù)語體系的凝練較為迫切。在人權(quán)原理凝聚與系統(tǒng)化過程中,理論界仍需理性檢省現(xiàn)有分歧,正視人權(quán)普遍性和特殊性,尋找共同價值和訴求,提煉標識性學術(shù)用語,打造融通中外的理論框架和話語表達,在普惠中實現(xiàn)理論的自我塑造。其次,理論研究的“超越”有賴于更深入地文明互鑒。諸多理論命題需要國內(nèi)外學者立足世情和國情共同探索,如彌合文化多樣性和人權(quán)普遍性分歧,各國傳統(tǒng)文化中現(xiàn)代人權(quán)意蘊,建構(gòu)現(xiàn)代人權(quán)的核心要素,人權(quán)話語體系表達和闡釋等。“強調(diào)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不是要閉門造車、拒絕借鑒國外優(yōu)秀經(jīng)驗,更不是拿‘國情’和‘特色’做降低標準的‘理論擋箭牌’,而是要追求在充分認識特點的基礎上對特點的優(yōu)化和超越”。再次,理論研究的深化需要輔之以更具說服力的人權(quán)話語體系。新時代學界須立足中國傳統(tǒng)、國情、文明樣式,研究中國人權(quán)理論命題,探索具有民族性、原創(chuàng)新、時代性的話語體系,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人權(quán)理論體系,為世界人權(quán)理論貢獻中國經(jīng)驗、中國元素和中國心智,從而真正使中國人權(quán)話語變成世界人權(quán)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