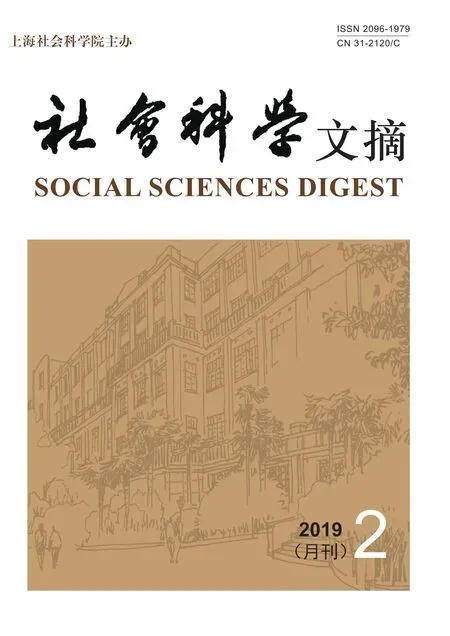從“理勢”互動到“體用”二分
——以清代中后期讀書人的世界觀轉型為中心
支配中國社會千余年的“天理”世界觀在清代中后期的瓦解,與嘉道年間讀書人在經學框架下重新思考“理勢”的問題密切相關。無論是今文經學、理學抑或經世之學,都在試圖重新回答何為“理”與“勢”以及如何重新詮釋“理勢”關系的思想命題。同時,正是基于對“理勢”關系及其詮釋策略的內在調整,拓展了朝野各界因應時勢的理論視野,也形塑了當日讀書人世界觀轉型的歷史進程。可以說,清代中后期的多元思想“內變”,既是對傳統“天理”世界觀修正與揚棄、推陳而出新的過程,也由此埋下19世紀90年代以至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世俗轉型的歷史伏筆。
“時勢”與“變易”:“天理”世界觀的內在轉型
自宋代以來,在理學支配之下,儒家“天理”世界觀逐漸成為支配中國政治思想與道德觀念的正當性依據。有賴于“天理”概念的確立,儒家讀書人通過“天理”世界觀重建以人的倫理秩序為軸心的道德體系。同時,“天理”世界觀強調現實世界對于天的政治責任、強調“天理”與政治、道德結合的傾向,不斷向更深層次發展,構成支配未來數百年中國社會道德實踐、文化認同和王朝政治正當性的核心依據。然而,進入18世紀以來,清代政治社會危機的持續爆發,帶來讀書人思想主張和學術旨趣的漸變。這使得自乾、嘉以來,作為讀書人理解國家政治基本視野的“天理”世界觀開始發生“內變”。在全球化的歷史情勢與數千年來培植政治觀念的經學傳統的共同催化之下,從18世紀儒家思想體系的內部,衍生出讀書人對于王朝內外關系和政治制度變革的重新思索。
延續千年的“天理”世界觀在清代中后期的歷史轉型,是儒家學術思想自身的內在張力與彼時社會動蕩的外緣刺激交互作用的結果。正如清初儒者以切實的“道問學”的經學方式,表達對于晚明王學末流“空辨心性”的批判那樣,18世紀的今文學者開始積極主動地從清代政治和社會關系的內部,尋求一種更能合理地平衡“理”與“勢”的制度嘗試。而此時經學表達方式的改變,從思想本質上看,其實正是“天理”世界觀不斷“內變”在學術上的必然反應。因此,如何借助變動不居的視野,通過對于“理勢”互動的敏銳理解,實現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新詮釋和政治制度的不斷完善,不僅是這一時期思想發展的深層動力,也使得今文經學成為清代后期日趨廣泛的政治變革的合奏當中一個嘹亮的聲部。
“理勢合一”:今文經學與“天理”世界觀的“內變”
18世紀今文經學的勃興,為讀書人針對內外時勢所進行的道德與政治評價,進而思考新的因應策略,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想契機。一方面,今文學者所倡導的“通經”、“明經”的主張,其思想實質是力圖從儒家經典的內部,依托制度變革,探尋“經世濟民”的政治策略。因此,圍繞“時勢”與“變易”現實前提展開的今文經學,其背后的深層動力,是讀書人世界觀初步的“內變”。同時,依托于儒家經典的理論張力,今文經學依然深受傳統“天理”世界觀的支配。這使得經學、王朝政治合法性與政治詮釋三者的結合,體現出今文學者與清朝國家正統學說在思想上一致而非對立的立場。
作為傳統中國“天理”世界觀支配下的重要哲學范疇,“勢”指力量的強弱及總體趨勢的不斷變化,意味著戰略上的發展趨勢和演變形式中蘊含的力量與潛能。出于對“勢”的意涵的豐富理解,讀書人推衍出對學術風氣、政治局勢、社會發展趨勢的進一步裁斷與把握。可見,“勢”具有造成社會變動外在力量的現實意涵,也與支配社會發展趨向和道德評價的“天理”,構成密切互動的思想關系。理解“勢”及其內外條件的關系,洞悉“勢變”的基本走向,進而以更具功利和權變的姿態提出因應策略,必然成為身處危機時代的晚清讀書人的重要思想使命。
因此,這一時期的今文學者,通過強化儒家思想當中古已有之的“經世”觀念,將“天理”世界觀所包含的諸多制度原則(“理”),從傳統的經、史所構建的道德范疇之中解放出來,組織成為因應“時勢”的“自改革”方案,進而從經學范疇內部,開啟了這一時期對于“天理”世界觀“內變”的新闡釋。龔自珍試圖藉助公羊“三世說”,捕捉“古之世”、“今之世”與“后之世”之間如風一般“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的“時勢”變化。龔自珍強調“規世運為法”,從“順/逆”的角度來看待時勢,將“順”與“逆”視為互相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取代,從而引起“時勢”變動的力量。“三世說”中所蘊含的線性演化因素,之后通過龔自珍以及好友魏源的論述得以強化,極大影響到后世讀書人對于歷史發展的看法。
在魏源的思想脈絡中,從早期《老子本義》的“以道治器”,到中期的《詩古微》的“三統說”,再到晚期的天道循環論,其中內涵雖頗多反復曲折,然其脈絡大致是強調“時勢”的變換有其循環規律,“勢”永遠在“道”的軌跡中運轉。當此之時,面對“世變日亟”的時代刺激,“理勢合一”的論說表現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上,即主張由制度的安排、政策的運用以及法令規范的約束,以達到儒家所謂的“治平”的理想。
從龔自珍內心彌漫的強烈的“衰世”意識,到魏源因應時勢而戮力編纂《皇朝經世文編》的努力,當日讀書人已經敏銳感知自身所處的時代特征——“惟王變而霸道,德變而功利,此運會所趨,即祖宗亦不能不聽其自變。”而“時勢”之變,最直接的后果是帶來了讀書人對于世界觀的修正。龔、魏均認為,在“王道”取代“霸道”的“時勢”壓力下,單純依靠傳統“內圣”的道德修養,已經不足以實現經世濟民的目的,尚需外在的事功(政策措施)和稅收、鹽政、邊防、漕運與軍制等專業知識作為補充。因此,對嘉、道以降的讀書人而言,歷史不僅是一個“祖宗亦不能不聽其自變”的道德衰替的過程,同時也包含時勢發展的世俗化趨勢——“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此后,歷史發展的價值訴求,不再局限于“王道”的道德空談,而是強調通過對時勢的認知與把握,不斷提升并強化國家治理能力,進一步擴大讀書人的政治參與,從而建立起“王道”與“霸道”之間新的平衡。
“以禮經世”:理、勢互動的道德認知
清代中葉以來,時勢刺激之下的世界觀轉型,并不局限于今文經學的理論框架與知識范疇,而是彼時讀書人面對“尊德性”與“道問學”思想之爭(漢宋之爭)所尋求的另一共識。理學與今文經學,從不同層面促成傳統儒家“天理”世界觀的深度演變,共同形塑重視實際事務、因應時局演變的經世傳統。從戴震、程瑤田到凌廷堪以降興起的“以禮代理”新思潮,意味著“天理”世界觀逐漸從宋明理學的形而上形式,積極轉向“禮學治世”的實用形式。
“以禮代理”的思想在18世紀的興起,并非簡單學術門派上的分野,而是從理學內部對“理勢”關系及其平衡策略的重新理解。它嘗試改變在“天理”世界觀支配之下讀書人因應時勢時所采用的心性論取向,拓展他們思考道德與政治問題的新空間。但“以禮代理”的思想趨勢中,對于“禮”的意涵的高度重視與重新提煉,又使得儒學內部道德論的主張被重新激活,為清代中葉理學家“以禮經世”的道德轉向提供了依據。19世紀中葉,湖南人曾國藩正是以宋儒義理之學成就經世大業的清代中興名臣,也是這一時期“禮學經世”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
這一“禮學經世”的嘗試,在曾國藩的世界觀認知當中,呈現出幾個不同的層次。首先,在“天理”世界觀的支配之下,曾國藩嘗試借助重整禮學,構建起漢、宋之間的學術關聯,以此化解清代中葉以來兩者之間的紛爭。因此,清代學者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的學術分歧,只有通過對于“禮”的重新研習,方能得以彌合。從更為本質的意義上看,曾國藩調和漢宋的努力,是在儒家道德義理層面,對宋儒“格物窮理”的信念與清儒“實事求是”的精神的一次貫通理解。
其次,曾國藩“以禮經世”的思想努力,顯然不僅僅局限于清代學者漢、宋之爭的學術范疇,而是延伸到對于時勢表達出深度關切的經世之學。曾國藩一方面肯定“理勢合一”,強調“理勢并審,體用兼備”。另一方面,曾國藩也認為“禮”不僅指涉禮儀與德性,更包含了制度與政法的內容。禮的意義不僅在于修身處世,也在于治國經世。“兼及內外”由此成為嘉道之際經世實踐的核心理念。因此,曾國藩的救國方案分為兩方面進行:一方面要衛舊,通過恢復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學精神來改造社會;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堅船利炮的實用技術來提升王朝實力。因此,在19世紀中葉讀書人心目中,曾國藩既是重視“明道救世”的理學名臣,也是重視事功的經世大儒。
從更長時段來看,曾國藩通過“以禮經世”為“理”與“勢”之間的平衡尋求道德的依據,對于清代中后期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直至20世紀的諸多改革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以禮經世”意味著,經世與變革的思想與實踐,并不以否定“天理”世界觀作為導向。另一方面,“以禮經世”同樣以一種道德實用主義的態度,為讀書人反思如何平衡“理”與“勢”的矛盾糾葛,提供了經學的理論依據與實踐范式,也為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等新一代讀書人,提供了突破經學藩籬的潛在動力與內在依據。
“環球大勢”的刺激:尋求富強與“體用”二分
伴隨19世紀中后期朝野各界尋求富強的整體努力,“勢”的比重在“天理”世界觀當中日漸凸顯。它不僅成為士大夫研判內外時勢的一般認知,也為“天理”世界觀的深度轉型提供了思想的內部動力。正是基于對“時勢”巨大動力更為深切的認知,在清代中后期的部分士大夫眼中,世界是一個在時勢推動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而讀書人自身也必須在“求變”中順應時勢——而非如同他們的祖輩那樣,兢兢業業致力于“復興三代”的道德使命。
身處于這一“天心”與“人事”愈加變動不居的時代,順應時勢的基本路徑就從龔自珍、魏源時代的“重估功利”,提升為“興功利”以自強。因此,“自強”成為這一時期士大夫的精神目標,而洋務實踐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策略。與此同時,部分士大夫對“勢”的討論,亦已逐漸超越科學新知、技術以及商務的內容,開始涉及政治制度與民主思想的內容。鄭觀應強調,“達民欲”和“與民協商”正是《周禮》、《論語》等儒家經典的古意,與西方議院思想溝通吻合。薛福成在《出使日記》里,就其在歐洲所見寫道:“民主之國,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廣益,曲順輿情;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縱其無等之欲。”王韜更進一步指出,英國富強的根本在于上下協調,特別是“通下情”的政府機構。他大力贊揚西方議會政治的作用,認為只有“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才能真正做到“有公而無私,民無不服也”。
到了19世紀90年代,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當中,嘗試沿用自洋務運動以來即已喧騰眾口的“體用”論述,對中學與西學的合理融通,作出更為系統的闡釋。《勸學篇》著力闡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實際上暗示在讀書人的一般認知當中,當時兩類“體用”(道器)并存的現實業已存在。因此,張之洞將針對時勢的因應策略,理解為限定在“器”的領域所進行的改革,竭力以西方的“器”來求變通,以中國之“道”來固國本。可見,在張之洞“體用”二分的思想背后,依然貫穿清初以來“天理”世界觀“兼內外”的思想脈絡,也不難找到19世紀中葉以來“道器貫通”的理念。
然而,“中體西用”之說意味著傳統儒家的道德價值只能在“體”的層面發揮作用,而在“用”的層面上,則不得不采用西力所引入知識與技術的尺度。換言之,“體”與“用”之間的關聯,在道德意義上的相關性已大為弱化。儒家德性的價值逐漸只在“體”的意義上發揮作用,卻必須從“用”的層面悄然引退。面對現實的時勢,張之洞在著力守衛傳統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卻又同時在“天理”世界觀之上打開了缺口。“體用二分”的思考方式,也開啟了未來中國變革的契機。中西、體用、內外等范疇的界定,在時勢的刺激下,隨后亦成為20世紀讀書人持續思索的世界觀議題。
余論
從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葉,面對一連串內外危機的刺激,清代中后期讀書人的世界觀發生了從“理勢”互動到“體用”二分的思想“內變”。首先,在莊存與、劉逢祿的時代,今文學者開始以“變易”作為理論預設,借助“時勢”表達對現實政治的干預以及對清代中葉以來“六經皆史”、“道器一體”等學術議題的重新理解。在繼之而起的龔自珍、魏源等人的論述當中,他們依托今文經學對于“理勢合一”這一思想關系的強調,將“天理”世界觀所包含的諸多制度原則(“理”),從傳統的經、史所構建的道德范疇之中解放出來,組織成為因應“時勢”的“自改革”方案,進而開啟了這一時期“天理”世界觀的“內變”。另一方面,在“尊德性”與“道問學”的思想之爭(漢宋之爭)的合力作用之下,理學與今文經學均從思想的不同層面,促成傳統儒家“天理”世界觀的深度演變,并且共同形成重視實際事務、因應時局演變的經世傳統。
其次,在傳統經學的思想范疇中,“理之是非”的剛性價值原則,開始在“勢之利害”的現實主義和世俗邏輯面前節節敗退。這一世界觀的嬗變,折射出自18世紀末期以來,晚清社會所面臨的儒家道德超越價值不斷衰退的“世俗化”進程。讀書人以更具權變和實用性的思路,消解傳統儒家德性與現實制度之間的價值關聯。同時,清代中后期的讀書人清楚地意識到,朝野各界如果無法在儒學內部,有效地發展出因應這一“世俗轉型”思想策略,進而從國家政權的內、外視角重塑晚清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現代形態與王朝合法性的根基,在西力日漸強勁的沖擊之下,儒學自身將無法擺脫最終衰亡的命運。
最后,讀書人的世界觀所發生的從“理勢”互動到“體用”二分的轉型,以一種從儒家思想邊緣深入到中心的節奏,部分地協助朝野雙方回應日漸急迫的內外時勢。隨著“天下”觀念的瓦解,中國最終亦無法自外于全球化帶來的新的世界體系。經學最終也無法為晚清的朝野各界,提供一個解釋世界和內外關系的整全性知識體系。因此,晚清中國面臨的“天朝的崩潰”,其實質正是支配中國千余年的“天理”世界觀的崩潰。在這一大的思想背景之下,“體用二分”為轉型時代的中國描繪出因應時局的“未完成的方案”,也由此開啟了晚清讀書人探尋新世界觀的復雜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