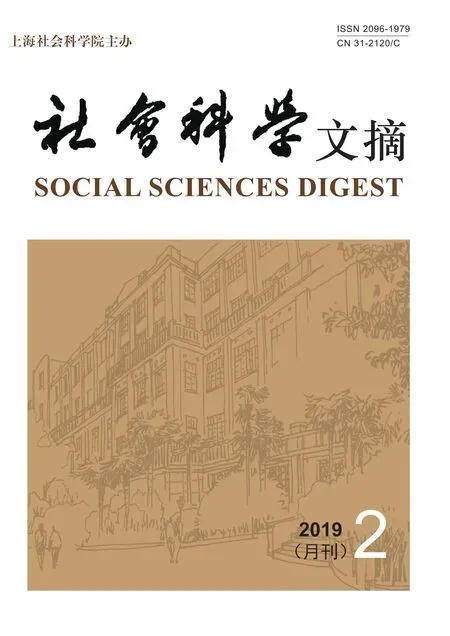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
當前我國共享(分享)經濟發展迅猛。據統計,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員工數約716萬,比上年增加131萬。2017年我國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人數超過7億,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7000萬。由于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員工,以及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龐大且急劇增長,共享經濟所涉及的勞動法問題極為重要。理論上,平臺服務提供者與平臺是否建立勞動關系,這一群體是否受勞動法保護,傳統的“勞動者”概念或“勞動關系”判斷標準是否已經過時等問題,是勞動法應予以應對的關鍵議題。實踐中,勞動關系認定也是與互聯網有關的勞動爭議案件的焦點問題。
傳統勞動關系概念和判定理論的核心及主要特征
通說認為,從屬性是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關系以及保護對象——勞動者(雇員)——的基本特征。勞動契約的本質屬性在于雇員的從屬性。從德國和美國的勞動關系理論可以總結出勞動關系和雇員判定標準的主要特征,認識這些特征則是分析如何認定互聯網時代勞動關系的重要基礎。
第一,勞動關系概念是以20世紀初工業化時代的勞動關系特征為原型的。勞動關系及從屬性概念主要建立在工業化時代,以傳統工廠為基本模型而形成和發展的。由于勞動關系理論主要確立于20世紀上半葉,而勞動關系以及現實中用工形式復雜多樣且不斷發展變化,因而傳統勞動關系的判斷理論和方法在當今時代,尤其是網絡時代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戰。第二,勞動關系的判斷標準具有相當的彈性。由于現實中勞動關系復雜多樣,在法律上難以具體、明確界定勞動關系的概念和判斷方法,因此,立法或判例規則對勞動關系一般僅提供相對抽象的概念和原則。無論是德國“從屬性”理論,還是美國“控制”標準或“經濟現實”標準,不僅概念本身富有彈性,相應的判斷因素亦是復雜多樣,且存在理論上的爭議。第三,勞動關系概念和理論具有很強的適應性。無論是德國“從屬性”理論還是美國“控制”理論,雖然經歷了約一個世紀,但其核心要義并沒有實質變化。究其原因,一是這些理論本身揭示了勞動關系與其他民事關系,尤其是承攬、一般雇傭關系的本質區別;二是這些概念和理論本身具有很大的彈性和包容性。法官可以在司法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第四,勞動關系認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德國、美國的理論都強調個案中需綜合考慮全部事實以及所有因素,而且都強調沒有任何單一因素是決定性或不可或缺的。因此,勞動關系的判定結果往往難以預測,因人而異,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互聯網平臺用工的勞動關系判定實踐及面臨的挑戰
(一)美德兩國勞動關系判定的實踐及面臨的挑戰
網絡平臺用工具有許多有別于傳統用工形式的特點,并且在現實中出現了許多訴訟和糾紛。美國、德國的平臺經濟走在世界前列,有關網絡平臺用工的爭議案件較多并廣受關注,對其實踐的考察于我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截至目前,美國法院并沒有一般性地確立平臺工人的“雇員”地位。在美國,關于網絡平臺工人的身份判定,許多案件本可以對此問題提供裁判規則,但由于案件采取或很可能采取和解方式,加上判斷勞動者身份的標準模糊,法院未來如何處理這一問題仍具有不確定性。在德國,按照傳統的從屬性標準判斷平臺工人的勞動者身份也是困難重重。眾包工作(crowdwork)存在不同的商業模式:在一些模式中,眾包商(crowdsourcer)和眾包工(crowdworker)之間可能存在合同關系,甚至是勞動關系;而在另一些模式中,眾包工則和平臺可能存在合同關系,甚至是勞動關系。但是,眾包工往往因缺乏從屬性(融入雇主)無法被認定為雇員。總體看,認定眾包工為雇員面臨巨大困難。
(二)我國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的實踐及面臨的挑戰
由于我國互聯網技術以及平臺經濟發展較快,與互聯網平臺有關的勞動爭議案件越來越多。從典型案例看,由于平臺用工的具體方式并不相同,加上勞動關系判斷標準較為彈性,司法實踐對平臺用工勞動關系的認定并不統一。
概括案例,我國網絡平臺用工勞動糾紛的司法實踐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法官在大部分案件中都不認可網絡平臺用工勞動關系的存在,只有少部分案件明確認定勞動關系,還有個別案件認定雙方存在雇傭關系,一些案件法官直接否定勞動關系或雇傭關系的存在,同時,很多案件法官回避了平臺公司和平臺工人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第二,在處理結果上,類似案件可能存在不同的判決。例如,原告同是代駕司機,被告經營模式也基本相同,但二者的法律關系在不同案件中認定不同。第三,當司機等平臺服務提供者造成第三人損害時,法院往往傾向于判決平臺公司承擔責任,即“損害結果同勞動關系認定呈現較強的相關性”。至于平臺公司承擔責任的法律基礎,法院有時按侵權責任法的規則,有時認定雙方存在雇傭關系,有時則回避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性質。值得關注的是,法院在一些案件中認定平臺工人和平臺公司之間存在雇傭關系,這一做法值得反思。
綜上,不管在美國、德國,還是我國,網絡平臺用工的特點的確使傳統勞動關系判定標準理論遭遇了嚴峻挑戰。特別是,平臺用工的一些新特點與經典勞動關系存在較大差異,使得平臺用工的一些因素將司機等平臺工人指向勞動者,一些因素則指向獨立承包人,法官往往陷入兩難選擇,難以認定平臺工人的勞動者身份。但是,根據以上國家的實踐是否可以認為傳統勞動關系判定標準理論已經過時了?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尚早。
傳統勞動關系判定理論過時了嗎?
相比傳統或經典勞動關系,互聯網平臺用工具有幾個突出特點,使其與經典勞動關系存在較大差異,這些特點也使網絡平臺勞動關系的認定更加困難。第一,許多平臺工人享有較強的自主性,包括是否提供服務、提供多少服務、何時何地提供服務等,而傳統勞動者不能自由決定是否工作以及工作的數量、時間和地點。第二,在很多情況下,工人自己提供設備和工具,包括車輛等進行服務,而傳統勞動者一般由雇主提供設備和工具。第三,很多平臺用工實行計件工資而不是計時工資,而且工資支付幾乎是實時支付。傳統勞動者一般都是計時工資,且工資按一定周期支付。第四,平臺工人的報酬一般來自和平臺按比例的分成,而傳統勞動者工資一般是固定的,與雇主的營業收入并不直接掛鉤。第五,平臺對服務提供者的監督一般借助于顧客,通過顧客的評級制度等方式,實現對平臺工人的監督。在傳統勞動關系中,雇主對雇員的管理和監督一般都由雇主完成。第六,從業人員準入門檻較低,進入退出自由。平臺工人加入平臺的程序較為簡單,往往通過在線操作和有關證書的審核即可完成,平臺工人退出平臺的程序也較為簡單,而傳統勞動關系中,雇主對雇員的招聘程序較為嚴格。這幾個特點,尤其是第一個特點,是對傳統勞動關系“從屬性”或“控制”因素的強有力否定,使平臺用工勞動關系的認定遇到了強烈挑戰,法官也往往陷入困境。即便如此,傳統的勞動關系判定標準理論并沒有完全過時,在網絡平臺用工背景下,傳統理論仍有適用空間,無需徹底顛覆或者放棄。
(一)網絡時代沒有改變雇員從屬性的實質
網絡時代需要對從屬性包含的諸因素的判斷方式進行反思和更新。傳統的用工強調雇主對雇員工作時間和地點的控制,但在網絡時代,由于技術發展,雇主對雇員的控制方式和手段發生變化,尤其是在某些行業,雇主對雇員工作時間和地點的嚴格控制失去了原有意義,雇主選擇通過其他方式施加控制。同時,雖然網絡平臺對服務提供者是否提供服務、服務時間、服務地點表面上減少控制了,但許多平臺對服務提供者其他方面的控制和管理加強了。網絡平臺用工的其他特點,也非對傳統勞動關系特征的顛覆。其一,工人在很多情況下自己提供工具,正是共享經濟的重要特征,是現代經濟資源共享的重要體現,并不會影響從屬性的實質。其二,很多平臺用工實行計件工資而不是計時工資,這一現象在傳統勞動關系中既已出現,并非新鮮事物。平臺用工工資實行實時支付主要是源于支付手段的技術發展,尤其是移動支付技術的進步,使實時支付成為可能。在傳統勞動關系中,由于支付方式落后、支付成本較高,通常以月為周期計算工資,但也存在以周等為周期計算和支付工資的。目前也存在許多按一定周期結算平臺工人報酬的平臺公司。因此,工資或報酬的支付方式和支付周期并不影響勞動關系的實質。其三,很多平臺工人的報酬來自和平臺收入按比例的分成,主要是因為平臺的收入主要來自工人提供的服務,而服務價格可以量化,加上平臺往往無需計算傳統企業場地、設備、原材料等成本,因此,平臺和工人可以直接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分成,這也是由服務內容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沒有改變勞動關系的本質。而且,傳統的用工關系中勞動者按收入比例“提成”獲取工資的做法也早已存在。綜上,平臺工人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且具有與傳統勞動關系不同的一些特征,并不意味著從屬性的缺失以及勞動關系的否認。
(二)經濟從屬性的重要性和地位凸顯
由于網絡技術的發展,服務提供者在是否工作、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等人格從屬性上的表面特征有所減弱,因此,經濟從屬性在判斷勞動關系是否存在上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網絡平臺企業往往否認經濟從屬性,即宣稱平臺公司只是一個網絡技術公司或信息服務公司,并不提供具體業務或服務,并以此為由,否認平臺工人與平臺公司之間勞動關系的存在。以交通出行網絡平臺為例,從各方面看,Uber等交通出行平臺公司,并不能否認提供出行服務是平臺公司的業務。因此,從經濟從屬性角度,尤其是平臺業務的歸屬看,網絡平臺企業和工人完全可能建立勞動關系。
(三)運用現有勞動關系判定標準依然可以判定勞動關系的存否
從美國、德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相關實踐來看,傳統的勞動關系判斷理論和判斷方法并未走到盡頭,毫無用武之地;相反,這些國家運用傳統勞動關系判定理論,通過通盤考慮各方因素,仍然可以作出勞動關系存否的裁判。在英國,關于Uber等網約車司機的身份,2016年倫敦勞動法庭的一個判決給出了明確答案。在美國,雖然法官在Uber等案中并沒有就司機是否是雇員作出明確判定,但法官認可當事人通過賠償達成和解的態度實質上支持了司機的訴求,特別是當和解金額不高時,法官對和解方案的否定,事實上也表明了法官支持司機的態度。在我國網絡平臺用工勞動關系認定的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可能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平臺對服務提供者的管理、服務是平臺公司的業務組成部分等而認定勞動關系存在,并非僅因服務提供者具有較強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而否定勞動關系的存在,最典型的是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閃送”平臺案。
勞動關系判定方法的改進及我國相關規則的完善
(一)互聯網背景下勞動關系判定方法的改進
盡管傳統勞動關系判定理論總體上并沒有過時,但面臨網絡平臺用工形式與傳統用工形式的差異,勞動關系的判定方法也應與時俱進。第一,平臺用工模式各不相同,勞動關系判斷還需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進行個案處理。第二,對從屬性的判斷應該更加注重實質性。隨著技術發展,平臺公司對工人控制和管理的方式更加隱蔽和復雜,對人格從屬性和經濟從屬性的判斷應注重綜合性、實質性的考察。第三,平臺工人的工作時間和收入來源也是考慮的重要因素。根據傳統勞動關系判斷標準,工作的持續性以及工作時長就是勞動關系判定應該考慮的因素之一。第四,社會保護的必要性也是勞動關系判定應考慮的重要因素。勞動關系的判斷標準雖然是一套客觀標準,但由于其本身的彈性和包容性,勞動關系的認定也具有相當的主觀性。因此,在認定服務提供者是否是勞動者時,也應考慮對其保護的必要性。
(二)我國勞動關系判斷規則的完善
勞動關系判斷理論及其規則的適用,始終是勞動法的核心問題。從勞動法司法實踐看,勞動關系認定始終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目前,我國在司法實踐中,對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主要采用我國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5年頒布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該《通知》明確了勞動關系判斷的基本方法。但拋開《通知》本身的制定主體和效力,該條內容也存在不足。面對網絡平臺用工的新特點,該辦法也需要完善。考慮到我國缺乏判例法的傳統,我國應當通過一定方式對勞動關系進行界定,以利于司法實踐的準確適用和裁判統一。由于在勞動法或勞動合同法等立法中界定勞動關系的概念和判斷方法難度較大,目前比較可行的辦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規則對勞動關系進行界定,對勞動關系可以進行概括式界定,突出人格從屬性,同時列明判定勞動關系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目前,沒有必要也不應專門針對網絡平臺用工群體制定專門的規則,更不應籠統地將網絡平臺從業員完全納入勞動者范圍,或完全將其排除在勞動者范圍之外。
勞動關系與社會保險的脫鉤及平臺監管制度的完善
由于勞動關系認定的模糊性以及現實中網絡平臺用工的復雜多樣性,目前對勞動關系的認定以及對網絡平臺工人的勞動法保護往往是事后的、個別的、零散的。平臺企業一般通過和服務提供者簽訂“合作協議”或合同,推定雙方關系為一般的民事合同關系,只有個別勞動者事后通過仲裁或訴訟確認勞動關系獲得勞動法保護。大量平臺服務提供者的身份處于不確定或模糊的狀態,而無法受到勞動法保護,因此,僅靠勞動法保護網絡平臺工人是不夠的,必須通過社會保險等制度的完善加強對此類主體的保護。此外,還應從經濟法和民商法等角度加強對網絡平臺企業本身的監管,督促平臺企業對服務提供者提供相應保護。
結論
平臺用工的新特點,使傳統勞動關系概念和判定理論在互聯網平臺用工背景下遭遇了巨大挑戰,法官在許多案件中面臨裁判困境。但傳統勞動關系概念和判定理論具有很強的彈性和適應性,并未完全過時,仍可包容網絡平臺用工關系,因此,不應輕易放棄傳統的勞動關系理論和判斷方法。同時,為適應網絡平臺用工的新特點,應改進勞動關系的判定方法。對網絡平臺用工勞動關系的認定,應考慮不同平臺以及同一平臺不同類型平臺工人的具體用工特點,綜合考慮個案全部事實進行具體分析。在勞動關系認定上,應更加注重實質從屬性,考慮平臺工人工作時間和收入來源,以及社會保護的必要性等因素。由于平臺用工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目前,我國不必針對網絡平臺工人的身份制定專門規則。除了勞動法,還應通過完善社會保險制度以及網絡平臺監管制度等,多角度保護網絡平臺工人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