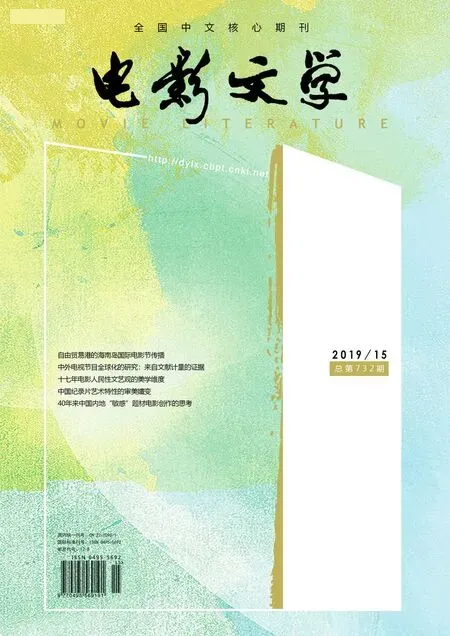電影民俗學視野中“講好中國故事”的敘事策略
沈 魯 吳 迪(南昌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民俗敘事,在文化“消費升級”的當下,越發凸顯其不被現代化馴服的力量。細察電影創作中的民俗敘事,發現電影創作者透過民俗講述中國故事、找尋中國文化過程中大抵呈現出三種視角:一是以啟蒙的姿態,通過現代理性重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透視民俗背后歷史積淀的滯重和國民精神的愚弱,期盼人性的回歸;二是重在關注民間市井生活,試圖呈現中國民間社會景象與問題;三是引入人類學理論,從更寬泛的意義上審視民俗,重在關注各類民俗事象,肯定民俗文化的價值,希圖在“固有血脈”和“歷史惰性”之間尋回傳統文化。這三種視角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其時的社會時代背景狀況,如今,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的時代要求下,回頭審視電影民俗敘事的這三種視角,以民俗敘事反抗“視覺快感”,對“講好中國故事”策略的提出有所幫助。
一、對民俗的“他者化”表現
(東方)“他者”出自西方后殖民主義理論,是一種與(西方)“自我”相對的存在,強調的是客體、異己特質。當“他者”與“主體”逐步被區分,“主體”不斷被確立,催生了“他者化”現象,即西方為確立自我中心價值,樹立自我支配地位而貶低、丑化異質(東方)文化的行為;相反,中國電影創作過程中的“他者化”是將(東方)“自我”塑造成(西方)“他者”更易接受的形象的行為。
張藝謀是電影民俗敘事中以啟蒙姿態創作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引領下,“新民俗電影”驅趕“文革”陰霾,重鑄國人靈魂,在國際舞臺大放異彩。他以“以意臆志”的創作態度,對民俗做出藝術化創造處理,將糟粕的封建民俗影像化,試圖喚醒沉睡已久的人性。《黃土地》被西方意外“發現”后,張藝謀開始琢磨如何“取悅”西方,《紅高粱》尚且以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崇拜贏得了國內外的美譽,《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卻將殘暴的“民族劣根性”表露無遺。盡管學者王一川曾經較為客觀地指出:“在《黃土地》《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和《秋菊打官司》中描繪的原始情調,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喚起了原始中國的真實感。”這些影片代表著正宗的“中國”形象,但是,我們不得不重新認真審視張藝謀電影中對民俗“他者化”的敘事表達,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民俗奇觀演繹的并不是中國人的常態,而是能夠喚起西方認同的被“他者化”了的東方想象。影片對古老/原始/愚昧/野蠻/專制的中國及中國人形象的塑造,對裹腳/長辮/深宅大院等丑陋的中國意象的表現,對宗族斗爭/亂倫野合等野蠻行為的呈現,是最能吸引西方人的地方。但是一味揣測西方的結果就是“自我”被“他者”所遮蔽。2017年《長城》再一次呈現出對民俗的極端“他者化”,“長城”是中國的偉大奇跡,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但是張藝謀似乎只是借用了長城的軀殼講述了一個好萊塢式的拯救故事:為抵御饕餮建筑的長城不堪一擊,若沒有兩個白人雇傭軍的舍身相助,長城軍團根本無法擊潰饕餮,中國也無法得救。影片故事內核與中國毫無關系,片中巍峨的萬里長城、中國神獸饕餮、高亢的秦腔“秦時明月漢時關”、孔明燈、火藥和指南針還有中國傳統兵法的排兵布陣在整個故事中都不過是為滿足西方人胃口的“饕餮盛宴”,只有一再用言語強調的“信任”是中國集體主義的象征。
顯然,張藝謀對民俗的“他者化”偏向極端,同樣對民俗進行“他者化”的導演李安并沒有和張藝謀一樣放大民俗事象中的神秘因子去迎合西方“他者”對東方“自我”的想象,而是將民俗安置于西方語境中,從“他者化”的視角審視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電影語言詮釋中國文化。他的“家庭三部曲”也被叫作“父親三部曲”,三部影片中的“父親”幾乎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大量的中華傳統民俗事象探討了中國傳統家庭人倫道德的深刻命題。《推手》里的中國書法、太極拳、京劇文化;《喜宴》中的紅包、旗袍、鬧洞房;《飲食男女》中的大量飲食民俗都非常好地糅合在一起,展現出“中國式家庭”這一耐人尋味的深刻命題,體現出更高層次的文化自覺與人文關懷。“一方面拋棄了后殖民心理帶來的民族虛無和模糊傳統文化身份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又消解了民族性的凸顯張揚,從此面貌中走向了與西方的平等對話。”
講好中國故事是要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里的中國故事可以是歷史的,也可以是現實的,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構的,但是一定要能夠展現中國文化精神。我們不能否認張藝謀電影極高的美學價值,但是他電影中極端他者化的民俗敘事不符合現下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要求,我們不妨借鑒李安導演中對民俗的“他者化”表現,站在“他者”視角凝視本族文化,找到中國民俗文化中與國際價值觀的“重合點”,將中國傳統文化以一種柔和的姿態呈現出來。
二、對民俗的“市井化”言說
繼張藝謀們的“新民俗電影”之后,第六代導演同樣表現出對民俗敘事的濃厚興趣,也就是“城市民俗”。例如,馮小剛的“賀歲片”充滿了京味兒,賈樟柯的山西電影描寫了汾陽縣城民俗,婁燁的電影也讓人領略了上海的市井文化……總的來看,電影中的“市井化”民俗敘事大抵體現為以下三種狀態:
一是電影中體現了較強的市民意識、世俗情懷。以往電影的民俗敘事多是寄托了某種文化因子,這些電影著眼于“市井”,表現著老百姓在時代大變革中的真實狀態;二是市井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成為電影的表達對象。這些電影大多將城市底層人物作為主人公,圍繞著他們的市井生活展開故事。《三峽好人》里的煤礦工和女護士,《站臺》中汾陽縣文工團的年輕人,《推拿》里的盲人按摩工,《甲方乙方》的自由職業者……三是以“方言”為主的電影對白。賈樟柯電影里的汾陽方言、馮小剛電影中的老北京腔調等。
拋開藝術形式不說,電影其實是一個關于“人”的藝術。國際評委在闡釋賈樟柯電影獲獎理由時,無不是認為他的電影通過對中國(人)市井生活的描述展現了一種普世的人的情感。他自己也說:“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生命的喜悅或沉重。”為了表現這樣的電影母題,賈樟柯將鏡頭對準了處處都滲透著民俗情感的山西汾陽縣城,通過對山西市井生活的展示來達到他的目的。電影里的人物最樸實的山西方言,汾陽縣城的特色民居,山西特色的刀削面、豬頭肉、餃子,等等。當然,賈樟柯電影在對民俗的“市井化”言說表達了對普通人關懷的同時,也是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另外一種影像化書寫。正如巴西導演瓦爾特·薩列斯所說:“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如此快速而猛烈的變化,更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像賈樟柯這么深刻地反映出這種變化。”
同樣,馮小剛也認為一部影片哪怕是喜劇,它的魂還是要“扣在普通人的夢想、普通人的煩惱上”。所以,他將“老北京”作為鏡像底色,表現著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和他們的市井生活。從《甲方乙方》到后來的《不見不散》《沒完沒了》《一聲嘆息》《大碗》《手機》再到《老炮兒》,北京方言“京片子”的調侃/揶揄/插科打諢以及從相聲/評書/戲曲/雜耍中汲取的“京味詼諧”,不僅是北京市井文化“油”與“貧”的表現,同時也將其時社會中的熱點問題包裝成城市民俗故事,在喜劇的裝點下表達他對現實社會狀態的思考及對人類情感的體悟與定位。例如,金錢對人的誘惑與異化,社會道德誠信的淪喪。可以說,馮小剛的電影形成于時代文化思潮變遷與中國電影體制轉型,將北京城市市井民俗作為影片的敘事軌道,為處于轉型社會中迷茫而失落的國內觀眾找到一條“回家”的路,滿足了他們對冷漠的社會人情的表達需要。
三、對民俗的“挽歌式”描寫
不少民俗在現代化浪潮中瀕臨消失,影視人類學家們拿起攝影機將它們記錄下來,也有不少導演將鏡頭聚焦于此,以藝術化的影像世界展現正在“失落”的民俗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藝術是用來闡釋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加強社會價值觀而精心制作的產物。電影如此,民俗藝術亦是如此。
吳天明導演在電影《變臉》中講述了一個身懷變臉絕技的民間藝人只身漂泊于江湖,面臨絕技失傳、香火難再續雙重危機,尋找下一代傳人傳承“變臉”的故事。中國民俗藝術大部分都受到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的影響,有著“傳男不傳女”的不成文規定,變臉王也是一樣。但是不同的是,狗娃面對變臉王“女娃無用”的觀點時,“觀音菩薩也是女的,何以你要去信她,求她?”的反駁以及影片最后變臉王把絕活傳給狗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同時,這樣的故事結局也給民俗藝術的發展開拓出一條出路。導演在表現對四川變臉民俗藝術的熱忱和對民俗藝術傳承出路思考的同時引發了人們對傳統民俗價值及其文化心理的深刻反思。
2017年,吳天明導演遺作《百鳥朝鳳》上映,這部同樣是以曾盛行于民間的嗩吶藝術為紅線的影片,反映了在現代化浪潮的裹挾下,嗩吶民俗的日漸式微、悄然隱退。曾“跪倒一片孝子孝孫”的“百鳥朝鳳”,所承擔“紅白喜事”及“娛樂解悶”等功能,構建了鄉村人際關系,維系著村民共同的感情和價值體系。但面對新文化的進入,除了師父焦三和游天鳴,其他嗩吶匠也選擇逃離奔向現代化都市的懷抱。“影片表面上是在講民間嗩吶技藝遭遇到的現代沖擊,但根本上,當然是用嗩吶來連帶整個傳統的鄉村倫理體系,從師徒關系、夫妻關系到婚喪禮儀、典章制度,嗩吶的衰弱是整個傳統文化衰弱的象征。”雖然說,影片敘事結構并未盡如人意,但是這樣的民俗敘事策略依舊是達到了警醒人們對傳統文化重視的目的。
在吳天明的電影中,正是因為他放棄了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以平視關照的視角,在對民俗進行挽歌式描寫的同時體現了導演對民俗藝術的熱忱、對民間藝人遭遇的同情,對日漸式微民俗藝術何去何從的擔憂以及對社會時代狀況的思考,才使得傳統民俗的靈魂在虛構的電影故事中得以重生。在想要講好中國故事的電影中,采取吳天明導演的這種通過對民俗的“挽歌式”描寫策略,讓國內觀眾了解到原來國家還有這些民俗,原來有些民俗正瀕臨滅絕,也讓國外觀眾看到中國更多的優秀民俗文化和國人對這些民俗文化的挽留。
四、結 語
民俗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千年歷史積淀。走過漫長的歷史發展,民俗成為能夠體現一個民族強大凝聚力的存在。在“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命題下,民俗敘事可以說是為電影“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一個快速、準確、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