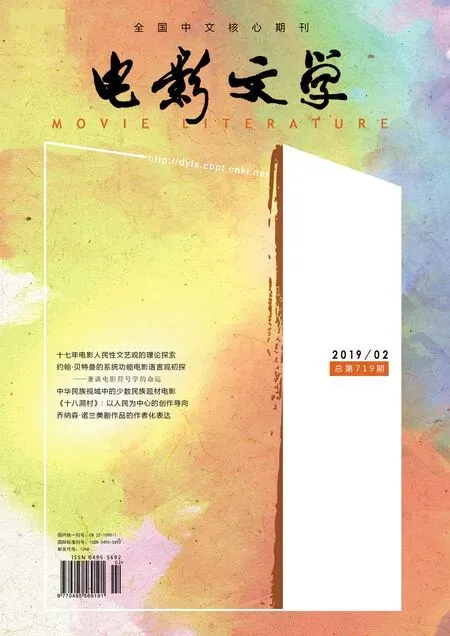電影《嘉年華》的主體構建與敘事呈現
戴思宇 吉 平 (陜西科技大學 設計與藝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21)
《嘉年華》作為一部典型的“敘述性影片”,它自身符號學敘事基調的形成與主體構建、敘事意象、敘事空間密不可分。導演文晏憑借細膩的女性視角,瞄準女性境遇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依靠人的外在形象和情緒表征,結合承載著敘事主體各種情感和欲念的敘事意象,構建出交織個人命運、原生家庭、男女性別、階級意識的混沌空間。
一、敘事體系中的主體構建
女性的個體風貌和生存姿態作為獨有的社會現象,是眾多影視重要的創作素材,導演文晏也正是在這片創作寶地中打造了電影《嘉年華》的雙套環式敘事體系。主人公小米小文的生活是相對獨立發展的兩個圈層,為了縫合主體構建間產生的敘事空隙,導演文晏將郝律師安置于雙套環敘事體系的交叉部位,起到連接兩位主人公生活的雙向交流作用。另外,雙套環式敘事體系分界點的建立,對應著兩大陣營:劉會長、王隊長、社會青年小建等人為代表的男性權力體系,他們是命令的輸送方,要求女性在男性權威所輻射的范圍中活動;小米、小文、孟母、莉莉等女性弱勢群體,她們的生活已經被男性權力滲透,處處充滿著消極的生活信號。導演文晏對這些不同年齡段人物的選用,也促成了主體人物多元格局的構建,進而也剝離出性侵案的實質——男性權力博弈下,女性被迫服從且飽受苦楚,正義公道的守護勢在必行。
(一)男性權力構建:權威指令的發送
《嘉年華》中劉會長、警察、高官、醫生組成的利益陣線,形成了負能量的集中營。劉會長作為性侵案的罪魁禍首,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掌控一切權力的陳府老爺一樣,以強權置身事外。即便正面鏡頭極少,“男人的權威性仍是一個缺席的在場者”[1],其命令式的腔調一出,強勢地剝奪女性選擇權的同時,也使男權同盟者有機可乘,顛倒黑白。諸位男性所處的行業雖然不同,但他們自私自利的舉動與劉會長用財力置換自由的惡劣性質是高度一致的。這些涉事的男性都真實地生活在我們的視野中,他們既是惡勢力的男性符號代表,又于廣施淫威中用金錢和權力占據話語霸權。
(二)女性悲劇構建:情感生理的傷害
面對避之不及的男性惡勢力,女性一方注定承受傷害。“黑戶”小米,用超出同齡人的城府和成熟去求得生存,小文整日郁郁寡歡,天真無邪的笑容變為兩位少女身上罕見的奢侈物。她們雖都予人以清冷的氣質,細細一品還是大有不同。小文的“冷”中存有一絲純真,可小米的“冷”,夾雜著冷漠和卑微之余,還不時地散發出一股忽強忽弱的孤傲之氣。從小米對待性侵案一事先是冷淡,后又心虛躲閃的態度,小米情緒的復雜多變使得觀眾對她的內心世界捉摸不透。對于比小米年長的成年期女性——莉莉、孟母等人,觀者則能從其鮮明的性格和生活狀態中窺視到當代女性的底層生活風貌。穿著美艷、圓滑乖巧的莉莉慘遭男友小建出賣,落得“下輩子再也不要做女人了”的一聲嘆息;孟母的職業是舞女,性格較為暴躁,面對性侵案只能敢怒不敢言。這群被男性權力符碼系統所操控的女性,愈是表面張揚,其內心焦慮和無力反抗的軟弱意識,愈是快速得到曝光。女性主體自我麻痹、妥協不抵抗的懦弱意識一旦構建,被動服從和妥協迎合便會成為女性自保的首要選擇,而這也使得大部分女性在遭受身心傷害后仍渾然不知,被冠之以“男權社會犧牲品”的標簽。這種被丑化的符號削弱了女性的反抗情緒和行動能力,進而直接瓦解了女性自我拯救的力量。
(三)正面人物構建:公道正義的守護
性侵案受到權力發送者的攔截,偵破進展困難,小米小文的成長之路受阻。在此等困境中,導演文晏似乎感觸到了某種正在覺醒的正面力量。于是乎,“新的主體構建作為一項自我賦權的重要行動”[2],自然而然地也就承擔了反對現實惡勢力、守護正義的使命。
就郝律師本人而言,她的身份設置近似于韓國性侵題材電影《素媛》里的心理醫生。她的現身不僅僅是積聚影片的角色效應,更是呼應底層邊緣群體中“缺位”的社會力量。郝律師除了專業素養極高、懷有仁愛公道之心,她的身上還流淌著一種可貴的雙性氣質。她每次出場都是一身西裝搭配公文皮包,簡潔大方中彰顯著一種剛硬的男性氣質。這種具有個性化特征的著裝,契合律師職業的嚴謹特性,又暗示在男權社會,女性要想擁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像男性一樣自立、自信。拋開律師的職業外衣,她又是一名普通的女性,有著不可多得的柔情。她本著尊重的原則,待小文如慈母般輕聲細語安撫,對小米亦如長輩般教導和包容。導演文晏精心設置的郝律師一角,以男性惡勢力的反對者身份現身,昭示自身對女性弱勢力量的支持。
二、敘事意象中的意蘊營造
敘事意象是電影敘事藝術中極具包容性的影像符號,影像符號“能指”和“所指”關系的建立,物象與象征韻味的融合,有利于促成敘事意象外在特征與內涵表意的有機統一。在影片的敘事過程中,敘事意象首先對現實物象進行還原和再現,直觀展示影像符號的“所指”。其次,敘事意象又是一“內心視像”,它通過對主體冥想和行為動作的真實觀照,成功地具備了人性化的思想和觀念,從而完成影像符號的“能指”。《嘉年華》中與主角緊密聯系的夢露雕像、金色發套等敘事意象,面對來自主體人物強大的感情沖擊,始終安靜地承擔著影像符號的表意功能,它們身為社會中“被看”的對象,化作欲望、情緒的符號指代陪伴在主人公的身邊。
回顧影片里夢露雕像的第一次出現,導演文晏是借助主人公小米的視角來展現的。彼時,小米發現了夢露的高跟鞋和紅色指甲,驚喜地在上面觸摸、描摹,一旁的游人則把夢露雕像當作玩鬧合影的背景。爾后鏡頭又多次順著小米所仰視的方向,到達夢露雕像裙裾下方的私密處。這一處極具深意的鏡頭里,夢露雕像身上具有女性典型特征的生理部位被公開,而小米抬頭、仰望、凝視,伸手拍照,一系列動作的發出,也直接展現了夢露身體的“被看”過程。“在一個由性的不平衡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3]在常見的影視作品中,女性的身體也常是“被看的對象”,男性往往是這種觀看行為的主導者。導演文晏在《嘉年華》男性角色弱化、男性權力隱身的敘事背景中,一反以男性視角為主的敘事常態,將女性身體被異性所觀照的傳統設置轉換成了身為女性的小米。從影片開頭夢露身體被小米觀察觸摸,再到后期小米對莉莉身體部位的主動撫摸,“被看”與“被摸”動作的前后呼應,也喻示著物化的女性身體和實質的女性活體成為小米心中建構女性形象的參照物。然而迫于尷尬的“黑戶”身份,正常的愛美之心成為不能見光的存在,小米把別人遺留的二手裝飾物收藏起來,把對美的一切欲念與向往都擱置在自我的想象中。與母親發生沖突的小文,深夜一人躺在夢露雕像腳下。兩處簡單的長鏡頭里,小文的情緒十分平靜,夢露雕像保持其一貫的沉默。導演文晏用不帶任何修飾的鏡頭語言來表現小文內心深處的顫抖和無助,頗有無聲勝有聲之效。
三、敘事空間中的符號呈現
“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動的匯聚處、紐帶和共同的根基。”[4]導演文晏以兩位少女的日常生活為敘事重心,建造了從私人空間(家庭)到公共空間(校園、社會)的“兩點一線式”的空間符號。在這兩個關系錯綜復雜的生存空間中,“身份是處理意義過程的前提,自我是符號活動的產物”。[5]主人公所歷經的原始成長環境關乎她們個體身份的形成,其后天的社會生活又最終影響到個體身份所做出的行為選擇。因此,電影敘事空間作為主體人物活動、思想、情感的依附基礎,它所關聯的主體符號活動和敘事話語實現了對主體真實身份的呈現——小米的黑戶身份,小文的離異子女身份。
(一)私人空間:“家庭”符號的缺失
電影《嘉年華》涵蓋了三種原生家庭模式,第一類是以張新新家庭為代表的完整獨生子女家庭,第二類是以孟小文為代表的離異單親家庭,最后一類則是以小米為代表的信息不詳、情況不明的“黑戶”家庭。這三類家庭的集合是中國式家庭的符號特征,他們共性在于“家庭”的不完整,或是父母中有一方缺席,或是家庭教育缺失。
《嘉年華》中的父親形象處于被弱化的層次,但他們對女兒產生的影響卻不容忽視。張新新的父親為自己的事業,鼓勵女兒拜劉會長為干爹,性侵案后又帶著張新新屈服于兇手的金錢誘惑中;小文父親是一個先抑后揚的角色,他曾在女兒小文的成長中缺席多年。初入觀眾視野,也是一派碌碌無為的作風,然而小文在絕望之際仍視自己的父親為“最后一根稻草”的舉動,使得小文父親這一角色化為一種親情符號回歸銀幕,轉變成治愈和陪伴的溫暖形象重新登場。反觀《嘉年華》中母親的形象,孟母對小文非打即罵,兩人難以溝通且常常冷戰;張新新母女向金錢妥協,充滿著諷刺意味的同時揭示張母是男性權力下的臣服者;小米表面是最自由的孩子,實則是影片里最為孤獨的一個角色。“三年前,我從老家跑出來,這是我待過的第十五個地方”,小米在不同的空間輾轉,模糊的話語中透露著許多的不確定性和逃避因素,那個隱藏在她身后的不愿提及的家庭,是“空白”的。
以上原生家庭的種種惡況,破壞了少女們正常的成長路徑。主人公小米、小文雙雙在成長的關鍵階段失去父母的親情關懷,她們所盼望的快樂和安穩總是遙遙無期,家庭內部的創傷致使兩位少女的情感空間不斷被壓縮,與其相符的純真無憂逐漸消失,最后直接促成小米、小文性格上的孤僻冷漠。
(二)公共空間:“社會”符號的混沌
對于家,少女們一度充滿失望。她們急于掙脫現有的桎梏,幻想蛻去稚嫩的少女身份,并試圖尋求某一種方法,在新環境中為自己找到暫時的解脫。校園本為自由純潔的圣地,承擔著教育和引導學生發展的使命。可《嘉年華》中的校園不似想象中美好,各種言語暴力和肢體暴力為主的霸凌現象盤踞于小文的校園生活中,加之單親家庭的背景出身、老師的冷眼相待,小文的弱勢性更為突出,因而極易成為被欺負的對象。隨著小文單方面的反抗到男女雙方的肢體沖突,再到小文被推倒在地和腿部傷口的特寫,導演全程以一種俯視鏡頭給予展現,間接暗示成年男性對女性的嘲弄意識已蔓延至年輕的男性學生身上。同樣與純真校園生活形同陌路的失學者小米,則逃到一座海濱城市。“我喜歡這兒,因為這兒暖和,就連一個要飯的,夜里也能睡個好覺”。影片通過固定鏡頭和長鏡頭的反復使用,真切地表現小米瘦小身軀下所要承擔的工作負荷。回視小米的生存境遇,邊緣群體的卑微出身讓她始終無法融入這里。年僅15歲的她,是這個表面溫暖的海濱城市中真正的“他者”。
學校、醫院等公共場域的不良作風,少女們日常生活的坎坷,無數問題的發生都是對社會符號系統內部男強女弱、利益至上、人際關系破裂丑態的鞭笞。男性權力不斷彰顯強化,促使女性在“被審視”與“被壓迫”的痛苦之間不斷游移,進而致使女性失去自身命運走向的自控權。在權力決定話語權歸屬、利益高于法律的社會背景下,以小米、小文為代表的弱勢群體傷痛無處可掩,有冤無處申的狀況更顯渺小可悲,弱勢群體的女性想要獲得獨立自信,擁有尊重和權益保障的愿景成為天方夜譚。
四、結語
《嘉年華》以少女個體的特殊境遇為主視點,連接其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各色成年人物,并透過這些主體人物的性格和行動表現,構建起主體人物的符號特征。此后,隨著主體人物的位移開展,與之聯系緊密的敘事意象,以積極的闡釋作用現身,影片象征符號的意蘊得以傳播至復雜的敘事空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