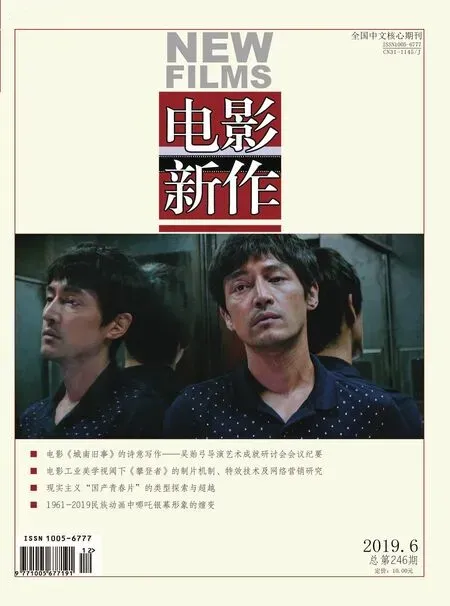新主流電影《攀登者》的國家敘事表達
劉福泉 趙雅馨
新主流電影與主旋律電影淵源頗深,葛慎海明確指出,“新主流電影指的是主旋律電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主流電影的價值內(nèi)核”。趙衛(wèi)防、皇甫宜川等學(xué)者指出,“新主流電影基于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向“大片化”轉(zhuǎn)變,同時歷史背景的變化,使得新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需要“走出去”。由此可見,從主旋律電影到主流電影再到新主流電影,表現(xiàn)出流變特征。新主流電影作為動態(tài)化的電影形態(tài),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nèi)核,表現(xiàn)愛國主義情懷,但區(qū)分于傳統(tǒng)主旋律電影,將商業(yè)屬性融入其中,從而兼具藝術(shù)性、政治性與思想性。
《攀登者》作為新主流電影的代表,獻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彼此之間相互襯托,共創(chuàng)60億元票房的佳績,滿足著大眾的審美期待。其中,《攀登者》以真實歷史事件改編,為彌補中國攀登者第一次登頂珠穆朗瑪峰沒有留存影像資料的遺憾,勇士們臥薪嘗膽終于在1975年北坡登頂,創(chuàng)造歷史,為國爭光。之所以稱其為新主流電影,是因為該片不僅以愛國主義為主題思想,而且采用航拍、微觀攝影、延時攝影、大特寫與大遠景兩極鏡頭等視聽手段為觀眾帶來視聽盛宴;除此之外,跌宕起伏、起承轉(zhuǎn)合的敘事模式,加之吳京、章子怡、張譯與胡歌等大牌明星的參演,又將商業(yè)元素融入其中,共同演繹著新主流電影的時代風(fēng)采。
一、影片國家敘事的特征呈現(xiàn)
中國融入全球化體系的過程便是不斷生產(chǎn)中國故事的過程,而“故事的議題設(shè)置既是建構(gòu)國家在國際地位上政治角色及其話語權(quán)的資源,同時也牽涉國家所主導(dǎo)的國際實踐能力”。可見,能否“講好中國故事”是能否在國際舞臺上擁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而新主流電影作為傳遞國家意志的發(fā)聲筒,自然擔(dān)負其形塑國家形象的重任,《攀登者》作為這類型影片中的佼佼者,以其獨特的藝術(shù)手段呈現(xiàn)國家敘事。
(一)主題表達: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契合
從語義學(xué)上講,“攀登”是指握住或者抓住某物奮力向上爬,而“攀登者”則比喻著勇往直前、不畏艱險、樂觀奮進的人。早在我國古代,曹操的“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便表達著統(tǒng)一中原的遠大抱負,杜甫的“會當(dāng)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亦表現(xiàn)出勇攀頂峰、俯視一切的壯志與兼濟天下、卓然獨立的豪情。可見,“攀登”作為一種民族精神早已融入華夏兒女的血脈之中,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而在新時代下“攀登”又被賦予著振興中華的使命,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fù)興,這一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影片《攀登者》在主題呈現(xiàn)上正是將新老一輩不畏犧牲、克服肉體與精神雙重阻礙、銳意進取的民族精神與揚我國威、彰顯大國意志的中華復(fù)興這一時代使命相互融合,呈現(xiàn)國家敘事,傳遞著獨屬于這個時代的“攀登”精神。正如福柯所說“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因而作品在呈現(xiàn)國家敘事時,將故事放置于20世紀60、70年代國家相對積弱的社會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將其看作歷史的產(chǎn)物,還將時代精神融入其中,傳達“窮且志堅,不墜青云之志”的國家風(fēng)骨,從而在風(fēng)云變幻的國際發(fā)展中,為國人打上一針國家富強的強心劑。
(二)人物形象:從扁平到立體的英雄形象塑造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影片突破著傳統(tǒng)主旋律電影中英雄人物“高大全”的扁平特征,取而代之是一群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如畏懼兩人愛情珠峰,遲到告白十五年的方五洲,又如因未能拍下珠峰影像懊惱頹唐的曲松林。除此之外,女性人物與少數(shù)民族同胞參與國家敘事是影片人物塑造方面的突出表現(xiàn)。受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女性往往是男性的附庸,“女子無才便是德”更道出傳統(tǒng)女性的從屬地位,即使在當(dāng)下的文藝作品中女性地位雖有所提高,表現(xiàn)出反抗、堅強與獨立的特性,但也僅僅局限于“小家”范圍內(nèi)對男權(quán)、對社會的抗爭,如《我不是潘金蓮》中的李雪蓮、《少年的你》中的陳念,卻很少參與“大國”的建設(shè)中,表現(xiàn)“巾幗不讓須眉”的家國情懷。但《攀登者》中的徐纓卻作為一名經(jīng)驗豐富的氣象學(xué)家,為登頂珠峰提供氣象數(shù)據(jù),以科學(xué)技術(shù)參與攀登珠峰的國家壯舉中。而作為藏民族同胞代表的杰布一代攀登者與黑牡丹二代攀登者,同樣在國家敘事中發(fā)揮作用,正是杰布的后勤保障才使得突擊隊免去很多后顧之憂,而黑牡丹作為李國梁的戀人,在他犧牲后承擔(dān)了攝影的重任。由此可以說,攀登重任的完成是民族團結(jié)的結(jié)果。
(三)商業(yè)轉(zhuǎn)變:奇觀化的視聽盛宴與片尾“彩蛋”
為迎合市場需求,影片在傳遞愛國主義精神的同時,以奇觀化的視聽語言沖擊著觀眾的眼球,但這并不是簡單地通過大場面、快速剪輯與情愛橋段去迎合觀眾,而是作為一種手段,為國家敘事的彰顯提供助力。就環(huán)境的拍攝而言,影片不僅大量運用航拍的手段表現(xiàn)珠峰的雄奇挺拔,而且以3D、4K的方式將皚皚白雪的壯美景觀收錄其中,從而形塑“神山”的奇麗俊秀。除此之外,微觀攝影下攀登隊員臉上的風(fēng)雪紋路與顫抖的嘴唇則更加細致入微地表現(xiàn)著環(huán)境的艱苦。在這種大遠景與大特寫的鏡頭切換中,一方面為觀眾觀摩雪山,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創(chuàng)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在偉岸雪山與渺小登山隊員的兩相對比下,凸顯國人意志的強大。
電影“彩蛋”源自西方復(fù)活節(jié)尋找彩蛋的游戲,本意為“驚喜”。近年來,為了增強影片的趣味性,一些制片方會在片尾的字幕后設(shè)置橋段,或用以呼應(yīng)前片或為續(xù)集埋下伏筆。同樣,《攀登者》在片尾字幕后同樣插入了由成龍扮演的老年楊光再度攀登的橋段,老年楊光恍若一直與當(dāng)年的隊友同在,與正片情節(jié)構(gòu)成互文性敘事的敘事結(jié)構(gòu)。另外,國家意志的傳達上,片尾“彩蛋”代表著“攀登”精神具有持續(xù)性與當(dāng)下性。
二、國家敘事策略的邏輯框架
高夫曼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中指出,就大眾傳媒來說,框架就是一種意義的建構(gòu)活動,那么對于影視作品而言,邏輯框架的建構(gòu)便是導(dǎo)演議程設(shè)置的結(jié)果,亦是該作品區(qū)分于“他者”的顯著特征。同樣,《攀登者》作為新主流電影中的一分子,其敘事策略的邏輯框架也表現(xiàn)出了別具一格的風(fēng)采。
(一)國家情懷與商業(yè)元素的互滲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的主旋律電影經(jīng)歷了三次較為明顯的轉(zhuǎn)型,而每一次轉(zhuǎn)型都與商業(yè)元素的滲透有著重大的關(guān)聯(lián)。第一次改變發(fā)生在20世紀50-70年代,這一時期的電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完成商業(yè)電影向革命電影的過渡,出現(xiàn)如《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樣板戲電影;第二次轉(zhuǎn)型發(fā)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到來使得革命文化轉(zhuǎn)向商業(yè)文化,但這并不是一種倒退,而是在政治理想中加入浪漫元素或人文關(guān)懷,使得銀幕上的階級群體變?yōu)榱巳フ位膫€體的人,如《黃河絕戀》《共和國之歌》等。此時的革命文化與商業(yè)邏輯相互融合,我國的電影市場也開始朝著產(chǎn)業(yè)化的方向發(fā)展。而第三次轉(zhuǎn)型則發(fā)生在2010年后,《戰(zhàn)狼》《湄公河行動》《流浪地球》等一批新主流電影的應(yīng)運而生,使得中國的電影產(chǎn)業(yè)走向成熟,這些作品在商業(yè)電影的敘事框架中融合主流價值觀念的同時,傳遞一些更具理性與超越性的概念,如《湄公河行動》中對毒品問題、恐怖分子的回應(yīng);《流浪地球》中對生態(tài)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guān)注。這不僅與第二時期追求商業(yè)化,滿足市場需求所不同,還與第一時期的革命電影存在差異,以潤物細無聲的力量將國家情懷滲透到個人行動與日常生活中。
《攀登者》作為第三次文化轉(zhuǎn)型中的作品,在敘事框架顯現(xiàn)了愛國情懷與商業(yè)元素間的互滲,一方面將民族精神與時代思想融入商業(yè)框架中;另一方面又用商業(yè)元素改寫歷史事件,從而以柔性敘事的方式傳遞更加豐富的內(nèi)涵。毫無疑問,這部影片最為凸顯的敘事主線便是個人理想與國家使命的關(guān)系,登頂珠穆朗瑪峰不僅僅是一種勇往直前的現(xiàn)代競技意識,更是一種對國家主權(quán)與國家名譽的捍衛(wèi),因此一個個“小我”選擇犧牲自己,如第一代攀登老隊長的犧牲、曲松林的受傷,第二代攀登新隊長李國梁的犧牲、楊光的截肢,但正是因為一個個“小我”的犧牲,才換來“大國”的日益富強。除這一條顯性的敘事主線外,男女愛情與民族情誼的暗線,以脈脈溫情的方式形塑著國家敘事框架。就愛情線而言,方五洲與徐纓在青春年少時便萌生了情愫,但在特殊的年代面對群眾的質(zhì)疑,方五洲成為一名鍋爐工人,而徐纓出國學(xué)習(xí),二人天各一方。直到十五年后響應(yīng)國家重建登山隊的號召,二人得以重逢,但重逢后的他們沒有立即結(jié)婚,卻選擇以同事的身份陪伴在彼此身邊,因為在他們心中,國家使命遠比個人情感更為重要。為平衡政治的嚴肅,導(dǎo)演有意加入“英雄救美”的經(jīng)典愛情橋段,面對雪崩巨石,方五洲義無反顧地擋在徐纓面前;而作為女方對男方愛情的回應(yīng),徐纓堅持跟隊上山以觀天象,最終因肺水腫吐血而亡。就民族情誼而言,李國梁與黑牡丹的結(jié)緣雖因愛情而起,但李國梁為救相機而自我犧牲后,黑牡丹承擔(dān)起攝影的重任,并在最終九人登頂珠峰后拍攝下珍貴影像。此時的二人之間的感情指代了漢、藏兩族間的情誼,可以說,正是因為民族間的深情厚誼,才使得國家日益富強。
(二)差異化的當(dāng)代歷史與新中國故事的互融
《攀登者》的敘事方式較其他的新主流電影而言,其突出特點表現(xiàn)為從現(xiàn)代的角度出發(fā),重新審視20世紀50-70年代那段具有差異化的傷痕歷史,影片采用插敘的方式,通過片中主人公的回憶將這段傷痕歷史與當(dāng)下的主流價值觀念相嫁接,從而顯示出在快速崛起的時代背景下,新中國開始與過去的傷痕握手言和,從而以更加自信的姿態(tài)講述中國故事。
1955年,我國與尼泊爾就珠峰的歸屬問題展開國際討論,建議按照國家界限進行劃分,但尼泊爾卻聲稱中國從未登頂過珠峰,因而珠峰應(yīng)全部歸屬于他們。事實上,在1953年尼泊爾從環(huán)境較好的南坡登頂,1960年我國的王富洲、貢布與屈銀華在物資短缺、蘇聯(lián)援助撤退的情況下從北面登峰,但為了挽救同伴性命,不得不丟掉相機,致使未能拍攝360°的珠峰景觀而使得登頂珠峰問題備受國際質(zhì)疑。于是在1975年5月27日14時30分,國人第二次登頂珠峰,測繪出8848.13米最新海拔高度,并在第二臺階處架設(shè)金屬梯,譽名為“中國梯”。
這段飽受爭議的歷史,在影片以“現(xiàn)實-回憶-現(xiàn)實”的方式展開,影片伊始,登山隊解散,方五洲成為一名教師,為學(xué)生講述登山知識,面對學(xué)生的提問,畫面閃回到1960年突如其來的雪崩致使隊長喪命,其他三名隊員歷經(jīng)千難萬險登頂珠峰,但因未拍攝影像而遭到國際質(zhì)疑,而后畫面回歸到現(xiàn)實的教學(xué)場景。這種“現(xiàn)實-回憶-現(xiàn)實”的組接方式被法國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家吉爾·德勒茲稱為“回憶-影像”,他強調(diào)閃回鏡頭具有重構(gòu)影像記憶的功能,他認為鏡頭畫面是一種時間化的功能,而不是一種現(xiàn)實功能,也不是確切的回憶,它構(gòu)成過去時區(qū)或者時段連續(xù)體。正是在這組回憶影像的畫面組接中,我們了解到國家那段悲傷的過去,相較于以往對傷痕歷史的規(guī)避,《攀登者》直面過去,并汲取過去的經(jīng)驗,繼續(xù)發(fā)揚“攀登精神”。此外,影片設(shè)置片尾“彩蛋”,將攀登的故事延續(xù)到2019年,表明舍己為人、為國奉獻的攀登精神在神州大地上不斷傳遞與集成,從而使得差異化的歷史與新中國故事的互融,以相反相成的邏輯框架建構(gòu)國家敘事。
(三)科技理性與國家意志的互構(gòu)
除卻與差異化歷史的握手言和外,《攀登者》在敘事策略上的另一個突出特點表現(xiàn)為以科技理性指導(dǎo)攀登行為。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攀登精神雖然早已融入國人的血脈中成為民族共識,但攀登珠峰這一頗具危險性的行為并不能單逞匹夫之勇,而需要以科學(xué)知識作為指導(dǎo),以客觀理性的態(tài)度加以對待。影片中為凸顯方五洲超強的身體素質(zhì)與攀巖能力,不時通過“動作電影”的特技手段強化視覺效果,但導(dǎo)演深刻的懂得登峰并不是個人英雄主義,而是團隊之間相互配合并需要科學(xué)技術(shù)作為支撐的結(jié)果。因此,在第二代攀登者登峰的過程中加入了以徐纓為代表的氣象觀測組織,提供氣壓與溫度的科學(xué)數(shù)據(jù)。除此之外,第二次攀登的重要任務(wù)之一是進行科學(xué)考察,獲得珠峰的實際海拔高度,而這些都依賴于我國在相關(guān)科技領(lǐng)域的重要突破。
以科技理性為指導(dǎo)完成攀登任務(wù),其背后與強大的國家支撐密不可分。首先,就登山隊的再度組建而言,便是由國家體委牽頭,聯(lián)合專業(yè)隊員、科學(xué)家與藏族同胞;其次,就科技力量的支撐,這同樣是國家發(fā)展、民族富強的結(jié)果;最后,就“攀登”的文化意指而言,它代表著中國對喜馬拉雅山國家主權(quán)的宣誓,代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洗雪恥辱的決心,代表著中華民族奮起直追的信念。影片的結(jié)尾,方五洲從雪地中翻出藏在手電筒中的五星紅旗并集眾人之力將之升起時,便彰顯著國家身份,建構(gòu)了國家認同。正所謂“科學(xué)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而影片正是通過科學(xué)理性與國家意志的互構(gòu)來表現(xiàn)國家敘事的。
三、影片對國家敘事表達的啟發(fā):以歷史記憶建構(gòu)國家認同
記憶理論起源于心理學(xué)的研究,20世紀初開始轉(zhuǎn)向社會學(xué)。1925年,法國的社會學(xué)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度提到了“集體記憶”概念,強調(diào)當(dāng)下對于過去的建構(gòu)性,從而使“過去”滿足于“當(dāng)下”的思維邏輯、情感表達與價值架構(gòu)。歷史記憶作為一種集體記憶,與社會、民族、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棲息相關(guān),通過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者目擊者對歷史事件的記錄和回憶,牢固地把群體凝聚在一起,從而獲得現(xiàn)行秩序的合法化表達。而國家認同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于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理想信念、國家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認同,是一種重要而且深遠的國民意識。
新主流電影作為一種媒介載體,通過藝術(shù)化的方式對關(guān)系民族或國家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記錄,形成一種具有集體性的歷史認識或歷史觀念,再經(jīng)由媒體的傳播,強化該國家、民族對自身根基的歷史記憶傳承,達到提高國人凝聚力以及認同感的目的,從而建構(gòu)國家認同。同樣,《攀登者》在國家敘事的表達中,亦通過對攀登珠峰事件的改編,在歷時與共時兩個維度書寫歷史記憶,從而建構(gòu)國家認同。
(一)歷史記憶“根脈”穩(wěn)固國家認同
歷史記憶以集體知識為載體,通過代際傳承來確保歷史的連續(xù)性,這能夠為后輩們重新構(gòu)建國家認同給予歷時性的視角關(guān)照。對于個體來說,歷時性的認同就是記憶的功能所在,有助于人們忠于自我。所以,歷史可以被當(dāng)作是一個通過社會建立起來的歷時性身份。正如哈布瓦赫提到的,相對于集體記憶,歷史記憶留存的時間性更長、持續(xù)度更高,可以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一脈相承。這種特征使得它能夠?qū)⑷后w凝聚,促進群體有效發(fā)展,并且易于群體內(nèi)的每位成員共享與接受。
從宏觀角度看,影片《攀登者》根據(jù)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從1960年的第一代攀登者到1975年的第二代攀登者,再到2019年前赴后繼的攀登者,本就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上顯現(xiàn)出了歷史的連續(xù)性,且代代相傳的“攀登精神”召喚了歷史記憶,從而在歷時性的維度穩(wěn)固著國家認同。而從微觀層面看,影片以第一代攀登者未能留下影像資料的事件為起點,通過一些歷史回憶的代表性象征物來形成文本系統(tǒng)、意象系統(tǒng)和儀式系統(tǒng),從而以歷時性的角度通過文化符號考量記憶的建構(gòu)與延續(xù),并用來解釋當(dāng)下現(xiàn)狀和未來發(fā)展趨勢等具有歷史指向性的議題。例如,在影片的開頭和結(jié)尾處多次出現(xiàn)的證明方五洲一行人登頂珠峰的海洋生物化石,便隱喻著國家由積弱到強大的發(fā)展歷程。影片伊始,在課堂上因遭到學(xué)生質(zhì)疑一塊化石碎落在地,暗喻著國際輿論對中國人登頂珠峰的不認可。而在結(jié)尾處,方五洲在峰頂埋下了他原本送給徐纓的化石,這塊化石不僅指代了他們二人共同理想的達成,也能指著全體國人對登頂珠峰的期盼。除此之外,攝影機也發(fā)揮著異曲同工之妙,第一次登峰過程中攝影機的丟失暗示著即使成功后也將面臨國際的質(zhì)疑,而第二次李國梁用自己的生命換回了攝影機,指代著時隔十五年之后的登峰使命必將成功,在結(jié)尾的“彩蛋”處展現(xiàn)的一段段真實歷史影像資料,便正是這臺攝影機拍攝的登峰過程。可見,這塊化石與這臺攝影機猶如象征歷史記憶的符碼,嵌入在國家敘事的詩篇中,喚醒著民族自豪感,從而建構(gòu)了國家認同。
(二)歷史記憶“基因”聯(lián)結(jié)國家認同
從歷史傳承的方向出發(fā),哈布瓦赫對集體記憶的形成以及作用進行了分析,研究了歷史發(fā)展的內(nèi)部規(guī)律。他提出,集體記憶的物質(zhì)載體是非常豐富的,包括文字、圖像、地點等。但是,無論呈現(xiàn)方式是何種形態(tài),其一是指向群體身份的歸屬問題,是在建構(gòu)某種特定的文化認同。正如在影片中,無論當(dāng)我們看到象征挑戰(zhàn)與困難的珠穆朗瑪峰,還是象征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飛鳥蓑羽鶴,抑或是代表國家尊嚴與權(quán)威的五星紅旗。從符號學(xué)的角度審視,他們都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形式上的能指,其所指的意涵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因子,也正是這些具有國家“基因”的文化元素,連綴成屬于上世紀70年代那一隊“攀登者”的歷史記憶,從而促進了文化層面國家認同的生產(chǎn)。
如果說歷史記憶的歷時性維度是影片建構(gòu)國家認同的“根脈”,那么象征歷史記憶的多種因子(蓑羽鶴、五星紅旗、攝影機等)則共同發(fā)揮作用,成了其建構(gòu)的重要“血肉”,更加明確地指向了國家文化身份。而當(dāng)諸多“歷史記憶因子”形成的“記憶場”,經(jīng)過媒介儀式“再生產(chǎn)”之后,最終指向的都是反映民族團結(jié)與國家強大的精神意指。而當(dāng)創(chuàng)作者將這些符號集群所生成的歷史因子串聯(lián)起來,就使得那段歷史記憶得以貫通,在喚起過去意義的同時,也與當(dāng)下的話語范式相結(jié)合,促使歷史記憶在文化認同建構(gòu)當(dāng)中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結(jié)語
新主流電影《攀登者》作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國家獻禮片,憑借國家情懷與商業(yè)元素的互滲、差異化的當(dāng)代歷史與新中國故事的互融以及科技理性與國家意志的互構(gòu)完成了國家敘事的表達。除此之外,影片直面?zhèn)蹥v史事件,以自信心與包容心與之握手言和,從而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雙重維度書寫歷史記憶,增強國人自信心的同時,建構(gòu)國家記憶。但細細觀之,便可發(fā)現(xiàn)影片對于登山主題與愛情元素之間的平衡問題尚且存在些許不足,過度的情緒抒發(fā)有時會沖斷國家敘事的鏈條,從而給接受者帶來過猶不及的觀影體驗。辯證來看,《攀登者》雖存在美中不足之處,但作為國內(nèi)首部登山冒險題材作品,確實在國家敘事的表達與國家認同的建構(gòu)上彰顯了其獨特魅力,以瑕不掩瑜之態(tài)為中國新主流電影的發(fā)展做出了一份貢獻。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