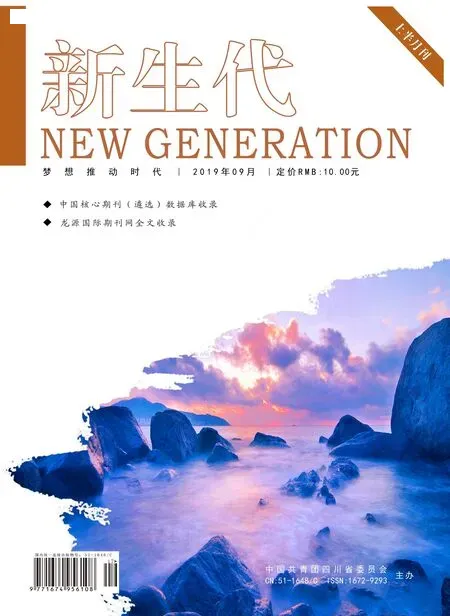紅與黑的碰撞—于連形象矛盾性分析
王國婷 西北師范大學 甘肅蘭州 730070
長篇小說《紅與黑》由法國作家司湯達根據真人真事加工創作而成。作品將視角聚焦于1825年費朗什—孔泰省的維里埃小城,講述了市長德?萊納挑選了鋸木廠老板的兒子于連?索萊爾作家庭教師,于連在任教期間獲得市長夫人的好感,逐漸愛上了這個漂亮的小伙子,成了他的情婦,不久后事情敗露,在西朗神父的安排下,于連來到貝藏松的神學院學習。得到院長彼拉神父的信任,院長舉薦他作了德?拉莫爾侯爵秘書的職務。任職期間 ,于連高傲不馴的氣質引起了侯爵女兒瑪蒂爾德的好感。但是瑪蒂爾德高傲的姿態常常讓于連痛苦難堪,于連在科拉索夫親王的指導下,成功勾引了瑪蒂爾德。懷孕后的瑪蒂爾德頻繁和父親通信,以企獲得父親的許可,侯爵最終答應了這門婚事,并授予于連稱號、軍階及莊園。這時,德?萊納夫人在教士的挑唆下,寫了一封告發信,揭開了她和于連的關系。盛怒之下,于連回到維里埃開槍打傷了她。很快于連被捕入獄,判決死刑。三天后,德?萊納夫人也離開了人世。
于連這一人物形象因其復雜性和矛盾性歷來被讀者稱道,其性格的矛盾復雜首先體現在對理想的堅定追求及對現實的妥協上。小說第四節(《父與子》)中寫到,于連在鋸木廠工作時,一心醉倒在書里。索老爹破口大罵“懶鬼!你看鋸的時候還要讀你那些該死的書嗎?”盛怒之下的索老爹抄起樹干,朝于連打去,把于連的書打到溪水里。那本書正是《圣赫勒拿島回憶錄》。年輕的于連酷愛盧梭的《懺悔錄》和拿破侖的《圣赫勒拿島回憶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盧梭筆下傳達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人與生俱來本該擁有的尊嚴與價值深深地影響著于連,使得他自始至終都為了自身的尊嚴而不懈奮斗。偉大統帥拿破侖的經歷也讓這個未諳世事的年輕人對未來滿懷激情與幻想,這使他堅信就算是最初不起眼的小人物,只要通過自身的奮斗拼搏便一定可以實現當家作主的遠大理想。由此可見,在于連的身上體現了“紅色”的特質,象征著激情、拼搏、抗爭。于連崇尚拿破侖的英雄風度,渴望像他一樣身著紅色的軍服征戰沙場建立功勛。但是生不逢時,拿破侖的帝國時代已經逝去,波旁王朝的復辟使得于連的理想無情地幻滅。對現實社會和統治階級的強烈不滿使得他始終胸懷憤懣意氣難平,但是面對艱難的現實狀況,于連選擇了“黑色”道路,借外力幫助進入神學院,穿起教士黑袍,為的是將來成為一名“年俸十萬法郎的大主教”。這種企圖憑借特權階層的身份實現翻身的目標和野心的心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
其次,于連形象中的矛盾性從他不完全純粹的復雜情感中也可見一斑。于連出身的低微造成了他極強的自尊心和報復心的心理。在小說第八節(《小小風波》)中,德?雷納爾市長一家在鄉間度假的時,于連不小心碰到了市長夫人的手,這只手很快抽了回去。這大大刺激了于連的自尊心,為了設法維護自己的榮譽,他下定決心當晚無論如何都要握住市長夫人的手。之后,于連為了報復市長大人對自己的輕蔑,粉碎他的驕傲心理,開始帶著目的與市長夫人交往。于連的這種仇恨心理和反抗即使在與德?雷納爾夫人進行熱戀時,也從未停止過,他把愛情看成是他對貴族階級的報復和爭取自由平等的愿望。但是幼年失母及成長過程中關愛和呵護的缺失,又造就了于連內心深處對被愛的深切渴望。與市長夫人的交往中,于連又真真切切地付出了真情實感。與瑪蒂爾德的結合亦然—既不是出于純粹的愛情也不完全為了利益。這兩段復雜矛盾、不干脆、不純粹的情感正是于連矛盾復雜的性格所致。
再次,于連性格的復雜性體現在他的偽善。在西朗神父的幫助下,于連去往貝藏松神學院進修神學。院長彼拉神父曾對于連說過:“嬉笑就是虛偽的舞臺。”神學院禁錮壓抑的氣息和修士們麻木虛偽的面容正印證了這點,信仰不再是純粹神圣的事物,而是一種謀取利益的工具。了解到這點后,于連再也沒有提過拿破侖的名字,時刻小心謹慎、偽裝虔誠苦行,孜孜不倦地鉆研神學。但事實上,他完全不相信神學。為使人們不對他的偽裝產生絲毫懷疑,他把拉丁文的《新約全書》和《教皇傳》這兩本他一直認為毫無價值的書背得滾瓜爛熟。于連偽裝成上帝面前最虔誠的信徒,憑借自身超強的學習能力和院長的賞識,做了侯爵的秘書,混跡貴族圈。然而于連卻時時對上層社會的虛偽,驕傲,感到不屑和鄙視。在這種不屑中,又仍舊偽裝著企圖達到更高的地位。這種無厭的野心和自命不凡的清高,將于連性格中的復雜性表現的淋漓盡致。
最后,于連性格的復雜體現在他悲劇性的結局上。法國學者馬爾蒂努說:“這樣一個結束于連一生歷史的結局,要比他的野心幸而實現更為和諧,而且是給個人斗爭與階級斗爭作出的唯一現實主義結論。”于連性格的雙重性與復雜性實質上是19世紀平民階層與小資產階級的投影,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不愿向統治階級屈服,對其恨之入骨。但同時又不愿團結人民群眾,而是企圖依靠個人的奮斗拼搏改變自身命運。正如拜倫塑造的“拜倫式英雄”:高傲而倔強,孤獨而憂郁,神秘而痛苦。與社會格格不入但是又與之抗爭到底的叛逆者英雄形象。雖然他們的不屈精神讓人感動,但是一味地獨自抗爭而不聯系具體的時代,最終淪為社會汪洋中的“孤島”,為時代犧牲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