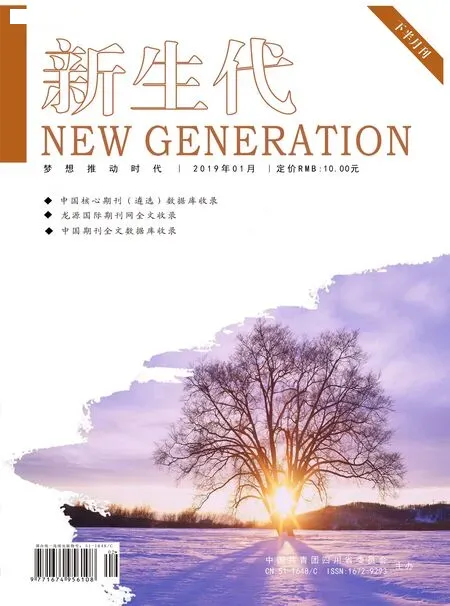具身認知:語言認知的跨學科視角
史新 魯東大學 山東煙臺 264025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與學術理論的發展完善,經典認知科學局限性的逐漸被發現,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的出現代表了認知科學一個新的研究綱領和研究取向,認知科學再次掀起一場認知革命,因此G.Lakoff & M.Johnson 以具身認知為標志,傳統的disembodied cognition和embodied cognition剝離開,分稱為“第一代認知科學”和“第二代認知科學”。[1]直到本世紀初期,國內學者才將注意力轉移至這一領域,多家期刊如《心理學報》、《心理科學》開始發表有關具身認知理論的專業論文,近年國內關于具身認知的研究逐漸增多。
本文主要討論具身認知與認知心理學中語言部分的關聯。
一、具身認知
(一)概念
“具身”是指人對身體的體驗,關于具身認知,首先涉及到的是對embodied和embodiment的翻譯理解和界定,這是一個綜合性、跨學科并內涵復雜的概念,因廣泛出現在眾多領域,學界對其的界定和理解和翻譯均不是非常清晰,也不統一。
國內關于embodied /embodiment的譯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五種[2]: 一是“身體性”。究其根本而言,在于embodied這一單詞的淵源可回溯至現象學,此處涉及的身體不是生理學或物理學中的身體,而是能夠替代心身二元對立的模式對個體進行探討的。二是“涉身性”。該譯法認為embodied來源于Merleau-Ponty提出的知覺觀,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涉身性思想,比如做出知覺活動的主體是有生命力的身體,而非內在思想。因知覺的本質是含混性,所以與之相關的活動也有非表征的特點,基于此,“涉身”有“涉及身體”的意思。三是“具身性”。從發生和起源的觀點看,心智和認知必然以一個在環境中具體的身體結構和身體活動為基礎。最初的心智和認知是基于身體和涉及身體的,心智始終是具(體)身(體)的心智,而最初的認知則始終與具(體)身(體)結構和活動圖式內在關聯,因此 ,將“embodied”譯為“具身的”,,將“embodiment”譯為“具身化”、“具身性”,將“embodied cognition”譯作“具身認知”。[3]四是“體驗的”。國內外語界不少學者將其譯作“體驗的”,“ embodied philosophy”譯為“體驗哲學”。五是“體塑 的”。在心理學角度看,多將embodied和embodiment理解為“具身”和“具身性”。
具身認知強調身體在認知的實現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一是認知期間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本質上是取決于身體的物理特性的,比如人的感知能力,其中涉及的廣度、深度以及能夠感知到的極限等,均為身體的物理屬性所主導。二是認知是具身的,認知的內容來源于身體,認知依賴于經驗的種類,這些經驗出自于具有特殊的知覺和肌動(motor)能力的身體,而這些能力不可分離地相連在一起,并且共同形成了一個記憶、情緒、語言和生命的其它方面在其中編織在一起的機體(matrix)。[4]三是身體是嵌入環境的,認知、身體和環境組成一個動態的統一體。
(二)具身研究的提出與發展
從心理語言學的視角,認知科學主張心智活動其實是心理語言的重組和加工過程。認知科學的符號范式和聯結主義范式主張認知的信息加工超脫于身體之外,心智不受身體制約,是與身體保持特定距離,并按照特定規則處理信息的機器,即人的認知是無身(disembodied)的。經典笛卡爾主義是身心二元論的肇始,這一理論關注人的理性思維,忽視人身體結構與屬性所處環境的影響,在笛卡爾看來,人的觀念活動與身體沒有任何關聯,后者同樣與心靈的思考活動無關。這一理念也基本得到了后人的繼承和傳遞,即心智可以脫離物理實體性質的身體而單獨在心靈內完成,信息和語言加工可以脫離身體而單獨進行,認知只不過是一個表征或符號計算的處理過程。
伴隨著哲學現象學的轉向,對身體的理解與思考的視角也在發生根本改變,拉開關注身體哲學的序幕。尼采和海德格爾扭轉了傳統身心二元論對身體的忽略,把身體推崇至至高無上的位置,也開創了從身體視角審視倫理和理性思維的視野。20 世紀末認知科學思想家拉考夫和約翰遜又進一步敘述了該理論,他們認為人通過身體來體認這個世界,在體認過程中不斷修正心智的狀態與形式。能否正確理解人的心智,關鍵在于身體的作用,具體而言,是運動系統與感覺系統的共同作用。唯有身體與思維共同作用,人們才可更好地認識這個世界。
二、具身認知下的語言認知研究
具身認知研究成為國內許多學科的研究熱點,并已彰顯出對哲學、認知科學、認知心理學、認知語言學以及認知神經學研究的巨大張力。
其中具身認知理論的一個應用領域就是語言認知范疇,語言作為人類認知的一個領域 ,與其他認知領域密切相關,并且本身也是心理、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反映。[5]語言結構依賴并反映概念的形成過程 ,而概念的形成過程又以我們自身的經驗為基礎。[6]這就是說,概念的形成過程往往是基于人的親身經驗,換言之,即語言并非由任意符號所組成的,而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人類本身的知識、經驗及話語功能等。國外國內許多學者都曾專門探討過認知語言學。
關于這一領域的語言的研究主要以具身認知作為哲學基礎構建認知語言學, 以王寅等為主要代表,根據G.Lakoff& M. Johnson的具身哲學(體驗哲學)表述了認知語言學的具身思想,具身哲學(體驗哲學)是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新興的認知語言學體系:“堅持體驗哲學觀,以身體經驗和認知為出發點,以概念結構和意義研究為中心,著力尋求語言事實背后的認知方式,并通過認知方式和認知結構等對語言作出統一解釋的、新興的、跨領域的學科”。[7]除此之外,他還提出語言具有天生的體驗性,且結合理論與實際經驗,對這一觀點展開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與論證,分別基于語言的體驗性、體驗哲學、社會性、人文性、勞動創造語言、隱喻的體驗性以及中西方學者對體驗哲學的研究對比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論證。至于語言本身的研究與考證,涉及的層面則有以下幾種:一是語音;二是詞匯;三是句法;四是詞法;五是語篇。而社會文化層面的論證性研究則以語言的多元化為主,詳細地論述了認知、語言、文化及現實等多個因素之間的互動與關聯。
許先文等明確地將具身認知和語言認知結合起來,提出并闡釋一種新的語言認知研究范式:即語言具身認知(Embodied Language Cognition簡稱為ELC),為認知語言學與具身認知融合打開一個新的研究視域。[8]許先文教授把“身體”的概念融入到語言認知中去,他把語言具身認知的基本內涵概況表述為五點,第一語言認知覆蓋了身體真正參與的活動;第二身體則相當于這種活動的中樞神經,主要表現在人們對語言認知所持有的態度、實際進程及效果點評等;第三語言認知所涉及的身體除了生理學上的基本含義之外,還被視為動態系統,主要幫助人們捕捉語言中所隱藏的信息、加工記憶;只有在第五身體參與之后形成的語言認知才可以充分地體現語言認知的有效性。總的來說,“身體”這一元素是語言具身認知的研究前提,也是該理論體系形成的關鍵。
這種關于語言研究的新視角、新理論將具身認知、心理語言學與語言理解相結合,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具身語言理解觀。典型的具身語言理解觀包括Glenberg的索引假設、Zwaan的浸入式經歷者框架、Feldman和Lakoff 的語言神經理論。[9]其相關實證研究其中以鏡像神經元的發現最具有影響力和代表性。
另外,還有一種研究視角是提取具身認知的部分內容融入外語學習。例如英語教學,在中國,孩子們從小就要學英語,英語的教學費時長,效果卻不甚理想,這是因其僅強調語言語法規則本身,機械的記憶,沒有與之對應的知覺經驗和情感體驗。而李宵翔等人則進一步探究了體驗哲學和英語教學之間的認知關聯性,且為當代大學英語教材的編制提出了幾點建議,以供參考。體驗哲學是認知語言學在哲學層面上的前提基礎,不僅為外語教學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與支持,還為研發英語教材發掘了不同的切入點。比如許先文教授,就基于具身認知的指導,為語言認知與英語理解構建了一個心理模型,在他看來,語言既是身體的一種活動產品,那么對語言的認知就一定要跟身體相結合,從而達到語言的具身認知,這也是最快的英語記憶法,借助特定語境下的語句體驗,為之建構出豐富的語句結構,其中也囊括了操作性較強的聽、說、讀、寫,這種以身體的動作模擬為基礎而投射的內容更有利于加深人們對語言的學習理解。學習英語應當在英語應用過程中努力誘導自己的情景想象、動作模擬和情感體驗,以便借此增進對英語語句的具身認知能力。[10]
三、國內具身認知研究面臨的問題
具身認知在國外已然成為現今研究的熱點之一,且已經有很多相對成熟的研究結果,包括具身認知理論上內完善,大量的實證研究揭示了具身認知的心理機制以及廣泛的應用價值。相比之下,國內對于具身認知研究才剛剛起步,處于還不成熟的早期,可以說在理論與方法上,都面臨著太多的問題。
這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國內關于具身認知的研究并不成體系,可以說是存在著各學科自說自話、各自為戰的局面,個學科之間的對話,互補和統一的研究模式尚未形成; 第二,國內學術界對國外具身認知研究進行了大量的介紹性綜述,缺乏創新;第三,與第二點類似,目前國內學界關于具身認知的研究,主要是從哲學或理論上闡述,多是理論框架,相對的實證研究和應用研究比較缺乏;第四,目前國內學界將具身性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本土研究相對較少。
基于國內具身認知才起步不算久,能取得如此成績已然不易,展望未來,具身認知還有很多可以挖掘和擴展的方向,如在心理學領域,未來可應用腦成像等科學技術開展對具身認知的實驗研究,從感知覺、記憶、情緒和語言等多角度,研究具身認知的心理機制。對于具身認知的多學科、跨領域的交叉研究將成為趨勢,構建一個多樣性的統一的具身認知理論,語言認知研究也會走向更好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