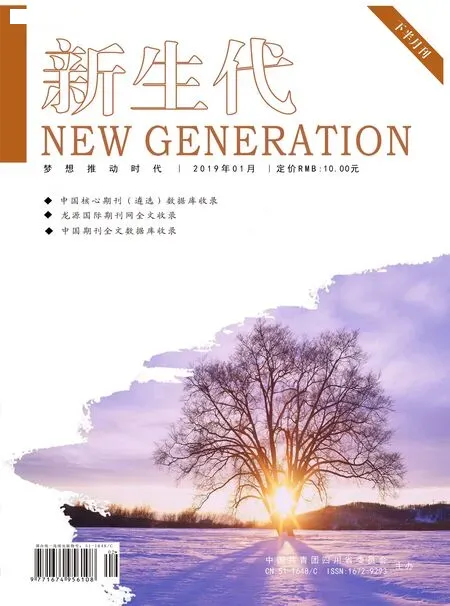生態恢復性司法的困境與完善
盧凌霞 江西理工大學 江西贛州 341000
一、生態環境領域適用恢復性司法的內涵與價值
(一)生態恢復性司法的內涵
恢復性司法起源于加拿大,是“非犯罪化、刑罰人道化輕緩化、法律親和化民主化”等理念萌發和傳播的產物。生態恢復性司法指的是對于生態領域的犯罪行為,通過促成刑事和解,將犯罪嫌疑人的補植復綠表現作為悔罪情節予以裁量,依法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或從輕處罰的決定。不同于傳統的刑事司法所主張的加害人與被害者之間的對抗關系,恢復性司法則更加注重糾紛的實際解決與效果,主張用“恢復性正義”來關注犯罪后果以及如何消除犯罪所產生的影響。
(二)生態恢復性司法的意義與價值
在生態環境領域開展恢復性司法,無論對社會還是對犯罪者個人,都能達到雙贏的效果。一方面,它體現了刑罰功能,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能夠在少用或不用刑罰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抑制犯罪,并合理利用犯罪人資源,達到用最小的支出獲取最大社會效益的效果。另一方面,恢復性司法符合生態文明建設本質,恢復性司法不僅僅意在懲治犯罪嫌疑人,更著眼于如何充分發揮犯罪人的主觀能動性,將被破壞的生態補償回來,從而真正解決環境破壞的實際問題。
二、生態恢復性司法所面臨的實際困境
(一)法律依據存在不足
自恢復性司法理念廣泛傳播以來,在我國以刑事和解為中心的恢復性司法理念下,恢復性司法主要適用于未成年人犯罪領域,而對于生態環境領域,卻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規定,具有以下情形的才可適用刑事和解:一是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是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而破壞環境犯罪規定在刑法第六章,多為故意犯罪,故對于破壞環境犯罪的刑事和解,法律依據方面確實存在不足。
(二)法理方面存在質疑
適用生態恢復性司法的案件中,法院通常是在刑事和解、向被告人發出補植管護令后,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或從輕處罰的決定,而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辦案期限的限制,法院若在被告尚未完成補植復綠時便作出判決,于法理而言難以自圓其說。同時,“補植復綠”作為由司法機關所確立的義務,極具身份屬性,而許多情況下,補植復綠義務常由被告人繳納補植復綠費或被告人的親屬代為履行,違背了罪責自負原則。
(三)實效性難以保證
生態恢復性司法的最終效果體現在其補植復綠義務的最終履行上,這就需要對破壞環境犯罪所造成的損失和應當恢復的補植復綠面積作出準確的評估,而對于補植復綠的標準與種植地點無明確的規定,這使得補植復綠工作無章可循。同時,在對被告人補植復綠成果的驗收上,如果被告人沒有將補植復綠義務履行到位,又該如何管控呢?
三、生態恢復性司法的實踐與完善
(一)推動立法建設
針對前述生態恢復性司法沒有直接法律依據的困境,通過推動立法賦予生態恢復性司法明確的法律地位,做到有法可依,成為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建議在下次的《刑法》修訂時,增加一項生態恢復令,即法院在辦理破壞生態環境犯罪案件中,附加或單獨判令被告人補種林木,恢復生態。同時,考慮到生態損害的特殊性,不允許通過經濟賠償的方式替代被告人的補植復綠義務,防止“以錢贖刑”。
(二)嚴格把控條件標準
生態恢復性司法案件適用時,應嚴格把控好條件標準。如福建省龍巖市長汀法院將審判工作分為“庭前三調查”、“判前三落實”和“判后三督促”三個階段。“庭前三調查”是查清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查明被告人能否完成補植復綠工作、查探案件解決的有利因素。“判前三落實”是引入社會力量解決專業性疑難問題、及時采取保全措施落實環境保護。“判后三督促”是保證被告人義務履行到位、保證司法建議和法律意見落實到位、保證釋法宣傳工作到位,確保司法機關的生態恢復性司法措施能夠轉化為生態恢復成果。
(三)鞏固成果完善機制
對于生態環境保護所面對的司法需求,需要建立全方位參與的系統性保護機制。這要求司法機關、環境行政機關、其他組織、公民個人之間的互相補充與促進,整合各方面力量共同保護自然資源。一方面,要建立信息共享,通過“兩法銜接”平臺,共同排查生態案件涉罪線索,及時有效的掌握生態環境領域涉案情況。另一方面,要加強協作配合,各部門之間建立聯合執法機制,對涉生態案件啟動快速辦理機制,從而實現對生態環境犯罪精準打擊。最后,還應注意的是,司法程序的結束并不是生態恢復性司法的終點,只有加強后續的跟蹤監督,確保被告人的補植復綠義務履行到位,使生態環境確實得到恢復,才是生態恢復性司法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