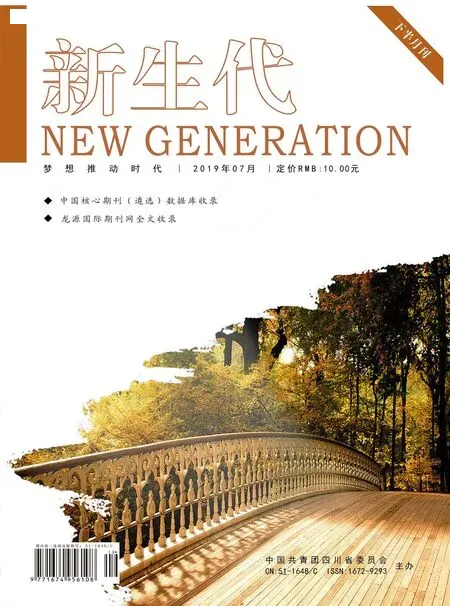淺析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姚伊霖 華南師范大學 廣東廣州 510006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起步較晚,最初的基本原則與基本規定始于憲法中規定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的規定.從憲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關系來看,憲法是靜態的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是動態的憲法,為維護憲法制度發揮重大作用.
1997年出臺的《刑事訴訟法》在規定了禁止刑訊逼供與非法取證,但這一制度真正開始于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2010年《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吸收后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臺的新《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稱《排非規定》)進一步在該制度框架下細化.2018年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將該制度納入了法律條文中,至此,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以下,將針對我國目前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進行分析:
一、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擴張
(一)非法取證的行為方式擴張
刑訊逼供行為根據方法不同可分為硬性的刑訊方法和軟性的刑訊方法 ,《排非規定》中對非法證據排除范圍的界定包含了這兩類.前者即通常意義上的以暴力手段刑訊逼供,通過損害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的身體健康,使其配合偵查人員供述案件實際情況、提供案件偵破線索、提供共同犯罪中的其他成員等 而后者的軟性刑訊方法并非直接使用暴力手段而是通過剝奪被訊問人的基本休息權利等方式對其進行長時間、不間斷的訊問或者剝奪其基本的飲食來源,使其因為嚴重缺乏正常休息和生存保障而無法拒絕偵查人員的訊問.
不同于上述的硬性刑訊方法,刑事偵查活動中這種通過剝奪基本休息和正常生存保障的軟性刑訊方法對于被訊問人的身體健康也是一大折磨.《排非規定》對變相肉刑這一軟性刑訊方法的明確規定,突破了刑事訴訟法與2010年的司法解釋,后兩者僅規定了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 變相肉刑即是對"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的進一步細化,有利于進一步保障被訊問的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
但并非出現以上情況均應排除,《排非規定》中明確非法證據達到排除標準的另一個條件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愿作出的供述"的程度.這一規定為界定非法證據提供了依據和標準,也為審判人員留下了裁量空間.在何種情形會使被訊問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仍需要在審判活動中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定奪.
(二)非法取證行為針對的對象擴張
另一方面,偵查活動中非法取證行為不僅包括對被訊問人身體上的暴力也包括心理折磨.《排非規定》第3條規定通過威脅或非法拘禁等手段嚴重損害被詢問人本人及其近親屬合法權益的方法得到的供述也要排除.不僅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還包括相關證人、被害人提供的證詞等.其中威脅的內容也不限于以施加暴力直接威脅被訊問人,仍包括損害其近親屬的合法權益.
將通過施加心理折磨和壓力的非法證據列入排除范圍,進一步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更全面保障了偵查活動的受審人.但不足的是《排非規定》在將其列入排除范圍的同時增加了排除的條件 ,同暴力取得的非法證據一樣,言詞證據只有在受審人難以承受心理壓力違背其意愿作出才屬于應當排除的范圍.但這一類施壓行為本身具有難以量化、難以判斷程度的特點,要求使受審人承受難以忍受的痛苦這一心理標準更加難以界定.這一限定條件可能使通過威脅行為取得的非法言詞證據避開排除,在刑事訴訟中難以較好實現該制度的初衷.
三、明確了重復性供述的排除規則及其例外情形
自白任意性規則時國際刑事訴訟中遵循的一大原則,即在刑事訴訟中,只有被追訴人基于其意志自愿作出的有罪供述才具有可采性,否則應予以排除.我國關于這一原則的基本確立是在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的第50條"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明確規定 .因此在刑事偵查活動中,偵查機關不得刑訊逼供.但在偵查實務中有一個爭議點,即在經歷了非法取證后,被訊問人最后自愿做出的供述與遭受非法取證時所提供的言詞證據相同的情況下,這一重復性供述是否也屬于不予采納之列, 理論與實務界的爭議主要可概括為以下三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不予排除.首先,刑事訴訟法并未對此類供述作禁止性規定,即排除重復性供述沒有法律依據.其次,犯罪嫌疑人在后來沒有非法取證手段的環境下作出的有罪供述具有獨立性,并非基于先前非法行為的不良影響.但第二種意見堅持絕對排除,認為先前的非法手段會對受審人留下恐懼心理和壓力,受審人很有可能為了避免再次遭受折磨作出相同的供述.由于先前的非法手段,受審人供述的自愿性已經得不到保障,這一重復性供述已不具程序合法性,應當排除.除此之外,第三種意見認為不宜在立法上一刀切,需要根據個案的實際情況具體判斷.若重復性供述是受先前非法取證手段的不良影響,則應當將這一重復性供述視為非法證據一并排除 但如果偵查機關積極糾正不當行為,消除非法取證行為的影響,為被訊問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保障并使其明確訴訟權利及認罪后果,這一情形下被訊問人出于自愿再次做出的供述若與之前的供述相同,則不應當列入排除范圍,否則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以及不利于對犯罪行為的打擊.
綜上而言,第三種裁量式排除的觀點較適合刑事訴訟的司法實務,《排非規定》對于重復性供述的采用也適用了這一觀點,明確指出受偵查機關先前非法取證手段影響的重復性供述不得作為定案依據,但排除先前不良行為影響的供述可以不排除.對于消除先前不良影響的判斷標準包括偵查活動中的偵查人員是否發生變更、變更后的偵查人員是否明確告知被訊問人其訴訟權利以及再次訊問的時候、被訊問人是否知悉其認罪的法律后果等.并且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角度出發,絕對地排除重復性供述不利于其享有認罪認罰的機會.因此面對偵查機關積極排除不良影響的供述,審判機關應從多個方面綜合考量再做出取舍.
四、制度程序保障不完善
"無救濟則無權利",任何法律賦予的權利只有落實具備配套的救濟程序才有其存在的實際意義,若無法通過程序救濟而使合法權益因不當行為遭受損害的,權利將只停留在法律文本之上,無法得以真正實現.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救濟目前存在以下3個問題:
(一)啟動程序可操作性弱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提出只有在審判階段.但《排非規定》在第14、17、23條分別對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中,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進行了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各階段的合法權益.不過也存在一定不足,雖然刑事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初步舉證責任仍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線索或材料并達到申請條件,否則審判機關可以申請人不符合申請條件為由不予受理.在我國刑事訴訟階段中,控辯雙方在刑事訴訟中地位不平等,偵查機關更容易證明證據的合法性,而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證明證據非法的難度更大.并且,即使完成了初步舉證責任,該制度是否啟動仍存在很大的彈性空間,《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非法證據調查程序的啟動是在法官認為可能存在非法證據的情形下.這一判斷標準過于主觀,法院可能以不需要為由拒絕啟動該程序.
(二)舉證責任落實困難
雖然控方對于非法證據的不存在承擔舉證責任,但根據《刑事訴訟》第60條,判斷標準是"確認"和"不能排除"兩種情形.在實務中,公訴人在面對非法取證行為責任承擔的時候,可以不斷進行說理和補正,并且可以通過證明證據材料的取得符合法律規定從而證明公訴機關取證行為合法,并不能實現該制度設想的保障.
(三)缺乏救濟和保障
《排非規定》第36條規定法院結束證據收集程序合法性審查后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寫明調查結論,但這部分調查結論無法獨立于案件的實體裁判.則刑事被告人及辯護人非經抗訴或上訴,無法單獨對非法證據的不當裁量結果進行救濟.應當增加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申請被駁回時,申請人的復議復核權利以及對于程序性裁判的單獨救濟權利.
五、結語
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完整構建是學界長期以來關注的焦點.由于我國刑事訴訟與對于刑事被告人保護的認識保護較晚,在法律規制方面存在較多漏洞,需要立法者結合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實務問題不斷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