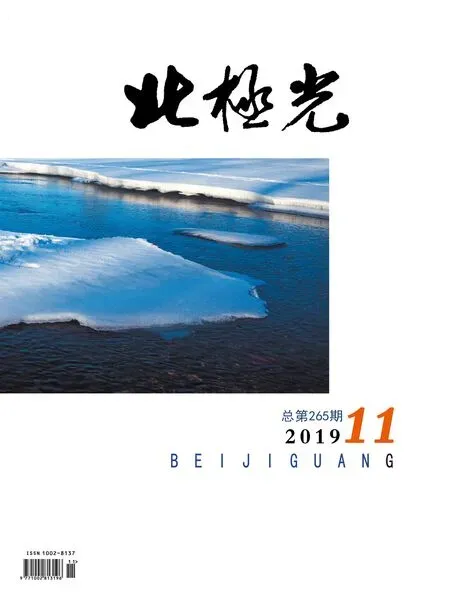鄉 音(組詩)
2019-11-12 19:29:19江九勝
北極光 2019年11期
江九勝
深秋印象
秋風起,倔強的水草矮下了一截身子
被水滋潤過的河床趁機抬高身架
柿子樹咀嚼完葉子和一些果實
骨頭就清晰硬朗起來
一隊隊的玉米秸是前赴的尖刀
立起的麥苗像蜂蛹的后繼者
落單的雁鳴是偷獵者自討的嘲諷
泣血的土地張開了傷口
黃牛的腳步不緊不慢
一些白由遠而近
收工的農者拍拍塵土
身上咸澀的晶體點亮了晚霞
鄉 音
蔬菜面黃肌瘦
向日葵迷失了方向
籬笆墻的影子不再拉長
皴裂的老槐樹熬塌了北墻
每一堵山墻上
都附著一枚血色的咒符
高樓越來越近
流經村南的小河越來越瘦
無需多年
僅存的一點鄉音
也沒了立足之地
獨輪車
生下就注定獨立行走
說是獨立
其實并不孤獨
左膀右臂是他的兄弟
那個中間的我
是從朝霞走向日落的苦力
一路負重
左傾和右傾都有險情
車輪碾壓下的薄冰
平靜中隱著猙獰
當車輪停止轉動
前程有奈何橋
轉頭就是無邊海
在老家偶遇老屋
回一趟老家
偶遇一棟最老的舊宅
黑色的瓦片泛著白
如寒冬的霜浸透了四季
舊式的木質窗戶
在垂暮老人的視線中筑起了籬笆
層層剝落的土坯墻
把皺褶的皮膚刻得更深
遠遠看了幾眼低矮的老屋
門口老兩口的頭向土地又探了一探
兩棵歪歪扭扭的老刺槐
再也扶不直佝僂的腰板
一陣風吹起
我起霧的眼睛搖晃得生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