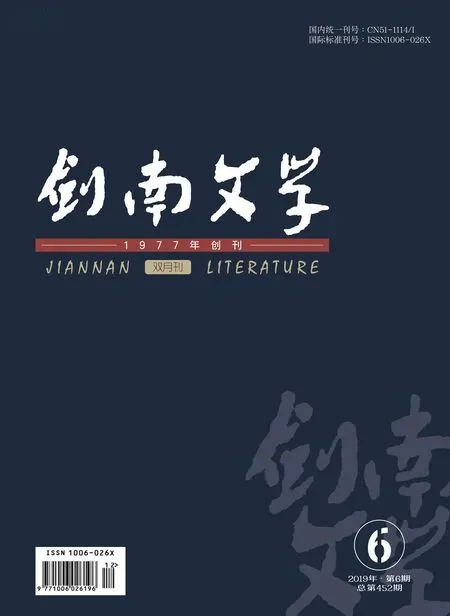遲到
□蒲雪野
記憶中,學生時代的我僅僅遲到過一回。準確地說,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回。
那是在鹽亭縣金孔中學上高中的時候。
鹽亭縣金孔中學是一所完全中學,緊挨著金孔場。從金孔場旁邊的一條小路走上百十米就來到了大操場,或者叫外操場。從外操場邊上的一道大門鉆進去馬上會見到一塊水泥地,那就是小操場,或者叫內操場。內操場的右邊站著一排男生宿舍,小操場的左邊下去一道坎也站著一排男生宿舍。從內操場遠遠望去可以見到一面墻樣的大黑板,大黑板緊靠的是一排教室。
這排教室一共有四間,我就在這排教室的第二間:80 級2 班。
那是一個秋天的傍晚,正上晚自習。校園里很靜,只有秋風與落葉在沙沙作響。
我已經不記得那天我到底怎么了,反正當我急匆匆地推開教室門的時候,班主任的講話被我突然打斷,同學們正用詫異的目光打量著我。
完了,遲到了!
我正想低著頭,趕緊回到座位上去,班主任沒有給我任何機會,她讓我倒退幾步,站到教室外面,然后用力關上門。
我分明聽見秋風與落葉在哈哈大笑,我分明感覺路燈在向我幸災樂禍地眨著眼睛,我分明感覺黑暗正不懷好意地向我涌來,我分明感覺身上的衣服正被一件件剝去……
別奇怪我有如此強烈的反應,我的這些反應與我的家庭背景和成長背景有關。
我出生在梨樹坪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五個,我排行老二。排行老二的我從小啥活不會干,只會讀書。這就給很多人一種錯覺:這娃兒是一塊讀書的料。農村,會讀書的娃兒在家里一般都很受寵,我也不例外。爸爸媽媽好吃好穿的總偏向我,姐姐弟弟妹妹大事小事總讓著我。我由此形成了一種矛盾的人格:自卑又自尊。因為貧寒而自卑,因為受寵而自尊。
多年以后,我讀到一個笑話,說是一個老秀才不小心從二樓上摔下來,第一件事是讓人看看他的假牙還在不在。
這笑話顯然是嘲笑老秀才的迂腐和虛偽的,但那卻正是我當時心態和狀態的真實寫照:把面子看得比里子重,把尊嚴看得比生命重。
還記得,有一次,在外婆家,敬愛的幺舅嫌我吃飯吃得慢,就說,別假斯文,快點吃!我覺得他不了解我,人家真斯文呢,哪來的假!為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
還記得,有一次,班里一會兒停電了,一會兒又來電了。來電的時候,我開了一下開關,被電打了。幾個同學大笑,我就覺得被美女蛇咬了,從此怕井繩。
其實,無論我多么死要面子,那晚如果沒有接下來的場景出現,我還是可以把這個罪活活受下來的。反正天已經快黑了,校園里已經很少有人走動了,除了班里同學,已經沒人看得見我在受刑了。至于秋風、落葉,就讓他們笑話去吧,他們傻瓜,哪曉得人間疾苦呢!至于路燈、黑暗還有趁黑暗伸向我的那雙黑手,就讓他們偷著樂去吧,他們笨蛋,哪值得我跟他們一般見識呢!
但是……
說實話,我對漢語里有些詞匯有些時候是很有意見的,比如 “但是”。你沒有“但是”不行嗎?你少點“但是”不行嗎?沒有“但是”,或許就沒有那么多意外發生;少點“但是”,或許就少點悲劇發生。
我不是蠻不講理,我是真氣極了。狗急了還跳墻呢,人急了還罵人呢,我發點牢騷怎么的!
但是,正在我心里翻江倒海、地動山搖的時候,我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出現了:夜色中,有兩個人影正向我走來。漸漸地,我看清了,這兩個人影不是別人,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我弟弟。父親背著背篼,弟弟緊跟在父親身后。很顯然,父親和弟弟是給我送大米、紅苕、酸菜來了。
啊,我什么時候給家里人帶信說我沒糧了?我什么時候讓父親和弟弟給我送糧了?
這真的是那個剛剛做完腸胃手術出院的父親嗎?這真的是那個整天捂著肚子、走家串戶給人理發的父親嗎?這真的是那個幾乎把蒲家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的父親嗎!
弟弟,你怎么也來了?你還這么小,就為了供我上學休學了,就開始挑大糞打谷子拾柴火養豬養牛扛起一家重擔了。這么晚了,你正可以歇歇啊,你怎么也來了?
我不知道父親和弟弟看到這個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親人此刻被罰站在教室外是什么心情,他們是不是也有好多問題要問我。我也不記得他們問了我什么,我答了什么。我只記得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法國大作家莫泊桑的名著 《我的叔叔于勒》,想起了那個曾經的敗家子于勒,那個據說發了大財的于勒,那個被全家寄予厚望的于勒,那個后來被偶然發現在游船上賣牡蠣的窮苦的于勒。
是的,我就是那個于勒,就是那個喚起家里人希望又讓他們陷入失望的于勒。我相信,菲利普一家人見到于勒是什么心情,父親和弟弟見到我就該是什么心情。
幾年后的一天,當我陪著重病的父親最后一次走過他曾經走過多少次的孫家坪、老馬坪、青崗坡時,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父親:“你還記得那年給我送糧的事嗎?”父親搖了搖頭,說是不記得了。
但我記得,永遠都記得。
我記得。所以,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都不會遲到。講課,我不會遲到;采訪,我不會遲到;約會,我不會遲到;請客,我不會遲到。
在德昌縣水利局打工時,有一天,暴雨如注,姐夫對我說:今天你可以不上班。但我不僅徒步準時趕到了工地,還自創了一首打油詩:軍人作風,戰士氣慨。說到做到,風雨無礙。
我記得。所以,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都會善待那些不小心遲到的人。當老師的時候,我很少罰站,更不讓學生站到教室外面。當部門領導的時候,也說要處罰遲到的員工,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
有一次,到一所學校采訪。大冬天的,一個孩子站在教室外面寫作業,兩只小手凍得通紅。一問,遲到了。這怎么行?我馬上找到校長辦公室,向校長反映情況。校長一聽,當即要求教師將孩子叫進教室了。
有時候,有朋友不解,問我為什么從不遲到?
有時候,有教師不解,問我為什么總是對將學生罰在教室外那么反感?
我的答案只有一個:曾經遲到過。
我還有幾個問題要問:要不你也遲到一次?要不回到若干年前?要不像我當年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