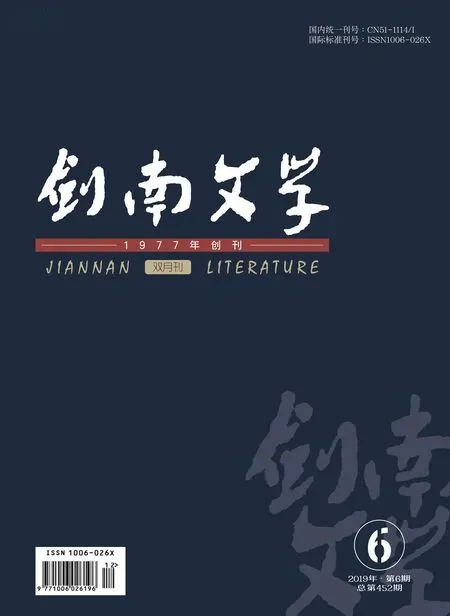石難
□楊 俊
一
洛陽的雨下得癡纏。從傍晚到清晨,從洛陽城到伊水間,最后在龍門的石灰崖壁上碰濺出萬朵牡丹,清冽綻放于野。
“龍門石窟位于洛陽伊河兩岸的龍門山與香山上。始鑿于北魏孝文帝年間,歷經魏、齊、隋、唐、五代、宋朝等400 余年的連續營造,形成了南北長1 公里,有窟龕2345 個、造像10 萬余尊、碑刻題記2800 余品的中國石刻藝術寶庫。如今,龍門石窟與莫高窟、云岡石窟、麥積山石窟并稱中國四大石窟,為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碎花雨傘下滑出的清麗女音,將龍門山伊水闕揉出一種出塵的仙靈韻,帶你尋找1500 年前絕壁之上開龕造像的身影,叮叮當當不疾不徐的悅耳斧鑿。那既有一種畫面感韻律美,也有一種跨越時空的詩意勾聯。
詩是一種介于真實與夢幻之間,用無窮想象構筑的鬼魅藝術。似是而非,亦真亦假,能得其意而不可言其狀,能無比接近真實又無法直抵真實。也唯如此,方能讓人無比自由、永無止境地徜徉、翱翔。就如同我們踏著一徑的迷蒙牡丹,在清麗解說的牽引下欣賞賓陽洞的 “維摩變”、蓮花洞的苦行僧、古陽洞的秀骨清像、蓮花洞的碩大浮蓮、皇甫公窟的飛天樂伎和奉先寺九軀巨型摩崖雕像時,想象的是北魏草徑中的枯瘦赤腳,是唐宋懸壁上的古銅肌膚,或是明清天空中滑過的一聲聲號子。細雨微風秋暝山色中,你可以穿越魏晉以降的千年時光,看佛的微笑,聽禪的偈語。
走著走著,眼前的道路變得模糊,然后就響起了慌亂的腳步聲、尖利的嘶叫聲,嘈嘈雜雜洶涌而來……
二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話用在龍門香山殊為貼切。兩山遙相對峙,一水破壁而出,讓這座天然石門擁有了一個“伊闕”的雅名。“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詩人白居易對此形勝山川是情有獨鐘的,不僅常居香山,自號香山,最終也埋骨于香山寺北、滿師塔側。晨昏聆聽誦經聲,俯仰凝目見佛陀,孤冢千年亦獨得風雅。
這樣的曠野山水又惹得了誰?怪就怪你宜人怡心的純美風情,僅距洛陽12 里的地理優勢,還有易雕善刻的優質石灰巖。經年斧鑿之工,黛綠蔥郁的原生態山體變得千瘡百孔狀若蜂巢。1400 年醞出的蜜,又引來了重洋之外貪婪覬覦的目光。
記得《北京日報》副刊版上曾刊載過一篇《龍門瑰寶被盜往事》的長篇通訊,里面考據的諸多史實、軼事可謂駭人聽聞不忍直視——關于179 年前那場戰爭,從政治體制到經濟結構,從民生民事到國力國運,乃至整個民族的自信、國民的精神,帶來的巨大創傷無法細述也不愿贅述。如果說被掠奪的物質財富還是可以再生的話,那么,飽受摧殘的文明的創傷卻深入了一個民族的靈魂,難以平復無法修葺。在世界史上,各個文明從不以資歷、名望或存續久遠論存亡,只有先進文明對落后文明的征服和吞噬,且常常是以簡單粗暴的野蠻方式在擄掠和取代。當歐洲文明與人性貪欲勾結而成的嗜血刺刀,在東方古國豐腴的大地上劃開一條深可見骨的傷口時,無數戴著禮帽打著領結穿著燕尾服的 “文明人” 嗅著血腥蜂擁而來。
兩山之間、伊水之上,一場“幾乎貫穿20 世紀上半葉”的饕餮盛宴紛紛亂亂地“開席”了,靜立石窟的10 萬尊佛像成了歐洲紳士們隨意“點選”“訂購”的文物大餐。他們或與國內不法奸商勾結,或威逼利誘附近村民,甚至還與寺廟里的和尚、畏洋如虎的地方官吏共謀策劃監守自盜,盜鏟壁畫,偷挖碑碣,砍下佛像的頭顱……
考古學家羅振常在1911 年的日記中記錄下了石窟被毀的情況:“顧小窟往往空洞無像,大龕諸佛亦多殘損,每有失其首者。”
地質學家袁同禮在現場考察后的報告中稱,龍門石窟被瘋狂盜鑿的情況以1930—1933 年最為熾烈。“龍門之南的外凹村,許多石匠都以盜鑿龍門石像為業。他們勾結土匪,夜里攜帶云梯、手電筒到洞窟中盜鑿。很快,這些被砍下的佛頭就會出現在北京的文物市場上。”
龍門石窟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這次有組織盜鑿活動也引起了西方媒體的關注。1914 年英國《泰晤士報》曾作過這樣的報道:“巨大的人物浮雕……被盜賊肆意切割、鋸斷或摔成碎塊,以便運往北京并出售給歐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館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買下他們……競爭在增長,價格在飆升,破壞的動機進一步受到刺激,變得日益高漲。”
紛紛揚揚的碎石淚,就這樣經年不絕滴落鄉野。自詡文明的西方人,肆無忌憚地干著最野蠻的勾當——這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講。
大型浮雕《北魏孝文帝禮佛圖》運到了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文昭皇后禮佛圖》 藏進了堪薩斯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蓮花洞釋迦牟尼弟子迦葉像存入了法國吉美博物館……金碧輝煌的大廳陳列著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也堂皇地展示著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占有、欺凌和羞辱!
三
癡纏的洛陽秋雨中,盧舍那大佛端坐龍門之巔,即使失了雙臂也依然豐滿圓潤妙相莊嚴。看著周遭瘡痍滿目的佛龕塑像,菩薩秀目含笑云淡風輕,通體高達17.14 米之龐然軀體似乎能容下世間所有難容之事。倒是蟻行足下一群看不透紅塵的凡夫俗子憤憤不平。他們想不明白這些佇立鄉野靜默無爭的石像,何以傷痕累累劫難不止。如果說“會昌法難”歸于佛道之爭,西方劫掠緣自利益驅使,那么五十年前那場轟轟烈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呢,僅僅就歸咎于世人的盲從和愚昧嗎?
摧毀寺院故居,搗碎神佛塑像,推倒牌坊石碑,藏書字畫付之一炬,甚至是陵寢枯冢里的遺骸也被掘出來挫骨揚灰……那些令千年文明灰飛煙滅的“造反派”們,大多是懵懵懂懂不醒世事的青春少年,或是大字不識的文盲農民,他們才不管什么是中華文明的象征、代表,什么是石刻藝術的巔峰、典范,他們被時代的浪潮裹挾著,以慷慨激昂之勢毅然絕然地“橫掃”著一切他們能夠看到和發現的文物古跡。存世1400 年,躲過了“三武一宗”之災,幸存于戰火盜鑿之禍的石刻菩薩們再一次成為“革命”的對象,不得不面臨前所未有的詭譎厄運。
絕壁之上,高大堅硬的佛像也不是那么輕易說毀就能毀掉的。那么,就揀容易的干。斷首、剜眼、殘手、搗足——你不得不佩服人類的毀滅力與創造力一樣,都具有強烈的創新性。據說,為了提高毀佛效率,有人進行了“大比武”似的競賽活動,看誰的花樣更出新,看誰毀的石刻更快、更多、更徹底。我很是懷疑,這些少年和農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這樣干的意義何在?搗下的佛頭手足,既不能賣錢也不敢私藏,最多就是聽聽佛像殘破斷裂時發出的“啵啵”脆響。
我甚至能夠想象這樣的畫面:在龍門的絕壁上,一群手拿斧鑿的人,一邊嬉笑閑侃一邊革著石刻菩薩的命。一斧子下去,一顆大好的佛頭轆轤著滾下山崖;一鑿子下去,一尊佛像便失了手斷了足;聲聲斧鑿中,沒了耳目的神佛們也就真成了一塊石頭,失了昔日威嚴,不必再存敬畏。砸得累了,就歇歇氣,抽一袋旱煙,灌一碗老茶,然后,接著砸。可恨那尊盧舍那大佛太大了,頭高4米,耳長2 米,沉沉何止十萬斤!于是,大佛得以保全。但敢于向舊世界宣戰的“闖將”們又豈能被一尊石刻的佛像嚇倒?漫步下山時,心中到底忿忿,于是一揚手,“嘭”,一聲悶響,一尊小佛像的頭顱應聲而折,骨碌碌沒于荊棘荒草間。這才昂首,挺胸,吹著口哨或哼著俚語小曲,如得勝將軍般凱旋——這樣的故事,在那段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漫長歲月里未必沒有真實上演過。
斧頭、鑿子,都是人所創造的工具,卻在“信仰”的驅使下演驛著創造與毀滅的不同劇情。曾經,四百年風雨無阻,把一座龐然巍峨生生幻化為一片祥瑞氤氳神佛世界。威嚴佛像前,升斗小民叩首以求康寧,達官貴胄折腰以祈顯重,精神的圖騰被寄予了太多的精神指向和暗示。忽然有一天,被革了命的諸天神佛不再可敬可畏,禁錮千年的精神鐐銬可以隨意摧毀——那是多么令人興奮的一件事啊!結果就是,沸騰的情緒不受約束地撒著歡兒地宣泄和釋放,甚至可以毫無理由毫無目的地盡情地敲,隨意地砸,跟玩兒一樣!
塑造時,畢恭畢敬,精雕細刻;毀滅時,毅然決然,毫不留情。紛紛揚揚的碎石淚,就這樣經年不絕滴落鄉野——成,石淚潺潺;毀,石淚汪洋。
四
渡盡劫波的龍門石窟是幸運的。2000 年11 月30 日,龍門石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被重點保護。也就在100 天后,開鑿于公元3 至5 世紀,被稱為“世界第三大佛” 的阿富汗巴米揚大佛在塔利班政權持續數天的轟炸中化為塵土。曾令晉代高僧法顯、唐代高僧玄奘明心見性、清靜明悟的兩尊巨佛,從此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段無法抹去的暗黑記憶。
成于斯亦毀于斯,這是否就是一次擺不脫的宿命因果?大佛不語,只于癡纏的洛陽秋雨中靜坐山巔,用千年如一溫潤如玉的表情,用秀眉彎月間那一縷無人能懂的微笑,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