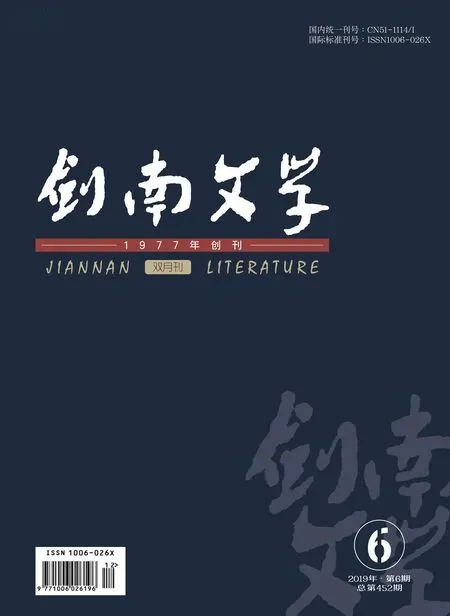小小說五題
□巴 可
月餅也硌牙
帶著幾分醉意,王局與薛老告辭。薛老的女兒香云把一個月餅塞給王局,說是自己做的,王局樂滋滋聞聞月餅,很香,就賞她一串贊美詞。
從薛老家出來,王局在夜色里散步,到清風路口,爽風吹去一半酒意,這才覺出腹中有點空。飯桌上,只顧與薛老敘舊,忘了關照自己的肚子。他摸出香云給的月餅,月餅又大又沉,咬一口,牙被猛硌,疼得他直歪嘴。月餅也硌牙,怪事,香云拿錯了?路邊有個垃圾桶,他順手把月餅扔進去。
局里決定將香云從文化站調到文化館。“調香云,并不因為她父親是老領導,在座的都聽過她演唱,那一嗓子出來,全場就像注了興奮劑,巴巴掌拍得震山響。她形象也不錯,這樣的人才不用,可惜。” 王局如此力薦,誰反對?
簽了香云的調令,王局安排人事科馬上辦相關手續,接著給薛老回電話,老人家為女兒的事懸了多年的心可以放下了。
晚報上“金子餡月餅”幾個字赫然入目,讀完全文,王局愣了。此文寫了一件怪事,一個清潔工在清風路口垃圾桶里撿了個月餅,月餅的餡亮亮的、硬硬的,經鑒定,是金子。
清風路口垃圾桶?王局想起那個硌牙的月餅,打電話問香云,香云說:“月餅如圓月,希望一切圓圓滿滿,心事如愿。金餡如心,是我一點心意,不成敬意,請王叔笑納。”
心意?王局一陣蒙。
“你的心能像皓月一樣明亮、赤金一樣純凈,你爸和我就省心啰!”放下電話,王局立即通知人事科停辦香云的調動手續。
官 運
快到那個小區了,梁子越發心虛,怕遇見熟人,就避著燈光走。月亮偏偏作對,掛在頭頂又圓又亮,把地上的枯枝敗葉照得明明白白。梁子埋著頭,手捂挎包。
樓房聳立夜空,真高,能不上嗎?梁子有些腿軟。科員八年,原地不動,鄙視像噴槍里的水,時不時噴出來欺負他,他最怕老婆罵他窩囊廢沒出息,給他白眼。還是上吧,送出挎包里的“意思”,就峰回路轉了。
硬著頭皮進單元門上樓,沒人,他的頭老老實實埋著,直到站在那扇門前才抬起來。該按門鈴,心跳得厲害,猶猶豫豫伸出的手在顫抖,手指與門鈴像兩塊同極磁鐵,怎么也挨不上。
斥罵聲驚他一跳,立即縮回手。李局在屋里罵蒼蠅。誰是蒼蠅?他梁子?定定神,確信自己沒按門鈴,不是罵他,這才松一口氣。撤吧,李局正發火呢。
主席臺上放了個裝滿紅包的籮筐,李局上臺就罵,指著那些紅包,說他出差沒一星期,成群蒼蠅就鉆進他家搞這么大一堆蛆,要把他搞得臭氣熏天啊,可惡。蒼蠅都啥面目,李局說有錄像,問大家要不要見識見識。
尖叫,聲音極短,誰心肌梗死?臺下的人望著李局,氣不敢出,眼睛都惶惶地瞪成了二筒。
梁子暗暗慶幸自己昨晚沒出手,臺上那些紅包哪個都比他挎包里的“意思” 塊頭大,忽聽李局點他名,一驚,身上汗毛立起,而后大喜。李局說基層科就他梁子沒下蛆,這樣的人不干科長,誰干?
激動,哆嗦,科長的帽子即將降臨頭上,梁子哆嗦著摸出手機給老婆發微信:“你老公官運來了,準科長指示你,挎包里的‘意思’捐希望小學。”
聚 會
林老頭臥床不起。
王老頭得知,找上門來。
林太太對王老頭說:“我家老頭子在電話里罵了你過后,就這樣了。”王老頭態度很好,接受了林太太滿眼的責備和疑問,看看床上閉眼挺尸一樣的林老頭,走過去,說:“老同學,看你面無血色,病得不輕呢。你不就是想見你的云妹妹、鳳妹妹嘛,不就是埋怨我與同學聚會沒叫上你嘛。你手機打不通,怪哪個呢。今天,給你補起,同學們都來啦。”
林老頭覷著細眼看看王老頭身后,就罵:“死老頭,把我當小娃兒哄嗦。”
王老頭嘿嘿一笑:“我王你林,我倆是亡靈(王林),死過一回,死不了啦。”扶林老頭坐起來,幫他披好衣服,王老頭把一本同學聚會紀念冊 《青春依然》給他。
林老頭翻開看,靜靜地看,靜靜地跟同學們相聚。漸漸地,他臉上有了笑意:“同學們都在這兒呢,四十年了,變了,也沒變。這個白云,還那么嫵媚,當年她跳舞跟仙女一樣,靚姿迷人啊。這個鳳凰,風韻猶在,她唱歌就像百靈鳥啼唱春天。這個禿老虎,有一回,他寫黑板報,我用毛筆在他屁股上悄悄畫了個長長的等號,說他左邊屁股等于右邊屁股,哈哈哈哈。”
“林老頭,你咋面色紅潤了,沒病?”
“扯淡,哪個有病?”
“既然沒病,賴床上干嗎,雞婆抱窩啊。走,咱哥倆打門球去。”
林老頭活動一下胳膊:“好!”
靈魂在廢墟上顫抖
身子晃得厲害,白蘭立即蹲下,樓房篩糠似地抖擺,隨著破碎和轟然崩塌的聲音,翻卷的塵土撲向她。
哭聲拽著靈魂奔跑。
“吉祥,吉祥。”白蘭嘶啞的喊聲與遠近驚呼混在一起,試圖把飛揚的塵土喝退。
四周模糊,樓房呢?眼前怎么是一群怪狀悚魂的巨魔?她戰戰兢兢在魔群中尋吉祥。世上可以沒她,不能沒她的吉祥。
“阿姨,救我。”
白蘭循聲從廢墟空隙往里看,杜小龍?這狗崽的媽兇惡的樣子立時閃現,她臉上的傷痕又在作痛,不禁怒火中燒,瞪一眼伸向她的手,走了。
不停喊吉祥,她辨認從廢墟里救出的那些生死不明的小孩。一個女孩吊著一只血糊糊的胳膊,抬起另一只胳膊指前方,告訴她那邊在救小孩,她趕緊過去。
魔嘴齜著牙恐嚇人們,有人向魔嘴里喊話,她擠過去,喊話的是位大爺,大爺說一個女人爬進去救兒子,剛才那陣余震后,里面就沒動靜了。
白蘭大聲喊吉祥,突然,她激動起來,她聽見了兒子的聲音,兒子就在魔嘴里!
解放軍與人們一道,從魔嘴里奪生命。廢墟下一個女人滿臉泥血,用身子為吉祥撐著一個空間,看不清她是誰,她死了。
吉祥獲救,躺在擔架上說:“杜小龍的媽媽幫我取壓著的腿,她又被壓著了。”
聲音很低,卻如晴天霹靂把白蘭的身子劈軟了,那個死去的女人是杜小龍的媽!又一陣余震,搖晃中,白蘭聽見有人喊她,喊聲低沉而浩大,是大地震動的聲音。
剎那,杜小龍的手從廢墟里伸到她眼前,她內心的地震爆發了。
她顫抖著身子,顫抖著靈魂,帶著救援的人們向那只手奔去。
皺紋里的慈祥
大城市生活節奏快,方芩上班、理家、帶雨兒,實在忙不過來,要請個保姆。
母親從鄉下趕來,把雨兒抱在懷里,啥也不說。方芩明白母親的心思,呆呆看著母親滿臉如溝如壑的皺紋,皺紋里泥土和炊煙的味道再次泛起她內心的隱痛。母親這輩子太苦,不能讓她走出貧苦的山谷,又鉆進辛苦的籠子。這里的喧囂、緊張和幾乎把人逼成神經質的苛求,不適合母親,那個清寧小山村才是她苦中尋福的地方。
“媽,回去吧,爸身子不好。”
母親抱著甜睡的雨兒不放手,眼眶濕濕的。
方芩家第一任保姆是個姑娘,姑娘不會抱孩子,雨兒在她懷里老是哭,沒兩天,姑娘就撂擔子了。朋友帶來一位大媽,大媽養了三個兒子,個個體壯如牛,都出息了。面對養兒高手,方芩喜出望外。
沒幾天,雨兒腹瀉了,大媽把幾十年前的經驗使出來,雨兒還是腹瀉不止。眼看雨兒一天比一天瘦,方芩著急,大媽也急。一串鑰匙放桌上,大媽出去后再也沒回來。
后續保姆要么嫌方芩家房子小得像籠子,要么嫌事多,屁股沒落座就走了。方芩憋得團團轉,向社區家政服務中心求助,對方說早有人指名道姓要做她家保姆,叫她下午在家等著。
下午,擔心來人扣門聲小,方芩緊挨門邊坐等。門被叩響,她條件反射,從沙發上彈起開門。
母親一臉皺紋出現在門口,皺紋里輕輕漾著慈祥。
方芩鼻子一酸,禁不住滿眼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