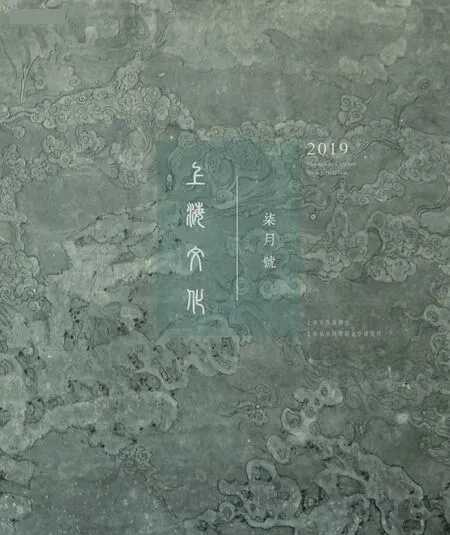孫頻小說論
韓松剛
一個作家被貼上標簽,到底好還是不好,其實不太好說。貼標簽是風格化的一種體現,是一個作家一定階段創作的穩定和成型,但這種穩定和成型也容易成為一個作家進一步突破自己的障礙和難度。
孫頻自2008年開始創作,至今已經十年。十年里,寫了兩百余萬字,出版了若干部小說集,已然小有成就。孫頻的小說以中篇為主,并以善寫身體、情欲,以表達孤獨、絕望,以尋求突圍和救贖,自成一格。
但正是對女性和身體的過度書寫,孫頻不自覺地成為被“標簽化”的一位作家——一位女性作家。關于孫頻小說的風格,評論界頗多爭議。贊同者有之,持不同意見者亦有之,這其實都不重要。孫頻的小說像一道道傷口,恰如她在一篇小說中描述的,這傷口露著猩紅色的里子,紅色之下是若隱若現的幾點雪白,那是骨頭。想來,有些凜然;讀罷,卻是“刻骨銘心”。
我認識孫頻,源于內人。她十分喜歡孫頻的小說,并寫過一篇短評《她與世界短兵相接》。她在文章中寫道:“孫頻拒絕對生命虛無本質的漠視與淡化,她近乎殘忍地將人性的幽微晦暗、猥瑣卑賤一刀一刀刻畫出來,她帶著原生的驕傲對庸常的幸福嗤之以鼻,她敢于放任自己筆下的女人在罪孽中層層受苦,并通過‘看’與‘被看’這種審視的方式,探索和剖析自己內心的黑暗,認識并承擔自己的罪,渴望借此獲得復活與重生。”她十分準確地把握了孫頻小說的意圖和本質。
后來,孫頻從山西調到江蘇作協做專業作家,我們就此成為同事。2018年,省作協給孫頻召開了研討會,也是籌備這次會議期間,我開始閱讀孫頻的小說。但我的閱讀順序,是逆時針的,最早地從《松林夜宴圖》,然后再讀她早期的作品。讀過這些小說,漸漸厘清了我對孫頻創作的認識和理解。她的小說固然存在著模式化和理念化的弊端,但好比一件件構造相同的武器,外形大同小異,威力卻截然有別。
孫頻的小說有獨特的意味。孫頻的獨特,得到了不少評論者的關注。苦難、卑微、存在、救贖,這些都是辨識和理解孫頻小說的關鍵詞。孫頻似乎對這個世界存在著一種天生的恐懼,她對這個世界和人性的追問,應該就源于這種恐懼和不安,她要撫平傷口,撫慰靈魂,雖然最后發現,一切終是徒勞。但是,孫頻的厲害之處在于,只要和這個世界產生緊張的關系,她的小說就有著耐人尋味的品質。這種緊張通過身體、靈魂、黑夜、屈辱等等,一層層地剝展開來,血淋淋地令人不敢直視。比如《乩身》中,人性的壓抑慘烈到極點、窒息到極點,似乎世界就在一瞬間崩坍,毫無希望可言。可是,作為作家的孫頻,有著她卑微的憐憫。正如她自己所說:“我寫的每一個人物,不管他丑陋還是讓人憐惜,我都對他付出了絕大的深情還有真正的同情。人對人最高的同情是什么?就是憐憫。”因此,她的小說還給人留以希望,哪怕是短暫的、渺茫的希望。還是在《乩身》中,常勇和幻影在黑夜中喃喃對話,互相擁抱。這時,孫頻寫道:“這種虛幻的崇高感緊緊地裹著她,有如給她塑上了一道金身,她在黑暗中感到了自己此時的祥和、寧靜、美麗。她的淚嘩嘩往下流,就為了能與這些幻影擁抱,她真的情愿再不醒來,她情愿就在夢中要一個個長長久久的擁抱,情愿她自己也只做一個沒有肉身的幻影。”這希望是如此地卑微,又如此地渺小,卻也如此地令人感動,令人無地自容。這就是孫頻,以個人之痛觸摸人性之痛,以個人之傷撫慰靈魂之累。
孫頻當然不愿沉湎于這些痛苦之中,她渴望筆下的人物能夠自救和得救,而她的寫作也是向那些在這個世界上認真、執著、堅強地活著的人致敬。救贖的方式是什么?在孫頻大部分小說中,希望往往指向了宗教性的旨歸。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這樣的宗教性處理,的確引人深思,同時,也引起了十分大的爭議。以我個人的觀點來看,這樣的處理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限制性,合理性在于獲得了精神的提升和靈魂的安落,尤其是具體到個別的文本來說,產生了切實的藝術價值和審美效力,限制性在于,這樣的處理在不少小說中有了同質化和模式化的意味,因此,也便值得作家反思。
孫頻喜歡寫愛情,當然,哪個作家不喜歡寫愛情呢。只是,在孫頻的筆下,愛情,源于那些最不起眼的曖昧和欲望。與此同時,連同著卑微的肉身,一共構建起她早期小說的美學風格。但如果僅僅以此來認知孫頻的作品,仍有失偏頗。孫頻的小說,不僅有小的微茫的個體,更有大的宏闊的時代。個體的微不足道,終究要靠時代和歷史來凸顯。《乩身》中,常勇之死,與其說是個體自身的覆滅,不如說是趨向時代的死亡。孫頻是用個人的細小無常折射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精神狀況。
孫頻喜歡寫死亡,孫頻對于生死的癡迷,其實比她對肉身的探求更加深入。與卑微中的堅持相比,死亡中的重生似乎更具有一種耐人尋味的哲思力量。愛得刻骨銘心,死得痛徹心扉,這就是孫頻對于這個世界的真實體驗和沉痛想象。在孫頻的小說里,愛令人絕望,死令人震撼,希望如同灰燼,絕望恰如重生。還是在《乩身》中,“在一切苦難之后,所有的人都會再次相見,再次擁抱。在即將失去意識的最后一秒鐘里,她的盲眼在金色的火焰里第一次看見了她自己的身影,一個女人裊娜的身影站在一條金色的大河邊,一頭拖及腳跟的長發,衣袂紛飛,她正低頭看著自己在河中的倒影,如臨水照花”。常勇,終于在死亡來臨的最后時刻實現了自我的“復活”。這是孫頻式的決絕和勇敢。孫頻的小說是對人性與靈魂的審判。這審判是慘烈的,如鹽入傷口,浸入骨髓,這審判是徹底的,陷自我和他者于萬劫不復。這樣的寫作,于孫頻來說,太過于兇猛了,甚至于是對自我生命的透支。所以,就有了大家對她創作轉型的期待。
還好,這樣的期待,時間并不長。小說集《松林夜宴圖》出版了。小說集《松林夜宴圖》收錄了孫頻最新的三個中篇:《萬獸之夜》、《光輝歲月》、《松林夜宴圖》。非常巧合的是,這三篇小說的題目都和“時間”有關,不管是有意或者無心,我想,孫頻應該是一個“時間性”很強的小說家。小說,一定意義上,就是時間的重演。孫頻在關于《光輝歲月》的創作談中說,“這曾經的時代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對于向死而生的人類而言,都將成為光輝歲月。”不管這時間是指向過去、當下或者未來,時間性“把如此這般作為存在著的有所當前化的將來統一起來”,好的小說就如同不可捉摸的時間一樣,始終是個謎。
孫頻說,這三篇小說是她的轉型之作。這種轉型,在我看來,是她試圖擺脫被一種過于“個性化”的風格奴役著的嘗試和努力。這種嘗試在《萬獸之夜》、《光輝歲月》中有點淺嘗輒止的意味,至少變化不是特別明顯,但到了《松林夜宴圖》中,孫頻可謂是完成了自我創作的風格“異變”。寫作《松林夜宴圖》的孫頻,少了徹底決絕、勇猛激進,多了寬和從容、蕩氣回腸。她不再一心癡迷于人類那具沉重的肉身,而是向生活的更深處、向生命的更細微處、向歷史的更不確定處,探求一種與靈魂、與人性、與時代的對話。《松林夜宴圖》的寫作,預示著孫頻在小說寫作的藝術探索中漾出了一片新天地。
英國著名詩人、評論家W.H.奧登說,藝術風格的變化總是反映出社會想象中神圣事物與世俗事物之間的邊界的轉移。于孫頻來說,也是如此。她正在從抽象感官的情感世界中抽身而出,投入到五彩繽紛的日常和歷史之中。具體到小說寫作來說,我覺得有四個方面的轉變:一是試圖擺脫一種慣常的情感表達的束縛;二是努力尋求一種比較深刻的醫治精神創傷的方式;三是對于肉身的迷戀,正在從一種本體的存在,變成一種審美的虛構;四是開始重視小說形式的意義。
這樣的寫作,于孫頻來說,太過于兇猛了,甚至于是對自我生命的透支。所以,就有了大家對她創作轉型的期待
孫頻是個“問題”意識很強的作家。這種問題意識在她早期的小說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甚至于太過明顯,從而影響到了小說的藝術質地。可能正是這種過于突出的問題意識,限制了孫頻小說寫作路向和風格多元,以至于受到評論家關于她作品“同質化”的批評。我想,孫頻對此,一定早有察覺。因此,也才會有《松林夜宴圖》的驚艷問世。《松林夜宴圖》中的故事,顯然已經超出了孫頻個人的經驗世界,她通過介入歷史的方式——這個歷史也顯然不是她所經歷和熟悉的歷史——試圖構建出個人與歷史、與時代、與世界之間的一種錯綜復雜的生命面相。
可是,我仍然懷疑,當代小說還能表現出新的情感體驗嗎?還能開辟出新的情感空間嗎?英國作家D.H.勞倫斯在《小說之未來》一文中說:“它應該有不用抽象概念解決新問題的勇氣,它必須向我們展示新的、真正新的感情和整個兒全新的情感軌道,從而使我們擺脫舊的感情套路。”在情感世界中摸索了十年的孫頻,似乎也正在尋求一種新的情感可能。尤其是她對于女性情感世界一如既往的執著,使得這種擺脫顯得更加必要。孫頻的小說人物主要以女性為主,并每每以女性肉身的饑渴欲望作為情感的出口,來表現個體與時代的對立與撕裂。這肉身是沉重的,有著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但在《松林夜宴圖》中,孫頻為自己打開了肉身的另一扇窗,從而以一種有別于饑渴的饑餓之感重新來打量、感受這個世界。而尤其可貴的是,這種虛浮的饑餓感,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內心的空虛、精神的渴求建立了一種互文的轉換,由此才不至于讓這司空見慣的饑餓狀態失去了“歷史”和“記憶”的填充。小說在關于外公的一段描寫中寫道:
他看起來內里總是很渴,很餓,很空,無論扔進去多少東西都填不滿,都能馬上聽見空蕩蕩的回聲。好像他患上了一種奇特的類似于饕餮的疾病。然而就在那些剛剛吞咽下食物的清醒瞬間里,他仍然會哆哆嗦嗦地拉住她的手,催促她去看倫勃朗的畫冊,他說,儂一定去看他那些無與倫比的光線,倫勃朗光線,真正的藝術家啊。就是畫不出,儂也總可以去向往的。人其實就是在活那一點向往。
饑餓,看似輕描淡寫,卻道出了生命最為迫切的本真狀態,它比饑渴更加致命。實際上,《松林夜宴圖》背后隱藏的就是饑餓狀態下的人性扭曲和灰暗世界。這在孫頻之前的小說中,并不多見。也因此,“畫里彌漫著一種奇怪的不安氣息,很緊張,近似于恐懼”,才顯得合乎邏輯。而那一點向往,看似無足輕重,卻是《松林夜宴圖》所象征的美和徒勞,也正因為有了這點向往,人生才“并非一切皆盡”。讀孫頻的《松林夜宴圖》,無意間想起了古代的一句詩:“黃鸝知飲愜,枝上送佳音。”而主人公李佳音之名,想必也暗含著作者小說敘事上的一點隱秘。一定意義上說,孫頻的小說沒有那么的讓人絕望了。孫頻在關于《松林夜宴圖》的創作談中說:“就在那些時刻(到人大藝術系旁聽西方美術史,作者注),你會覺得,欲望與名利真的沒有那么重要,起碼它們不是人生里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它們也不足以支撐起一個人的骨架與魂魄。但是,生而為人,我們都軟弱、自私、貪婪、痛苦、需要被認可需要被贊美,我們就是這樣一種生物,我們終其一生在與自己的弱點搏斗,終其一生要不停完善和修補自己沖突的、分裂的人格。藝術是什么?藝術就是讓我們活在世上能不那么苦痛的東西吧,哪怕它只是一種幻覺。”有了“松林夜宴圖”,李佳音有了游走世界的勇氣和希冀,有了《松林夜宴圖》,孫頻讓人看到了她小說中所追求的天際的光輝。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一書中曾指出:“關于生活的意義問題,關于從惡與苦難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類的問題在藝術創作中是占優勢的問題。俄羅斯作家沒能停留于文學領域,他們超越了文學界限,他們進行著革新生活的探索。”當代中國作家,需要的也是這樣一種精神高度和思想氣魄。
如果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對于“身體”的呈現和迷戀,應該始于1990年代以來一批年輕女作家的精神探索和藝術嘗試。她們大都以第一人稱來敘述,以自我經驗為標本,來展開內心世界的獨白,來呈現現實的殘酷。她們以自我的經歷,寫出了中國的歷史變遷。她們展現的是個人的命運,同時應和的也是時代的遭際。對于孫頻來說,她所面對的世界和現實,比起上個世紀末來說,更加破碎、更加寂寞、更加不安。孤獨、虛無、蒼涼正在成為一種日常的情緒和感覺,侵襲著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個體的存在,也成為歷史語境下的巨大疑問。由此,孫頻開啟了她在新的時代境遇下關于靈與肉的藝術思考。
肉身無處安放,靈魂如何可能?肉身與靈魂這兩個不同的敘事維度,在孫頻的小說中呈現出一種混雜而莫名的張力。她一方面癡迷于肉身沉淪的蠱惑,一方面又執著于精神突圍的可能。由此,也形成了孫頻小說虛無而幽暗的神秘氣氛,以及滯重而壓抑的審美風格。孫頻的小說,透露著與她這個年齡段所并不完全契合的“兇猛”和“暮氣”,同時也讓我再次確認,一個人的審美趣味和思想深度,和對一個人生理預期的判斷并不是一回事。而這本身也是研究孫頻小說的一個秘密通道。
孫頻在其他兩部中篇小說《萬獸之夜》、《光輝歲月》中,時刻在向我們呈現著這個時代的巨變和精神的淪陷,這是一個物的時代,網友的時代,欲望的時代。歷史的車輪在滾滾向前之時,同樣在生命與人性的增長過程中留下了現代性的明顯烙印,以及一種裂變式的內在創傷。孫頻的小說,一直在試圖醫治這些創傷,以宗教的方式、以沉淪的方式、以遺忘的方式,終至于在《松林夜宴圖》中以死亡的方式。不,她不是以死亡的方式,是以時間的方式,“1995年7月2日深夜”,孫頻以時間的重演,幻滅了歷史的煙云,以生命的死亡,昭示了一種不可實現的可能性。《松林夜宴圖》是歷史之謎,是人性之謎,也是時間之謎。
但毫無疑問,肉身和性愛,始終是孫頻小說人物確認自己存在的方式。“只有在性愛中她(李佳音,作者注)才不再是一個人,在這個過程中她親眼看著自己從我變成了我們,我們被創造出來。她的絕望和孤獨就在那一瞬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稀釋和解救。這種解救是如此的龐大,以至于她無法從中逃脫。”然而,她得救了嗎?她逃脫了嗎?沒有。《松林夜宴圖》中對于肉身的描繪,正在變得虛無和抽象,它不再是確切的感官歡愉和精神墜落,而是以一種虛構的形式上升到接近于哲學的層面,于是,在經歷了肉身的沉淪之后,她“卻越發覺得所有的肉身之下其實都不過是累累白骨”。在這里,肉身正在變成一種幻象,正如時間也在變得虛無縹緲一樣。孫頻從肉身的沉迷,走入了時間的永恒。她似乎意識到了,在這一具具毫無生命力可言的肉身之上,已經很難孕育出健康美好的靈魂之子。唯有時間,歸于永恒。
孫頻的小說,透露著與她這個年齡段所并不完全契合的“兇猛”和“暮氣”
在孫頻作品研討會上,黃德海說,孫頻寫的是非常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小說,不適于用現實作品的框架來評價。孫頻不僅現代,而且浪漫,孫頻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閱讀孫頻,我們會發現,浪漫主義是她作為一個作家的天然的生命底色。但似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孫頻始終沉浸在虛妄的現實之中不能自拔,體現在創作上,就像是被束縛住了手腳,很難破繭而出。正如D.H.勞倫斯所言,“現代小說家被陳腐的‘目的’或自我觀念所約束,從而讓靈感屈就了目的和觀念”。幸運的是,《松林夜宴圖》,讓我們看到了靈感在孫頻寫作過程中的肆意和勃發。說到底,一個小說家的天分決定了她的精神層次和藝術高度。比如下面這段關于白虎山的描寫:
從美院畢業被分回榆中的那個夏天,她又一個人來到白虎山上。西部的落日碩大而金碧輝煌,仿佛是從一種無生命的深淵里長出來的兇猛植物,只是不停分泌出金色的光線,再把這箭簇一樣的光線擲向每一棵樹的生,每一道黃色土地的生,每一道溝壑的生,每一道嶙峋峽谷的生。它像一種無生命的生命,蠻橫有力,強暴萬物。白虎山上的黃土吸飽了這樣濃烈兇悍的陽光,變得通體金黃剔透,天上地下,這么大規模這么浩瀚的金色匯聚在一起,天真單純而掃蕩一切。無論是曾經在那三江匯聚的甬城,還是后來在北京深秋的銀杏林中,她都再沒有見過這么多這么大規模的金黃色。黃沙之下露出的白骨像埋在這土地里的種子,不知道將要長出怎樣奇異的人形植物。她坐在沙丘上,眼看著自己如曠野里的一座佛陀被夕陽鍍上了一層金色。
在孫頻的小說中,我真的很少發現這樣帶著正常體溫的肉身的自然呼吸,它似乎還有一點點的遲滯,但是已經與自然世界的勃勃生氣相互交融和交流,一種接洽中國“抒情傳統”的可能性,也在她綿密而富有彈力的語言節奏中滋生開來。也因為有了這種情感的鋪墊和舒緩,那白骨也不再駭然,而是如種子般有了希望的期冀。當然,這個肉身也是虛妄的,也是想象的,一種自我的沉湎,但它不是沉淪,是世俗的超拔,是浴火的重生,此時此刻,它代表了虛構的“肉身”的一切意義。
最后,再談一點孫頻對于小說形式的領悟。事實上,關于孫頻“同質化”寫作的批評,一方面源于其寫作題材和內容的大致雷同,另一方面則是小說結構和形式上的過于單一。這個問題在孫頻的小說寫作中,的確是存在的。實際上,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絕不多數中國作家,并不十分重視形式的意義,即便是當年風起云涌的先鋒小說,也不過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次突發意外,短短幾年,便曇花一現。但形式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十分重要,形式決定意義。陳曉明說,“作家對他要寫的一部作品,如果沒有獲得形式感,沒有獲得語感和結構,是無法建立其虛構的語言世界的;也就是說,其作品不能給出高于生活的文學形式,那樣的文學作品其實是無效的,其實并不存在——實際沒有自身的存在。在這意義上,文學作品的形式具有決定意義,即它決定了此一作品的文學性形狀,它的完整性和總體性,一句話,它的文學性在世方式”。《松林夜宴圖》顯然是孫頻創作歷程中具有形式意義的里程碑之作,它通過孫頻的藝術之手,獲取了一個獨特的小說形式,特別是以真摯的情感、深度的思想和溫情的意念,讓它獲得了一種形式上的真實生命。而那些外在的形式技巧,最終不過是作品確定和完成自己的一種藝術方式。
孫頻正在通過新的嘗試和探索,尋求小說形式的完美構造,豐富自我寫作的精神內涵,從而寫出生命體驗更加本真的復雜性和可能性。W.H.奧登說,我傾向于相信,當一個人身體和精神處在一種愉悅狀態中,特別想要驅散小心謹慎的心靈探尋,就像驅散病態的煩亂,這個時候才應該讀卡夫卡。當一個人精神低迷,就應該對卡夫卡敬而遠之,除非伴隨著卡夫卡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內省的是一種相同的對美好生活的激情,不然這種內省很容易退化為柔弱無力的對自身罪和孱弱的納喀索斯式迷戀。在此,我并非把孫頻與卡夫卡相提并論,我只是想說,讀孫頻的小說集《松林夜宴圖》,我們也應該懷著一種有別于對孫頻既定認識的精神愉悅和肉身放松,因為,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孫頻。
孫頻正在通過新的嘗試和探索,尋求小說形式的完美構造,豐富自我寫作的精神內涵,從而寫出生命體驗更加本真的復雜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