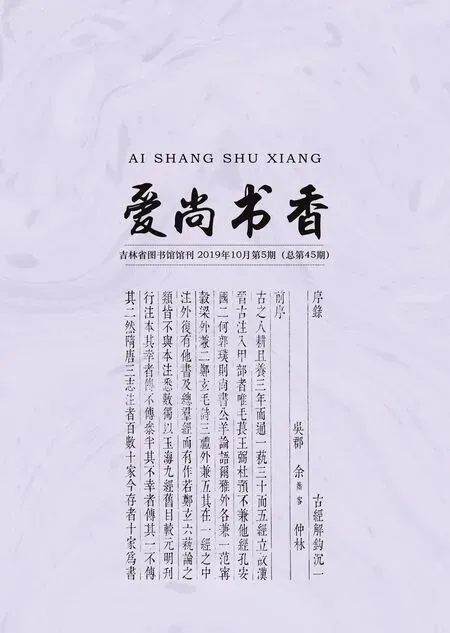愛花愛貓的冰心
李 輝
生活中,鮮艷多彩的花兒,總是裝扮著人們的環境,陶冶人們的情趣。在富有感情的人們那里,花兒,不再是孤立的、冰冷的純植物,而是溫暖的、真誠的愛之體現。
冰心是愛花的。
三十多年前的五月,北京正是繁花似錦的季節。走進冰心老人的靜雅秀美的客廳。八十高齡的冰心老人,矮矮的個頭,臉龐清瘦,幾年前的骨折,使她至今行走不便,更少外出。
她講起話,語調委婉柔和,帶著南國女性特有的溫柔,一如她的小詩。我們交談著,談她的小詩,談她的小說,談她和文壇同代人的友情。她的記憶力那樣好,半個多世紀前與某某作家的第一次見面,她竟然說得那樣清楚。
她笑,開懷的笑,甜蜜的笑,融進窗外射進的溫煦的陽光,也融進了窗臺上、桌子上那一盆盆鮮花散發出的清香。
一會兒,冰心遞過幾份印著鉛字的征訂單,原來是月季花征訂單。一個由待業青年創辦的月季花種植場,熱情洋溢地向人們推薦新鮮月季花。文中還感激地寫到:“冰心先生很關心我們這一事業,她曾囑咐我們一定要育花又育人。”
的確,冰心對此特別熱心。她興致勃勃地說:“你知道這件事嗎?你拿去幾張吧,可以幫助宣傳宣傳。”老人的熱誠,溢于言表。我看她身后那一朵朵紅的花,白的花,那張掛著微笑的慈祥的臉。
冰心愛花,不正是她愛生活的體現嗎?她以一個女性細膩溫柔的愛去寫作,去和讀者交朋友。花,愛,作品,從窗臺的花,手中的紙,臉上的笑,我仿佛看到了無形的,卻又確實存在著的聯系之線。
冰心五四時期的創作,是以愛之主題著稱的。母愛、對自然的愛、對兒童的愛,是她反復謳歌的內容。讀她的小詩,小說,會贊嘆委婉和清麗,飄忽在作品中的愛之氣息,給人溫暖。
花,她在生活中傾心相愛之物,在創作中則成為她的愛之理想的寄托物。最為突出的,無疑是她的成名作——《超人》。
冰心寫小說,是用詩之筆去寫。無論《斯人獨憔悴》,抑或《超人》,她似乎都不曾將人物性格塑造看得那么重,而是著意用清新秀麗的文字,用飽含詩意的情緒,寫出她對人生的憂慮和思考,哲理詩化,正是她在小說中力求表現的。
《超人》中對愛的贊美,是曾貫串在她的詩中的基調。有意思的是,整個作品中愛的體現者,不是別的,是花。主人公何彬這個以冷漠待人生的超人的轉變,是以花為催化劑的。
何彬不相信人們之間是有愛的。他不理睬別人,也自然沒有溫暖。于是,“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里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
然而,當何彬一旦看到祿兒的信,看到祿兒送給他的花,他心中十幾年來用冷漠筑起的壁壘一下倒坍了,如同雪人在陽光下消融。冰心是這樣寫的:
祿兒趁他閉眼睛躺著時,送進一籃金黃色的花,并寫了一封信。信上說: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著花。——這里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
信中講了許多孩子心中的話,孩子把花同母親對自己的愛聯在一起。作品的精彩處是何彬信念發生變化,感情劇烈起伏的時刻,這里花兒向何彬展開了“強攻”。“何彬看完了,捧著花兒,回到床前,什么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他哭了,是悔恨舊時的冷漠?是感激孩子的天真和純潔的愛?是驚詫于花兒的魅力?他變化了,提著祿兒送給的花籃離開了,開始走向新生活。他給祿兒留下一紙悔恨和重又回到心中的熱情。
他說:“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尼采)……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著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母親,花,愛,三者終于在“超人”那里化為一體了。何彬答應送給祿兒一籃花兒,那是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系在弦月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里的一籃花。
自然天真的祿兒,還難以理解何彬的比擬,他只能簡單地從字面上看,他奇怪為什么只見信,不見花籃。只好仰著黑胖胖的臉,呆呆地望著天上。從有形的具體的花,到無形的抽象的花,其實意味著從個別的愛擴充到廣泛的愛。
冰心用美麗的語言描繪出無形的花籃,反映出她的藝術構思,這無形的花籃,在冰心來說,就是愛,而這愛一般人是難以領會深刻的。
灑進窗戶的陽光,忽明忽暗,那是一朵朵云彩飄過。桌面上花影漸漸拉長,那是太陽在緩緩移動。收好冰心遞過的月季花征訂單,我順便請她為《北京晚報》寫篇文章,她應允了。
“寫什么呢?”她想了想,又說:“我覺得醫院的病房里應該有花瓶。人住在醫院里,重要的是精神愉快。你看我們老人,看看花比什么都舒服。葉圣陶上次住院,我去看他,帶了一把花,可就找不到地方放。”“那您就寫這個內容吧。”“好!”
沒幾天,一篇文章寄來了,題為《花瓶》。冰心在文章中建議病房里應該有花瓶,看望病友最需要的是花朵。“看望你的朋友去了,他們留下的花朵,放在床頭,它的光鮮和清香,總會使你想起你和你的朋友之間,或其他的美好往事。”一篇短短的不到千字的文章,字里行間,仍跳動著當年寫《超人》時的年輕的心!
冰心生活中愛花,是她的性情意趣所在。人們常評論冰心的風格屬于陰柔之美,從她對花的偏愛上,不是也可以看到她的個性的特點,看到她的創作風格的內涵嗎?作家的個性影響創作,人們說過多少次,要是能深入細致地觀察一下作家的那些生活興趣細節,大概還是會大有裨益的。
冰心年輕時,在作品中贊頌母愛,在生活中,幾十年從未減少對花的喜愛。當她住在病房里,寂寞,悵惆縈繞于心時,友人送的花會帶著友情溫暖她的心。
當她看望朋友時,如果帶上一束花,便寄托了她的親切的慰問。花,一直是她聯接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媒介,無怪乎到了晚年,還那么熱心地扶植待業青年的月季花種植場。
我看到她那顆充滿母愛的心,仍然那么年輕,活潑,她盼望著花兒如她所描述的那樣,帶著愛,出現在每個家庭的窗臺、桌面,出現在每個老人的床前。其實,不僅僅是花,許多能體現柔情的小物件,冰心都是偏愛的。早在二十年代的《給小讀者》中,她就這樣對孩子們說:
“小朋友,我們所能做到的:一朵鮮花,一張畫片,一瞥溫和的慰語,一句殷勤的訪問,甚至于一瞥哀憐的眼光。在我們是不覺得用了多少心,而在單調的枯苦的生活,度日如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賜。”
何止病者,在冰心的感情世界里,溫和地待人是持久而普遍的。她以溫柔和細膩去感受自然,去感受生活,去擷取生活的浪花,然后再將之用委婉清秀的文字,藝術地再現在作品之中。
她不注重冷靜的細致刻劃,卻擅長縷縷情思的表達,特別是母愛的表現,正是這些特點構成了她的創作風格的陰柔之美。花,我們說不僅僅是了解冰心生活情趣的一把鑰匙,也是了解她的藝術風格的一把鑰匙。或許,這是武斷的結論。
事情巧得很,距冰心寫《花瓶》之后,劉白羽先生也寄來一篇散文《春的使者》,文章也是寫花的——他寫的是送花人。
元旦那天,兩位青年人給劉白羽送花來了,他們就是冰心所支持的那個青年月季花種植場的送花人。原來劉白羽從報上得知,冰心是這個月季花種植場的第一個訂戶,便立刻給冰心打電話,請她幫助自己也訂一份。花送來了。
每周兩次給劉白羽送來鮮花。看著紫的、紅的、白的、嫩黃色的鮮花,劉白羽陶醉了,他感慨:如果生活中沒有鮮花,那將是何等的荒涼和寂寞!
冰心愛花,寫花,謳歌花,她的作品就是一朵又一朵的花,給人以溫暖的安慰,親切的愛!
生活中的冰心,不也是同樣給人帶來愛嗎?
想到請冰心題跋,是在1987年。十月,北京舉辦《巴金文學創作生涯六十年展覽》,請柬題簽由冰心題寫。展覽過后,我去看她,特意帶去請柬請她題跋。
她在內頁上寫道:“說真話,干實事,做一個真誠的人。冰心,一九八七,十一,十六。”
半年后,我去上海看望巴金,請他也在這份請柬上題跋。巴金在請柬封面上寫道:“我不是一個藝術家。我寫,只是因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燒,不寫我就無法得到安寧。巴金,八八年六月十三日。”時隔多年, 兩位老人的題跋,多了記憶溫暖,多了思想的厚重與豐富。
每次去看望冰心,她都會簽名送上新書,但不愛題跋。只有一次例外。1988年6月,她送我一本新出的《關于男人》,是剛拿到的樣書,簽名之后,她順手補上:“這是現在我手里僅有的一本。”還開玩笑地說:“來得早,不如來得巧。”這一年,冰心米壽。
冰心的心中一直擁有大愛!1988年,在“冰心文學創作生涯七十年展覽”的開幕式上,蕭乾發表感言:“可以向冰心大姐學習的很多很多,但我認為最應學習的是她那植根于愛的恨。那些滿足于現狀、維護現狀、利用現狀自己發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對現狀有所指摘。其實,這樣的人心里所愛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權勢和既得利益,因而對生活中不合理的現象那么處之泰然,那么熟視無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愛。”
的確,冰心在精神上與巴金是相知相通的。每次去看冰心,她都會提到巴金。有一次,她拿出一個藍色的盒子讓我看,說它專門用來放巴金的信。
她和巴金的這種誠摯友誼,不只是有著幾十年的交往,如何真誠做人方面有著同樣追求。我想,兩個人精神上從來沒有孤獨過。
冰心是以歷史的反思態度,表現出一個智者的透徹與從容。
九十年代初我請冰心談巴金。她談得非常好。最后一句她說:“世界上的問題并不復雜,心里簡單就行了。”心里簡單,多好!
冰心在北京醫院住院期間,我去探望她。她說:“你來晚了,我的遺產都分完了。”我聽了,哈哈大笑!
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九十九歲,也是高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