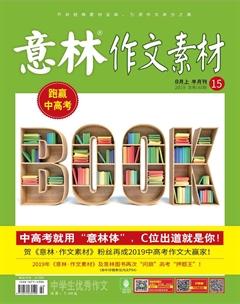酒招非酒
余秋雨
經常有年輕的朋友來詢問文學之道,我總是告訴他們世上并沒有共通的文學之道。但看了他們的作品只想作一個最簡單的提醒:酒招非酒。
他們往往還沒有開始釀酒,就開始涂抹花花綠綠的酒招。
酒招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醒目景象。行走在漫漫長途間,忽然看到樹叢村落間有一面小小的旗幡飄出,表示這兒有酒肆等著你,可以坐下來慢慢喝上幾盅。這對疲乏的旅行者來說無異于荒漠甘泉,一見就興奮異常,立即加快了腳步向那里走去。
酒招之下必須有酒肆。如果酒肆還沒有開張或已經歇業,旅行者一怒會把酒招扯下來,以免后來者上當。我把這個比喻移回到文學上。
這是他們送來的一篇小說的開頭:
一棵老樹抖盡了樹葉,像是已經枯萎,但寒鵲知道這仍然是明年棲腳的地方。農村女性堅韌地支撐住了一個個家庭,讓子孫后代都不忍離鄉外出。
把作品的主旨一下子端了出來,卻忘了多數陌生讀者的閱讀心理。大家都不愿意與路邊一個開口就講大道理的人交往,因此大多會轉頭而去不再成為你的讀者。
如果是這樣的開頭,效果就不一樣了:
她好像是說出去走走。但是等到年菜擺滿一桌,全家已經坐定,八十五歲的老祖母還沒有回來。
一看就知道從這里釀酒開始了。“酒招”上的理念,可以在這種質樸敘事的過程中慢慢滲透。
另一篇小說的開頭是:
海睡了,浪困了,一場人類與大海的搏斗明天就要慘烈地展開,慘烈到天地驚悚鬼哭狼嚎。
我看上了開頭的六個字,因此建議改成:
海睡了,浪困了,李家大叔卻笑了。他從床上起身,到海邊嗅了嗅明天的氣息。
把搏斗的慘烈性提前預告,這就成了“酒招”。該怎么寫這樣的搏斗,請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那個文本因最質樸的敘事方式而驚心動魄。
一篇散文是這樣開頭的:
《周易》有云:渙其群元吉。此為本卦爻辭,渙坎下巽上即風行水上。此間哲理千古皆通讓人醒悟。
這個“酒招”顯然是過于賣弄古風的玄秘了,只讓人覺得藏有遠年陳酒,卻故意不肯說明白,那又怎么會“千古皆通讓人醒悟”呢?
如果讓我這個熟悉《周易》的人來寫,就一定要讓廣大讀者都能懂得:
《周易》里說:“渙其群元吉。”意思是:渙解小團體是一件好事。不僅對社會好,而且也對自己好,好上加好,所以稱得上“元吉”。
另一篇散文是寫自己告別托爾斯泰式的蒼老小說后所接更的現代文學,開頭是這樣寫的:
我平生最喜愛的小說是愛爾蘭作家弗蘭·奧布萊恩的《雙鳥戲水》。作品的敘述者是個學生,他在寫一部關于特萊利斯的作品,而這個特萊利斯則正在寫另一個人,而另一個人又在反寫他。這個渦旋構成了現代派文學的大解放。
這一段文字其實寫得不錯。但是對廣大中國讀者來說,還要以引路的方式說明這種小說結構的文學價值。因此我的寫法會是這樣:
愛爾蘭現代小說《雙鳥戲水》采用了一個奇特的結構,作品里的四個人都在寫書,都是輪盤式的互相揭發、互相報復的書。這些書一段段地交纏在一起,讓讀者明白人類寫書是怎么回事。而且又交纏進了神話,原來老祖先也是如此。
這里出現了散文和學術論文的差別。散文即便是在講述最深奧的事,也要盡量為讀者排除障礙,產生感性效果。如果借用酒的比喻,那就是一定要讓讀者聞到酒香淺嘗口。在散文寫作中,過于艱澀那就不是酒,而是“只能入目而不能入口”的“酒招”。
沒有感性必遭拒絕而且又必趨雷同。
記得我在哪篇文章中提到,有一次參加一所名校的校慶,臺上出現很多官員,奇怪的是有四個官員講話的開頭居然一模一樣:“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估計是秘書們懶惰照抄了通行文本。但在第一個官員講話之后,后面三個官員為什么不避開重復呢?答案是:避開了重復他們不知道講什么好了。
明明是很不一樣的生命活體,避開了重復話語就不知道說什么了,這正證明他們關閉了自己的感性系統,認為那是拿不出來的東西。其實感性系統恰恰是人類最精彩的部位,關閉了感性系統,也就關閉了文學系統和美學系統,再加添多少“金秋”“桂子”都于事無補。一個關閉了感性系統的人總是顯得又木訥又笨拙,缺少靈性與感情。這樣的人做什么都不會出色,更萬萬不可觸及文學和藝術。
這又回到了本題:所有的酒招總是重復的,只有酒招而沒有酒總是讓人氣憤的。
好,至此已經可以做一個歸納了。
文學之道的入口處有兩級臺階,它們是:
一、質樸敘事;
二、感性描述。
質樸敘事對小說更重要,對散文也需要。感性描述則是小說、散文都不可缺少的。
現在不少文學愛好者常犯的錯誤就是太迷醉說理和抒情。在這一點上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常常糊涂,是因為他們受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太深影響。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那些作品有什么共同的缺點和弊病呢?那就是當時的作家都是文質彬彬的書生,又都是疾惡如仇的失意者,都不擅長天馬行空地編故事,都不善于繪聲繪色地講故事。結果從總體看確實也沒有留下幾個精彩的故事。當代影、視、劇的從業者很想從現代文學中改編一些作品,但由于找不到具有足夠張力的故事,每每半途而返。
由于嚴重缺少編故事的能力,中國現代作家們就只能把文學的地盤讓給說理和抒情。因此多數作品都是情緒性的社會揭露和思想批判,美學成色都不太高,很難與古典小說和國際名著相提并論。
我在上海戲劇學院主持“編劇”課程的時候,首先要全體學生熟讀世界各國小說中最精彩的五十個故事,然后十人組進入課程。每個學生每次都要用五分鐘時間講一個即興編出來的故事,由九個同學進行評判。評判時禁用理論概念,只從感受上來評判好聽不好聽、動人不動人、新穎不新穎,而且要說明原因何在該怎么改。修改之后再講再評。每個學生聽了別人的那么多故事、那么多評判,也就明白了自己的故事存在的問題。這樣一輪輪下來大家講故事的能力快速提升,當然也自然成了合格的編劇人才。
上文在舉例時提到愛爾蘭的現代派小說《雙鳥戲水》就是在我的編劇課里令同學們深深驚嘆的作品。它給質樸敘事一個有趣的輪轉結構,里邊并沒有說理和抒情的地位,卻能讓人卷入一種浩大的冥思。在這種作品中整個世界都酒意爛漫了。
上好的文學作品數不勝數,年輕的愛好者們只要入了門,就百無禁忌,可以按照自己的選擇自由馳騁。
(摘自《雨夜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