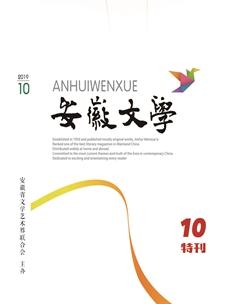六尺巷
程為本
六尺巷
六尺巷里沒有風景,只有思想。
所以當你走進了六尺巷,你便開始思考。思考它的淵源、文化和那個時代的背景,思考那封家書的格局、立場和態度,當然,還有文學色彩。文學色彩與思想同時閃光,讓那封家書流芳百世。直到今天,家書中最精彩的部分仍然光榮地影現在這里的照片墻上。
墻外是挺拔的香樟樹和桂花樹,它們都是常綠品種,枝繁葉茂,覆蔭如蓋,讓人看不見蒼穹。不時有長青藤從墻外爬過來,讓巷內充滿生機。巷的東西兩頭是“懿德流芳”和“謙恭禮讓”之類的牌坊和石刻,還有休閑廣場、詩畫照壁、假山奇石等,讓人聯想到官宦之家的氣派和書香門第的高雅。路面上偶爾有從枝葉間灑下的陽光,斑斑駁駁,好像在說:“世上的巷道多得如同恒河沙數,唯有這兒可圈可點。”
這條建于康熙年間的六尺巷就是康雍乾盛世的一個縮影,也是傳統文化在此處的一個備份。這個風景里的故事數不勝數,首先讓我們走近張英。
張英來到大清王朝的時候,已滿七歲,還未懂事的年齡。他從哪里來?他從衰落的明末而來。他在順治年間讀書長大,到康熙二年(1663)時中了舉人,過了4年,中了進士。官做得夠大了,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值南書房,進入皇權中心。雖仕途中也有過耽誤,但影響不大。康熙是一代明君,他也是一代名臣。他見證了明朝滅亡的悲哀,享受著康熙盛世的榮耀,他懂得仕途的不易,也就更加“勤勉有加”,他不僅入值南書房,還常扈從在康熙左右。他是百姓眼中的大官,更是康熙心中的“要員”,這樣一位“大官要員”的家就在桐城縣。
我們不能還原歷史,但我們可以拾起一些生活片段。張英這個官宦之家也是要過日子的,另一個富商之家吳家也是要過日子的,尋常日子里發生“撞膀子”的事情總會有的——他們在修墻的時候就“撞了膀子”。據說是吳家人想在與張家的分界線上修一道墻,這很正常,張家人也想修一道墻。可吳家人過了界,占了張家的地,張家人自然不同意,矛盾就這樣產生了,直至打起了官司。地方官不敢輕意決斷,只好拖,官司久拖不決。這讓張家人很生氣,于是寫信給朝廷里的張英。
張英接到家書以后,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略施小壓,問題就解決了。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修書到家,對著家人這樣說:“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張英說“讓”,張家人自然就讓了,一讓就讓出了三尺。這一讓,讓吳家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于是吳家人也退讓了三尺。各讓三尺,六尺巷就這樣誕生了。
張英這一讓,讓出了一個令他在南書房、文華殿都沒有過的大手筆。他寫過數不清的奏折、典章、圣旨,唯有這封家書,才是他的絕佳之作,讓出了他后來衣錦還鄉的榮光風采。他在60多歲時,便以“老乞歸”的名義,回到了生于斯長于斯的皖西南桐城縣。這個時候“桐城派”還在孕育之中。
張英回到了六尺巷,在這條巷道里來回走著,欣賞、撫摸、感嘆這條巷道為他留下的一道道輝煌印記。他在這條巷道里怡養天年、教育子孫,在72歲時仙逝,享譽“文端”謚號,長眠龍眠山下。龍眠山與六尺巷組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長廊。
風景還在繼續,讓我們再說另一個人。這個人也走過了三個時代,從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成為大清內閣的“首輔宰相”,配享太廟,這個人名叫張廷玉。他正是張英的次子,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入值南書房,先后任戶部、刑部、吏部尚書。同樣是晚年致仕歸家,病逝家中,葬于龍眠山,謚號“文和”,他是清朝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臣。
于是后人眾口交譽,給予了六尺巷這處人家一個常人難以企及的光環——“合家頂戴,滿門朱紫”。當然,這還包括了張英的孫子、張廷玉的兒子張若靄。張若靄同樣中了進士,只是來不及有更多的建樹便英年早逝。
張廷玉在其父仙逝20多年后曾回家祭父撰詩:“昨向妝樓檢遺墨,班昭猶有未殘篇。”
不言而喻,這是在向我們昭示著,其父所寫的家書和這條六尺巷猶如班固、班昭的《漢書》一樣將永載史冊!
于是,無數后來者走進了這幅歷史的畫卷。
現在,回首這條六尺巷,雖然只是一個復制品,但依然擠滿了游客和瞻仰者。他們覺得六尺巷之寬,不只是寬在六尺上,更是寬在人們的心靈上。也不局限于張家與吳家的個人道德層面,更是一個時代處理官民關系的范本。
孔城老街
離開六尺巷,直奔孔城而去。
孔城于我,就是一個“局”。30多年前,我被困在那里,直到今天,才破“局”而歸。
孔城那條長達2公里的老街,據稱是安徽省最長的老街。印象里它有些破舊,先富起來的人家又蓋了新房,使老街有點不倫不類。后來看了朋友筆下的《老街》,讓我有了另一番情懷。
1984年的一場大雪覆蓋在文都桐城的大地上,安慶行署的伏爾加小汽車在覆滿積雪的路面上艱難爬行。年前的送溫暖活動把我帶進了孔城,來到孔城區公所的所在地——老街。這是一片普通的街面,看不出城的樣子來。
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孔城大概與孔姓有關,甚至與孔子有關,認為這里有不少孔姓人家是孔氏的名門望族。然而,找不出這樣的答案來,甚至連一戶姓孔的人家都沒有。送溫暖是工作任務,忙碌得很,我沒有時間擅自離隊,去探究孔城的源頭。孔城就這樣與我匆匆晤面,留下了一個謎。有幸的是我們得以在桐城八景之一的“孔城暮雪”里向孔城揮手道別。
人在旅途,這樣的勝景可遇而不可求啊!
一般來說,每個地方的名字都有它的起源。但隨著歷史的變遷,滄海桑田,名字便難以得到正確的詮釋。一種說法是,孔城由“空城”演繹而出,諸葛亮用“空城計”嚇退了司馬懿,留下傳奇。可能是這里的人們艷羨這種傳奇,也曾演繹過類似的故事。還有一種說法是,這里習慣將河渠的出口稱之為“孔”。孔城有大量的水道南通長江,東連菜子湖,“孔”確實是夠多的。不管怎樣,孔城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逐漸明亮起來。
孔城,現為一個鎮的建制,在桐城市的東部。與廬江、樅陽縣接壤,是桐城市的第一人口大鎮。宋代有志載:“淮南路舒州九鎮,孔城即九鎮之一……”這么說來,它始于宋代,有近千年的歷史了,是安徽的千年古鎮。而老街上的人說:“老街有1800年的歷史了。”這就更早,1800年前是三國時期。無論始于三國還是始于宋,它都承載著歷史的蒼茫與厚重,一路走來,確實老了。
老了就稱為老街,這很拙樸,又很高雅。這讓我想起了別的古老城市,如南京的新街口。南京,六朝古都,卻冒出一個新街口,確有新鮮味,讓古老在新奇中“出彩”了。
老街,確實很老,1800年前,三國的煙云早已“折戟沉沙”。即使拉近到宋元豐年間,還是很老。所以,說它千年古鎮,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我想再拉近一點,1840年,當鴉片戰爭的煙火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候,這里誕生了桐鄉書院。桐鄉書院,已經跨越了一個半世紀,夠老的。與書院相對而望的太平天國白果廳,與此同期的李鴻章錢莊,當然也就同樣老了。李鴻章,晚清重臣,合肥人,卻將錢莊開在了孔城老街,是不是他看好的正是這個“老”呢?
還有倪知府大宅,建于光緒年間,系江西撫州知府倪延慶老先生告老還鄉定居所建,是孔城老街最大的官宦府邸。大宅古色古香,與街面上的石板路和青磚黛瓦粉墻互為印證,述說著這條老街的滄桑。
知府大宅算是老街上最年輕的建筑了,但也有百年歷史。我走進大宅的客廳,坐在知府的太師椅上,似乎聽到了書院那邊朝陽樓上的書聲。那書聲穿越古今,送來傳承光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朗朗書聲,這書聲讓這條老街、這方古鎮陡然間年輕起來。
你看,在大廳的主立柱上,分明寫著“期寸心無愧不鄙斯民,與百姓有緣才來此地”。這是怎樣的情結,又是怎樣的胸懷啊!
坐在倪知府的太師椅上,我們想起了另一個應該坐在太師椅上的人,他叫戴名世。戴名世是與張英差不多同時代人,可他沒有張英那么幸運,雖然文章蓋世,可直到56歲才考取進士第二。而在四年之后,又由于《南山集》案而走向了生命的盡頭。這讓我們想起了方苞,方苞也因《南山集》案而差點丟了性命。方苞、劉大櫆、姚鼐成為散文“桐城派”的三大鼻祖,以“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和起承轉合的章法結構讓文風大振,積極地影響了康乾以降二百多年的清朝文壇。從此,桐城有了“文都”之稱。
一個縣,在并不多長的歷史里,如何就誕生了那么多的文壇大家,甚至形成了桐城流派?這是有歷史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