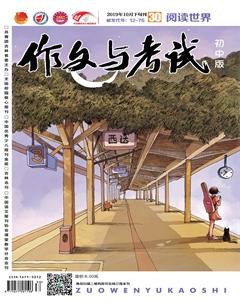月亮堂堂
2019-10-18 02:12:11許冬林
作文與考試·初中版
2019年30期
許冬林
月到中秋,分外的清白而圓潤,掛在藍汪汪的遠天上,像豆芽缸里剛撈上來一樣,又白又胖。
記憶中,每每這時候,我奶奶站在門旁,對著浩瀚的天空里那一輪皓月,很抒情地嘆道:“月亮——堂堂哦!”于是掇條長凳放在門前的場地上,她坐在一片奶白色的月光里,周身暈染一層絨絨的白光,像蓮花上的觀音。
我喜歡我奶奶那“月亮堂堂”四個字,多年后再在嘴邊咀嚼,只覺得有一片浩茫而澄澈的月光,那樣廣大無邊地覆下來,人世乾坤,堂堂中正。就連月色里夜游的飛蛾與螞蟻,都能在這蛋青樣的月夜里,覺出塵世的清明與平和,還有悄悄的說不出的歡欣與滿足。
月亮堂堂的夜晚,奶奶喜歡坐在門前的石階上剝豆。豆是種在田埂上的豆,或者無人耕種的河畈上,個個豆莢長得肚大腰圓,得意滿滿。黃昏時,奶奶從河畈或田埂上背一大捆豆稈回家,堆在場地上或者屋檐下。晚飯吃過,吹了油燈,只見月光無限慷慨地灑下來,粉粉地鋪在門前的石階上。奶奶坐在那月色里剝起豆來,安靜無聲的。只是過那么一會兒,會扔了一棵已剝完的豆稈,再抽出另一棵,如此往返,不緩不急。沒有什么會驚擾得她停下,也沒有什么會催著她趕緊,剝豆的奶奶和月光一起構成一幅人間的畫兒,安詳而明朗——是月光,把一個鄉間老嫗最普通的勞動,注解成人間美麗的圖畫。
有一年仲秋時節的夜里,是下半夜,口渴了,爬起來到廚房找水喝。趿著一雙涼軟的布鞋,朦朦朧朧到得廚房,立時驚呆了——好一片月色!……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