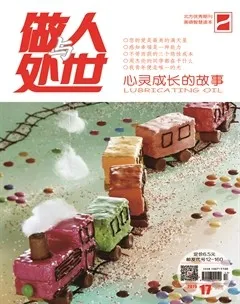巴金印象
王一秀

對巴金最初的印象,是我8歲時在縣醫院留下的。1963年時的縣醫院真有文化氛圍,《上海文學》赫然與醫學大部頭著作擺放在閱覽架上。父親上臺去做手術,我讀《上海文學》,看到了巴金的報告文學《手》,寫上海陳中偉大夫,為一個青年工人斷手再植,再植手術寫得動人心魄,緊張得讓人手心出汗。
后來看電影《英雄兒女》,是由巴金的小說改編的。“你有一個老工人的爸爸,還有一個老革命的爸爸。”老工人爸爸好像叫王復標。慢慢地,從五六年級大孩子嘴里知道了巴金并不姓巴。
改革開放以后,我畢業工作,當了編輯、記者。矯健說起了兒時夜晚看到的巴金。1966年,停課鬧革命,反正,小學生矯健的學校不上課了,精瘦又機靈的矯健,在文聯作協出版社的宿舍區逛悠。他家的宿舍西南隅,是巴金的宿舍小樓。一天,天快黑的時候,他爬上了墻外的法國梧桐樹,驀然,他看到了房間里的巴金。巴金是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后,先京后杭,剛剛歸來,似又得到了什么消息,燠熱的8月,昏黃的燈光下,已過花甲之年的巴金,在房間里踱步,沉思著。一會兒,又坐下來,無聲地望著窗外的天空。7點多了,天還沒有完全黑。一會兒,他又站起來,來回踱步。在少年矯健的視角里,這時的情景是令人奇怪的。巴金爺爺怎么了?燈光下,在少年的惶惑里,一直到很晚。巴金并不知道,夏夜里,窗外還有一雙少年純真無邪的眼睛在關注著他。第二天,矯健已看不到老人的身影,后來才得知,巴金被隔離關進了牛棚。
鄧小平力主改革開放,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單說買書一項,我已是想買就買,完全不似上一個年代的貧窮,需精打細算。《隨想錄》五卷,《家》《春》《秋》3個版本,入手珍惜,閱讀時的心情那個激動啊!于是,我決定采訪巴金,請他談談對新一代人成長的希望,也談談他自己的少年時代。晤見巴老,也解我自少年時代就滋生的一直的景仰。
1985年,揚州三月蠶花放,正是河豚初上時。我不能貿然打擾,先請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劉老師介紹,劉大姐聯系后,說:“巴金先生住華山醫院已近兩個月,為靜養,組織上安排不能打擾探視。”當時,我正訪蘇步青先生。我想,原來巴老病了,怪不得給他和李小林老師的信未復。可內心,自南京至揚州又至上海的勃勃三月早春心情,總是感到了一些不足和遺憾。
1987年8月,南京上海多年不遇的酷暑,我復赴滬,得知巴金仍住院,在華山醫院北樓。酷暑難耐,我趕早上趁清涼去外灘南京路市文衛辦一趟,復訪《文匯》月刊,回住處又熱又燥,沖涼后迷蒙中沉沉睡去。“王先生,電話。”是服務員喊,我接了,竟是巴老府上,說:“現在正好合適,你過來吧。”
乘車到武康路113號巴金先生家。一路燠熱,但大門外,似已感覺到了院內綠樹的清涼。開門人自稱是巴老胞妹九姑媽,瘦弱的九姑媽朗朗地回頭喊:“四哥,山東的客人到了。”一樓會客廳向陽臺門旁一張小桌子,1尺來寬,有3尺長,擺放著剛寫完的文稿和幾本書。九姑媽說:“剛上了三樓,你可以上去。”走道、樓梯拐角、3樓,全是書。穿一件已不新的藍色卡嘰布中山裝的巴老,正在找書,轉過頭,慈祥地笑著說:“你過來啦。”我恭敬地問候一聲:“巴老。”鞠了一個躬。呵!自小敬仰的巴金,鏡片后的目光含著笑意,謙和、文雅、彬彬有禮。“你坐。”親切、隨和、友善的巴老,看著我,像看著一個剛剛放學回來的孩子。我說了約稿想法,并想讓巴老寫幾個字。巴老語速有些慢,說:“寫了,給你寄去吧,我帕金森氏癥,好幾年了,手,抖。”我連連點頭,說:“好的。”內心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
回魯后,不久,看到了巴老為無錫小朋友寫的回信。11月25日,巴老生日前夕,我給巴老發去了賀卡。
如今,捧讀《隨想錄》,就想起兩次赴滬訪巴老的情景,巴老的為人處世永遠是我心中的豐碑。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