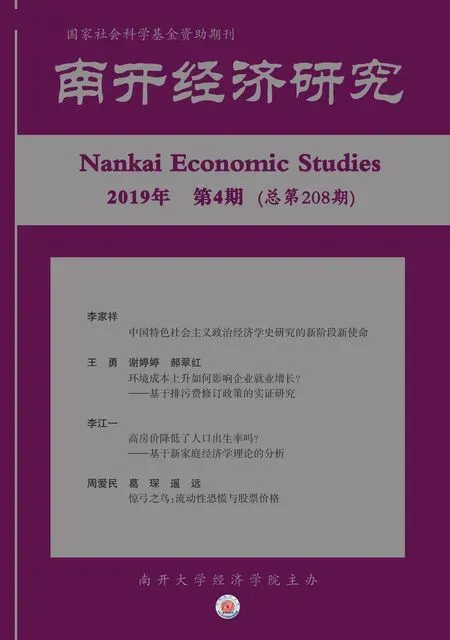環境規制對工業企業選址的影響
——基于微觀已有企業和新建企業數據的比較分析
薄文廣 崔博博 陳璐琳
一、引 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迅速,在經濟總量上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與此同時,經濟迅猛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引起全社會重視,當前的“霧霾”“滲坑”“土壤污染”種種環境事件①相關新聞報道:“霧霾又襲京津冀 大氣治理仍任重道遠”(http://www.yicai.com/news/5287883.html);“河北17萬平米污水滲坑:一個廢水坑有21個足球場大”(http://yuanchuang.caiting.com.cn/2017/0419/4261874.shtml);“不能承受‘重’污,土壤面臨防治雙重難題”(http://news.ifeng.com/a/20151030/46048072_0.shtml)。表明中國環境問題已經比較嚴重。亞洲開發銀行(2011)的研究也指出,中國最大的500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空氣質量標準,世界上空氣污染最嚴重的10個大城市中,中國占了7個①具體參見http://dz.ttckb.cn/www/pages/webpage2009/html/2013-01/15/content_61936.htm?div=-1。。面對這些環境污染,我國也采取了積極的應對舉措,僅在國家環保相關機構設置上,就相繼經歷了1972年的官廳水系水源保護領導小組、1974年的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1982年的隸屬于當時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的環境保護局、1988年成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的國家環境保護局(副部級)、1998年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正部級)、2008年成立的環境保護部以及2018年組建的生態環境部等。
隨著環境保護機構設立的不斷完善,我國環境規制力度也呈現日益強化趨勢。2017年,為了有效應對北方特別是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地區的霧霾天氣,當時的環境保護部實施了大氣環境區域聯防聯治,確定了“2+26”城市的京津冀大氣污染運輸通道,并對此區域內的醫藥、農藥、包裝印刷、工業涂裝等行業在全國率先開展排污許可證核發工作,在水泥、鑄造等行業繼續全面實施錯峰生產。
此外,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日益深入,特別是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的《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更是明確指出,生態環境出問題將首先問責省市縣委一把手。各個地區的地方領導更需要平衡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這兩個目標,環境規制對于企業特別是污染程度較高的制造業的影響問題也成了學者關注熱點。環境因素在企業家選址建廠決策或產業轉移過程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那么環境規制是否會產生通常的“污染避難所效應”?各地區已建成的企業和新建企業是否會從環境規制強的地區轉移到環境規制弱的地區?環境規制是否會對不同類型企業的選址產生差異性影響?對上述問題的探討不但有利于深入了解我國環境規制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而且也有助于我國實行精準環境規制政策,從而更好協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前言,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介紹計量模型設定及相關數據說明,第四部分定量分析了環境規制對新建企業和已有企業選址的影響,第五部分根據一些標準對相關樣本數據進行了細分,以深入分析環境規制水平對不同區域、不同污染程度以及不同規模的企業選址產生的影響及其可能存在的差異性,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結論和簡單的政策含義。
二、文獻綜述
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一直以來就存在著較大爭議。早期,對于環境規制與企業選址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學者們通常得出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沒有影響的結果,如Bartik(1988),Jaffe、Peterson、Portney和Stavins(1995),Levinson(1996)以及Thomas和Ong(2004)等,他們最常見的解釋是環境合規成本相對于其他成本太小,因而對企業選址決策影響不大。
隨后學者們逐漸將研究對象轉移到污染較高的行業,得出了與之前不同的結論。Condliffe和Morgan(2009)調查了1977年清潔空氣法修正案(CAAA)對美國縣級污染密集型制造工廠選址決策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嚴格環境監管對企業選址決策的影響因制造業污染強度而有所不同,聯邦環境規制對高污染密集型制造商的影響要大于對中度污染密集型制造商的影響。Mulatu等(2010)采用13個歐洲國家16個制造行業數據,研究了環境規制對制造業選址的影響,結果發現“污染避難所效應”是存在的,而且這種效應的相對強度與行業類型有關。只有在污染程度較高的行業,才會出現環境規制對工業區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的現象。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嚴格的環境規制會對企業特別是優質企業的選址有正向促進而非負向限制作用。Kirkpatrick和Shimamoto(2008)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污染密集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格局,結果顯示,對于樣本中五個污染密集行業中的每一個行業,企業都傾向于在擁有更多而不是更少嚴格環境規制的地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似乎更愿意被那些承諾建立一個透明和穩定的環境監管框架的國家所吸引。Bu和Wagner(2016)分析美國跨國公司進入中國FDI的表現情況,也認為環境問題處理能力更優的公司傾向選擇環境規制較為嚴格的省份,而無力應對污染懲罰的低能力公司則傾向選擇較低環境規制的省份。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對中國省際內部是否存在“污染避難所效應”也進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Lian等(2016)參照經典的產業與省份交互模型和中國制造業數據,得出制造業傾向于從嚴格管制的省份向松散管制的省份轉移以及環保寬松的省份更容易吸引污染企業從而成為污染避難所的結論。Wang等(2015)根據對企業所有權分類,發現環境規制對國有企業選址有積極影響,而對民企選址則有消極影響。對于環境規制越嚴格越吸引國有企業這一現象,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國有企業是政府處理市場失靈問題的工具,所以利潤不是國有企業的唯一目標(Hafsi、Kiggundu和Jorgensen,1987;Bai、Lu和Tao,2006);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財務、稅收、就業、監管和投資審批方面可能享有特殊地位(Liao和Zhang,2014)。周浩和鄭越(2015)發現環境規制對全國范圍內以及東部區域內部的新建企業遷入有顯著抑制作用,但是在中西部地區內部則沒有顯著表現。
綜上所述,國外早期的研究通常沒有對企業污染程度進行分類并以此來討論環境規制的影響效果,且大部分是針對已有企業,而不包括新建企業。實際上,由于已有企業特別是制造業已有企業通常具有較多的沉沒成本以及社會關系網絡,因此相對于新建企業而言,同等條件下,其遷移可能性無疑較低,故而之前的文獻常常得出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無影響的結論。在以中國為對象的實證研究中,一方面,大部分學者使用按省劃分的樣本數據,而非包含更多樣本和實際上更多承擔環境規制制定和實施單元的地級城市的微觀企業數據,從而導致回歸結果可能存在偏誤,穩健性較低。另一方面,即使存在少數實證研究按城市劃分且以新建企業為研究對象,但是這些研究都是討論當年環境規制對當年新建企業選址的影響。事實上,新建企業在進行選址時,通常因為無法預判當年及之后的環境規制如何,而選擇根據前一年的環境規制來進行選址,所以當年的環境規制不是影響新建企業選址的最直接因素,而已有企業由于已經選址在該城市投產,因此其滯后影響也可以忽略不計。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中國288個地級市的新建工業企業和已有工業企業的微觀數據為研究對象,定量分析了環境規制對新建工業企業和已有工業企業的影響。此外,還依據一些標準如不同區域(東部、中部和西部)、不同污染程度(重污染、中污染)和不同生產規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等,進一步深入分析環境規制對這些基于不同原則細分城市制造業選址的影響及可能存在的差異性。
三、計量模型構建與相關說明
(一)計量模型的構建
本文通過構建下述計量模型來定量分析環境規制對已有企業和新建企業選址的影響:

其中,Y是被解釋變量,用新建企業數量或已有企業數量來表征;X是用來衡量環境規制度的核心解釋變量,加入2X是為了驗證環境規制與企業選址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關系;Control是其他控制變量的集合,ε是殘差項。具體展開后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NFij是i城市j年新建企業數量,EFij-1是i城市j-1年已有企業數量,核心解釋變量TPij-1為環境規制,(TPij-1)2是環境規制變量的平方項控制變量,Indusij-1、Roadij-1、GDPij-1、Salaij-1、Eduij-1分別代表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城市GDP值、職工平均工資、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數。
(二)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
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早期主要是通過各地區已有企業數量來衡量,但在環境規制從寬松逐漸轉向嚴格的情形下,已有企業數量由于沉沒成本以及根植的社會網絡效應等難以發生較大變化,從而削弱了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這也是早期研究得出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影響較少的原因之一。從動態視角,則可以使用各城市中微觀企業遷出數量來表征被解釋變量,但是由于企業經營狀況總是在變動中,一些企業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或縮小會進入或退出年銷售額在2000萬元以上(之前入庫標準是500萬元,從2011年起調整為2000萬元以上)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統計門檻,而對于新進入統計門檻的企業,其開業年份也并不一定都是2013年(本文使用的數據年份是2013年),所以會導致2013年統計的企業數量超過2012年統計的企業數量的部分要遠大于這一年新建的企業數量①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統計,北京市在201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為3485個,而在2012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僅為3321個,而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開業年份標準,北京市在2013年新建企業數量僅只有4個。因此,我們無法根據“2013年末已有企業存量-2012年末已有企業存量=2013年新建工業企業數量-2013年遷出工業企業數量”這一等式來計算出2013年北京工業企業的遷出數量。,無法準確得到2013年相關城市的工業企業遷出數量,因此我們也無法使用企業遷出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
根據本文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數據可獲得性,在借鑒周浩和鄭越(2015)的基礎上,本文使用各城市的新建工業企業②使用工業企業的相關數據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是相對于第一產業的農業和第三產業的服務業而言,主要屬于第二產業的工業更容易產生環境污染,因此也更多地成為各級環境部門的規制重點。第二是由于可以從公開渠道獲得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有許多微觀企業數據指標,能夠滿足論文研究的需要,因此同國外諸多文獻一樣,國內有關環境規制的文獻中分析的對象也常常是制造業。數量及各城市的已有工業企業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的表征(分別是log(New firm)、log(Existing firm))。
2.解釋變量
衡量環境規制的指標有很多,通常包括單一指數以及綜合指數等。單一指數主要是指用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達標率、單位產值污染治理設施運行費用、治污投資支出等單一指標來表征環境規制。綜合指數則是使用多重主要污染物或多種表征環境規制的相關變量指標,經過標準化以及相應權重計算后構成的總指標來度量環境規制。
在主要涉及到中國環境規制的相關文獻中,并無公認的統一方法來表征和度量環境規制變量,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288個具體負責環境規制制定和實施單元的地級城市中的相關微觀企業,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并無太多的可以使用綜合指數來計算的環境規制指標,因此本文使用了單一指數來表征各城市的環境規制程度,即采取各城市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不包括工業廢物③由于數據的可得性,《中國城市經濟統計年鑒》中只有各城市的一般工業廢物利用率數據,而沒有相關城市的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數據。另外,與工業廢水及工業廢氣相比,市民對工業固體廢物的“感知度”較低。工業廢水影響水源、河流等,工業廢氣直接影響空氣質量,這兩個因素很容易被市民所感知。工業固體廢物對環境確實產生影響,但是市民對其的“感知度”低,從而給政府的壓力小,故政府對其“重視度”也相應偏低。)總排放量,而不是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量來相對表征環境規制。這是因為普通市民對環境的評判通常是基于所見所感的環境污染物總量而不是單位產值污染物。即使一區域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總量低,但是在產值較大的情況下,該區域范圍內的污染物總量也會較多,其環境狀況相對惡化,該區域的人群對環境狀況容忍度越大(環境狀況越差),間接說明其環境規制越弱①本文沒有采用污染排放量的倒數來表征環境規制,原因在于污染排放總量和環境規制呈現負相關,但并不能嚴格推斷出環境規制可以用污染排放量倒數的數值來表示,環境規制可能是污染排放量平方的倒數或者負數等其他負相關關系,僅僅依據負相關關系而選擇污染排放量的倒數或者其他數學表示方式的數值來作為環境規制度表征值在理論上是不夠嚴謹的,而且在進行后面的回歸分析時也更容易產生偏差。。另外,由于新建企業通常無法預判當年的環境規制強度,因此其根據前一年的環境規制進行選址更加符合理性考慮,所以環境規制以及下述其他控制變量均采用滯后一期。
3.其他控制變量
本文中包含的其他控制變量是企業選址中常見的控制變量。工業基礎:本文借鑒Lian等(2016)采用的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來衡量每個城市的工業基礎。城市基礎設施:徐敏燕和左和平(2013)采用交通網密度表示城市建設程度,Dean等(2009)采用道路和內陸水道的長度表示城市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人均城市道路面積代表城市建設基礎。市場規模:史本葉和王曉娟(2019)、程艷和劉灝(2019)及Kirkpatrick等(2008)對于市場規模的衡量均采用當地的GDP值,本文借鑒上述表征方式來表征市場規模。勞動力用工成本: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成本是影響企業選址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借鑒周浩和鄭越(2015)采用各城市的職工平均工資來代表。勞動力投入質量:Wang等(2015)用大學畢業生的數量作為當地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指標來衡量勞動力投入的質量,但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各地級市市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數說明當地的教育水平,代表勞動力投入質量。
本文的數據主要來自歷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2012年和2013年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城市GDP值、職工平均工資、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數、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等指標來自于歷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此外,通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匹配和篩選得出了2013年各城市新建工業企業數量及工業企業總數量。由于環境規制對新建企業選址的影響存在滯后性,本文研究2012年的各變量對2013年新建企業選址的影響及2013年的各變量對2013年已有企業選址的影響。
四、回歸結果及相關解釋
(一)描述性統計
新建企業和已有企業數量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的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包括新建企業數量的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2 包括已有企業數量的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從表1和表2中可以看出,新建企業數量取對數后的均值為0.949,最大值為2.210,最小值僅為0,已有企業數量取對數后的均值為2.824,最大值為4.003,最小值為1.398,說明不同城市的新建企業數量和已有企業數量差異均巨大,且前者差異程度大于后者。2012年總污染排放量取對數后的均值為4.669,最大值為5.733,最小值為1.857,2013年取對數后的均值為4.596,最大值為5.723,最小值為1.857,說明從全國范圍來看2013年的環境規制相比2012年更加嚴格。此外,各個城市的經濟水平、基礎設施建設和教育等指標差異也較大,而工業基礎和工資水平差異則相對較小。
包括新建和已有企業數量的主要變量之間Pearson相關系數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包括新建企業數量的主要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

表4 包括已有企業數量的主要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
從表3和表4中可以看出,新建企業數量以及已有企業數量和總污染排放量的相關系數均較小,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于控制變量,如工業基礎、道路建設和工資水平(除了與表征市場規模的GDP外),其與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也均較小,且具有顯著性;而對于GDP變量,其與新建企業和已有企業變量、環境規制變量和教育水平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大,一起納入模型中可能存在著多重共線性,因而影響到回歸結果的可信性,因此我們分別對新建企業和已有企業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包括新建企業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檢驗

表6 包括已有企業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檢驗
從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其檢驗值均低于5,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可以納入到回歸模型中進行定量分析。
(二)回歸結果分析
環境規制對新建企業及已有企業選址影響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對于氣液兩相水溶液包裹體,測定冰點溫度Tm(ice)和最終均一溫度Tht;利用經驗公式計算或利用實驗相圖確定流體鹽度;利用溫度—鹽度—密度相圖、經驗公式或直接查表求得NaCl-H2O體系的密度;并使用“FLUIDS 1.”軟件包(Bakker,2003)中的“BULK”程序校驗。等容線的計算通過“ISOC”軟件,使用(Bodnar and Vityk,1994)、(Knight and Bodnar,1989)方法計算獲得,該方法試用于H2O-NaCl體系,溫壓試用范圍為100~800℃和0~600MPa,只使用鹽度和均一溫度Tht(℃)即可計算離散壓力-溫度點,擬合等容線(表3)[15]。
從表7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于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變量log(TP)前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但是在加入其平方項后,變量log(TP)的系數為正,變量2[log(TP)]的系數為負,且兩者均在1%水平上具有顯著性,這說明污染排放量對企業選址影響存在著非線性關系,兩者之間呈現倒U型,即隨著污染排放量越來越小,企業數量先增加,達到轉折點后再逐漸減少,又由于總污染排放量與環境規制度呈負相關關系,因此隨著污染物排放量越來越小(即環境規制越來越嚴格),企業數量也是先增加后再逐漸減少,這說明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影響呈現倒U型,在環境規制達到轉折點之前,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有正向促進作用,在環境規制達到轉折點之后,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有負向抑制作用。對于新建企業而言,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為0.221①假設 log(TP)前的回歸系數為 b,其平方項前的回歸系數為 a,可得出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為 1/log(TP)*,而log(TP)*=-b/2a。根據表7中的模型7.4可知,log(TP)*=4.5,所以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為0.221。。在2012年,我國地級城市中有198個地級市的環境規制程度小于0.221,說明環境規制對新建企業選址有促進作用的城市高達198個。對于已有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為0.240②與上面對于新建企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計算方法類似,可以得到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為0.240。。在2013年,我國地級城市中有241個環境規制程度小于0.240,說明環境規制對已有企業選址有促進作用的城市達241個。

表7 模型計量回歸結果
隨著百姓收入水平提升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之前的“人隨產動”日益轉變為“產隨人走”,且越是高端人才越是對單純工資之外的軟環境愈發看重,而具有嚴格環境規制的地區通常擁有高質量的環境,因此也更易于吸引相關企業和人才的入駐,同時較佳的環境質量也意味著不要求企業投資于改善一般環境基礎設施(Adams,1997;OECD,1997)。對于企業而言,一方面,擁有技術創新競爭優勢的企業往往會更愿意建址在嚴格環境規制的地區,另一方面,遵守環境標準也可能導致技術變革,從而提高企業的競爭力(Porter和Linde,1995),因此提升環境規制開始階段會有利于企業選址。當環境規制越來越嚴格且超過轉折點時,企業符合環境規制所需要付出的合規成本也越來越大,導致成本-收益計算后其預期凈利潤為負,這會限制企業在環境合約成本較高地區的選址,進而對企業選址產生負向抑制作用。
此外,通過比較已有企業和新建企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發現,已有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大于新建企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這說明環境規制對已有企業選址產生正向促進作用的范圍更大,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新建企業而言,已有企業具有大量的固定和沉沒成本,因此其對環境規制的“忍受”程度可以較高,而新建企業則無需支付這些成本,可以完全根據環境規制情況來較自由地決定是否在此選址生產。
對于控制變量,無論是對于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GDP的系數為正,工資水平的系數為負,且均具有顯著性,這說明企業更傾向于在市場規模較大及企業用工成本較低的城市進行選址生產,而表征城市基礎設施以及勞動力投入質量的回歸系數均不具有顯著性,這說明從全國層面的數據看,新建企業或已有企業選址對于上述兩個因素不敏感。
(三)計量模型的穩健性檢驗
國內外學者在分析中國環境規制是否存在“污染避難所效應”時,由于使用不同的環境規制表征指標,導致得出的結論也具有較大差異性。本文采用總污染排放量作為環境規制表征指標,優勢在于政府通常是為了市民的健康狀況而實施相應的環境規制,而普通市民對環境的評判更多是通過所見所感的環境狀況,而不是去衡量單位產值污染物排放情況。總污染排放量這個表征指標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因為少數城市總污染排放量過少可能更多的是因為企業數量少或者總產量少,而不是由于更嚴格的環境規制。因此,為了使得上述計量結果更具有穩健性,本文對于核心解釋變量的環境規制指標采用不同表征方法并再次進行了計量回歸。我們借鑒Lian等(2016)的方法,其用加權處理后的單位制造業產值的污染源排放量來表征環境規制,不僅僅解決了地級市間經濟規模差異導致的偏誤,而且單位除數選取得更加合理。因為污染排放量或治理成本方面往往是由制造業產量直接導致的,與城市總人口的相關性較低,將單位產值的污染物排放量作為環境規制的衡量標準更加合理,具體表示如下:

Eij是在i城市污染物j排放總量,oi為i城市的第二產業產值,UEij代表i城市單位產值污染物j排放量,j是廢水或廢氣。

ΣEj指所有城市污染物j排放總量,Σoi指所有城市第二產業產值總和,Wij為i城市污染物j指標的權重,這個比率可以轉換為i城市每單位污染物j排放量與整個國家每單位污染物j排放量的比率。

為了將Si控制在合理大小范圍內,對其進行了乘數上的放大。Si反映了環境規制的強弱,Si越大,說明在i城市制造業的環境規制越弱,j=1表示工業廢水污染物,j=2表示工業廢氣污染物。應用新環境規制指標后的模型計量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從表8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于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變量log(S)前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但是在加入其平方項后,變量log(S)的系數為正,變量2[log(S)]的系數為負,且兩者在1%的統計水平上均具有顯著性,說明即使采用新環境規制表征指標,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依然呈現倒U型關系。對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為0.147,而2012年我國地級城市中有166個地級市的環境規制程度小于0.147,也就是說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有促進作用的城市有166個。其中,既滿足小于舊環境規制指標轉折點又滿足小于新環境規制指標的轉折點的城市高達131個。這說明對于新建企業采用新環境規制表征和原環境規制表征得出的結果較一致。對于已有企業,新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為0.152,而2013年我國地級城市中有179個地級市的環境規制程度小于0.152,也就是說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有促進作用的城市有179個。其中,既滿足小于舊環境規制轉折點又滿足小于新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的城市高達169個。這也說明對于已有企業采用新環境規制表征和舊環境規制表征得出的結果較一致。
綜合來看,無論是采用原有的總污染排放量指標還是采用新的加權處理后的單位制造業產值的污染源排放量指標,無論是對于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都呈現倒U型,且已有企業環境規制的轉折點均大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的轉折點。
(四)計量模型的內生性檢驗
環境規制與新建企業或已有企業選址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而導致回歸結果出現偏誤,因而本文也對環境規制變量的內生性進行了檢驗。理論上,一方面,由于新建企業的數量遠少于原有企業數量①2013年全國新建企業總數僅占全國已有企業數量的1.36%。,因此其對所在城市帶來的污染排放量也遠少于已有企業;另一方面,由于新建企業通常存在的時間小于或等于一年②因為在統計數據的時候(比如 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其新建企業的建立時間和存在的時間肯定是少于一年的,如果多于一年那開業年份就是2012年了。,在時間方面與已有企業相比,對城市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也相對小。因此,無論是從污染物排放量方面還是時間方面,新建企業對環境規制的影響都很小。實證上,本文采用上述的 log(Si)作為log(TP)的工具變量,首先我們進行檢驗工具變量是不是外生的F檢驗,在確定外生性后,我們再用工具變量進行Hausman檢驗以檢驗log(TP)是不是內生的,檢驗結果如表9和表10所示。

表9 工具變量的F檢驗
從表9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其F檢驗得出的P值均大于5%,因此接受零假設,即它們的工具變量均是外生的。其次,我們采用了Hausman檢驗,利用外生性的工具變量來檢驗log(TP)的內生性,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Hausman檢驗內生性結果
從表10中可以看出,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其P值均大于0.1,在10%的顯著水平下,較大的P值說明接受原假設,即log(TP)是外生的。
綜合表9和表10的檢驗結果,說明環境規制與新建企業或已有企業選址之間不存在內生性,表7和表8的回歸結果是穩健可信的。
五、基于進一步細分樣本數據的分析
(一)基于不同區域細分樣本數據的計量分析
在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無論是經濟發展、產業數量還是環境規制都具有較大的差異性①如2013年,最低的西部地區固原市的GDP僅僅占最高的東部地區上海市的0.847%,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只占上海市的 0.114%。此外無論是采用未加權的環境規制還是加權平均后的環境規制,東部地區三亞市總污染排放量分別只占中部地區四平市和西部地區重慶市的0.0160%、0.0136%。。劉郁和陳釗(2016)指出,我國目前實施的環境污染總量控制政策在東部和中西部存在差異,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獲得的排污指標較少,因此其面臨的減排壓力相對于中西部而言要更大,而為了完成減排目標,東部地區往往實施更加嚴格的環境規制。因此,為了分析不同區域是否因為環境規制不同而呈現出對新建企業或已有企業選址不同的影響,本文按照東部、西部和中部三個區域②東部包括北京、天津、遼寧、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劃分樣本城市(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并進行分組回歸。
基于不同區域新建企業和已有企業細分的樣本數據回歸結果如表11和表12所示。從表11和表12中可以看出,在東部地區,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影響均存在倒U型,且已有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0.234)大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0.198),而實際上,對于新建企業,2012年東部地區80個地級市的環境規制程度大于0.198,占東部地區地級市總數的81.6%。這說明嚴格的環境規制對大多數東部地區新建企業選址已經發揮了負向抑制作用。對于已有企業,2013年東部地區中有 81個地級市的環境規制程度小于 0.234,占東部地區的 82.6%,這說明環境規制的加強依然會對大多數東部地區已有企業選址產生正向促進作用。綜合來看,對于大多數東部新建企業的環境規制已經超過轉折點,而對大多數東部地區已有企業的環境規制還未達到轉折點。

表11 不同區域新建企業細分的樣本數據回歸結果

表12 不同區域已有企業細分的樣本數據回歸結果
在中部地區,對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有正向促進作用,而對于已有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影響存在倒U型,環境規制轉折點為0.227。2013年,我國中部地區中高達74個地級市的環境規制程度小于0.227,在全部中部地區地級市中占比高達69.8%。因此,加強中部地區環境規制不僅不會對企業選址產生負向抑制作用,反而會產生正向促進作用。
綜合上述分區域的回歸結果發現,目前環境規制對東部地區新建企業選址更多發揮抑制作用,而對東部地區已有企業及中部地區企業選址更多發揮促進作用。因此,對于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應實行差別化而非一體化的環境規制政策,對于東部地區新建企業采取適當寬松的環境規制,而對已有企業采取適當嚴格的環境規制,均有利于促進企業選址。喬曉楠和段小剛(2012)研究也發現,對一些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采取適當寬松的環境規制(如分配較多的排污指標),有利于提高全國企業的利潤總額,在全國范圍內促進經濟發展。對于中部地區,適當提高環境規制程度,一方面既有利于該地區的環境狀況,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企業在該地區選址,從而帶動當地經濟發展,進而實現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二)基于不同污染程度細分樣本數據的計量分析
通常而言,污染程度不同的行業給環境造成的影響也不同,重污染行業產生的污染排放量較多,也更容易受到環境規制的監管,而輕污染行業產生的污染排放量比較少,環境規制對其的影響相對也較小。因此,為了研究環境規制對不同污染程度細分行業選址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性,把所有樣本分為重污染行業、輕污染行業①重污染產業包括:造紙及紙制品業(22)、非金屬礦物制品業(31)、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32)、有色金屬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33)、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26)、石油加工及煉焦業(25)、紡織業(17),其余行業為輕污染行業。,并對其細分樣本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13所示。
首先,從表13中的模型13.1~13.4可以看出,對于新建企業,無論重污染行業還是輕污染行業,變量log(TP)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但是在加入其平方項后,變量log(TP)的系數為正,變量2[log(TP)]的系數為負,且兩者在1%的統計水平上均具有顯著性。這說明對于新建企業而言,環境規制對重污染行業和輕污染行業企業選址的影響均存在倒U型。依照上文對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的計算方法,重污染行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為0.205,輕污染行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為0.221,而2012年33.3%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重污染行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多達68.7%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輕污染行業環境規制轉折點。這說明對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對輕污染行業的企業選址發揮促進作用的范圍更廣,對重污染行業企業選址發揮約束作用的程度更強。

表13 不同污染程度細分的樣本數據回歸結果
其次,從表13中的模型13.5~13.8可以看出,對于已有企業,環境規制對重污染和輕污染行業的企業選址也存在著倒U型影響,其環境規制轉折點分別為0.221和0.245,重污染行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也小于輕污染行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2013年66.3%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重污染行業環境規制轉折點,高達87.5%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輕污染行業環境規制轉折點。這說明,環境規制對已有輕污染行業企業選址發揮促進作用的范圍更廣,對已有重污染行業企業選址發揮約束作用的程度更強。
綜合來看,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包括重污染企業和輕污染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均存在著倒U型,且已有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均大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輕污染行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均大于重污染行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
(三)基于不同規模細分樣本數據的計量分析
由于限制或關閉環境污染企業會對當地經濟發展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帶來消極影響,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常常采取不嚴格執法或少嚴格執法方式來達到適當“保護”污染型企業從而維持轄區經濟發展的目的。中央政府為了減少地方政府潛在的地方保護,也特別設立了由原環保部牽頭成立(并由原中紀委、中組部相關領導參加的)代表黨中央對各省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開展的環境保護督察組。2016年11月,中央環保督察組分別向江西、廣西兩省份反饋了督察意見,兩省份均被指存在環保不作為的問題①2012年至2014年,江西樂平市地方政府被指多次用財政資金為36家企業代繳排污費超過千萬元。。為了分析環境規制是否會對不同規模企業的選址產生差異性影響,本文將企業規模按我國的《大中小型工業企業劃分標準》劃分為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兩類②企業年銷售收入和資產總額均在5000萬元以上的為大型企業,其余為中小型企業。,回歸結果如表14所示。

表14 不同規模細分的樣本數據回歸結果

續表14
首先,從表14可以看出,對于新建企業,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中小型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均存在倒U型,大型企業環境規制的轉折點為0.213,中小型企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為0.211。對于新建企業,2012年51.4%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大型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45.8%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中小型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對于已有企業,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中小型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也存在倒 U型,大型企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為 0.231,中小型企業的環境規制轉折點為0.227。對于已有企業,2013年77.4%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大型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69.1%的地級市環境規制程度小于中小型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
綜合來看,無論是新建企業還是已有企業(包括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均存在倒U型,且已有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均大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大型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均大于中小型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環境規制對大型企業選址發揮促進作用的范圍更廣,對中小型企業選址發揮約束作用的程度更強。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中小型企業而言,大型企業能為當地帶來更多的稅收和GDP,因此能夠得到更多的當地政府的直接或間接的保護,從而較少受到環境規制的不利影響。Wang等(2015)也曾得出環境規制對國有企業的選址影響較小這一結果,他們解釋為國有企業有更強大的議價能力,能夠通過談判減少污染支付,而小企業談判能力較弱無法獲得該待遇。一般而言,企業規模越大,談判能力越強。大規模企業可以通過私下交易等減少排污費,而小規模企業往往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六、結論及簡單的政策涵義
本文以 288個地級市微觀的新建企業和已有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匹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2013)和相關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對比分析了環境規制對新建工業企業和已有工業企業選址的影響及其在不同區域、不同污染程度以及不同規模等細分樣本數據方面可能存在的異質性差異。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環境規制對新建企業及已有企業選址的影響均為非線性,即隨著環境規制越來越嚴格,環境規制對新建和已有企業的選址呈現先促進后抑制的倒 U型。在開始階段,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有促進作用,但是當環境規制達到一定的強度之后,就會對企業選址產生負向抑制作用,且已有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大于新建企業環境規制轉折點。對于新建企業,有超過三分之二(68.75%)的地級市2012年環境規制程度小于轉折點,對于已有企業,有超過五分之四(83.68%)的地級市 2013年環境規制程度小于轉折點,中國大多數地級市環境規制強度低于轉折點。穩健性檢驗、內生性檢驗以及細分結果檢驗也支持上述結論。
此外,細分后的實證結果還發現,環境規制對企業選址的影響在不同區域、不同污染程度及不同生產規模企業間具有異質性特征。環境規制對東部地區新建企業選址的抑制作用更多,而對東部地區已有企業及中部地區企業選址的促進作用更多,環境規制對輕污染企業和大型企業選址發揮促進作用的范圍更廣,對重污染企業和中小型企業選址發揮約束作用的程度更強。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從全國范圍來看,樣本期內環境規制對新建企業和已有企業選址的影響均呈現先促進后抑制的倒 U型,且在數據考察期內,中國大多數地級市環境規制強度均低于轉折點,這也意味著通過制定合理的環境規制力度,可以在有效降低環境污染排放的基礎上達到促進企業選址的目的,進而實現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雙重目標。
第二,對于不同建成期企業以及不同區域等細分類型企業,應該實行精準的差別化而非一體化環境規制政策,但當前國家為了治理與人民對于美好生活期待遠不適應的環境污染,實行了日益嚴格且“一刀切”的環境規制政策,例如原環保部 2017年2月聯合六省市地方政府下發《京津冀及周邊地區 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針對電解鋁和化工行業,要求各地采暖季電解鋁廠限產 30%以上,以停產的電解槽數量計,氧化鋁企業限產 30%,以生產線計。但這些停產、限產等具體指標如何在不同類型企業間進行分配和確定,是所有企業統一執行還是根據某些技術指標來精準執行,是按照企業規模、技術水平還是其他標準,這些在文件中均沒有涉及(薄文廣和殷廣衛,2017),這也導致了地方政府在具體操作中往往采取“一關了之”的簡單粗暴方式來落實環境規制,對經濟發展甚至民生的負向影響也逐漸凸顯。
第三,當前我國的環境規制更多是地方政府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權力和行政命令來加以推行和深入,與中小型企業相比,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以及經濟總量中占據更大比例的大企業無疑在與地方政府環境監管部門的博弈中會具有較有利地位,而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對環境監督力量不夠,公民參與環境監督程度也較為滯后,再加上激勵公司主動引領和提升環境保護而非被動遵守環境規制的舉措不足,這些也都使得環境規制變成了政府的“獨角戲”。因此,構建企業、地方政府、社會組織、個人等多方力量共參與、協同互動的網絡化環境治理格局,同時加快環境監督部門的垂直化處理,以有效擺脫地方政府對環境規制執行的不利影響也是應有之義。
第四,對于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環境保護重點和難點的跨區域和跨流域的環境污染問題,在中央政府的理性頂層設計上,也應積極探索并加快構建跨區域的省際橫向生態補償和中央對上游環境正外部性區域的縱向生態補償以及包含相關配套措施在內的區際利益協調與補償機制,以有效構建上游環境保護“不吃虧”和下游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上下游共受益的經濟環境雙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