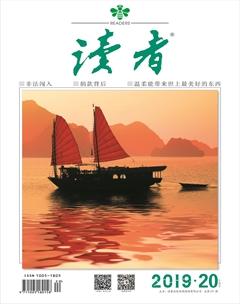非法闖入
〔英〕薩基 馮濤譯
喀爾巴阡山脈東沿的一處雜木森林中,一個人在一個冬夜立在那兒諦視、傾聽,仿佛在等待林中的野獸進入他視線的范圍,進而成為他的槍下之鬼。烏爾里希·馮·格拉德維茨在暗林中巡邏,為的是追蹤一個仇敵。
格拉德維茨家的林地幅員頗廣而且獵物豐富;位于其邊界的這條狹窄、陡峻的林地卻藏不住什么獵物,犯不著在此地浪費彈藥,不過在其領主的領地中卻屬它受到最為審慎的防護。通過他祖父時代的一起著名訴訟,這塊林地才從鄰近的一個小領主的非法占有中被強行奪過來。但被剝奪了所有權的一方卻從未認同法庭的判決,于是這兩個家族之間綿延三代不斷爆發偷獵的爭執以及類似的丑行,相互的敵意日深。到烏爾里希成為族長后,家族間的爭執已發展為個人間的仇恨。假若說世間有一個人使他深惡痛絕,他巴不得這個人倒血霉的話,此人就是格奧爾格·茲納耶姆,敵對家族的繼承人、偷獵的慣犯以及爭議林界的肆意入侵者。要不是這兩個人之間素懷敵意,那場家族間的紛爭可能早就消歇或達成妥協了。他們倆從小就渴望嘗到對方的鮮血,成人后彼此祈禱對方不得好死。在這個狂風肆虐的冬夜,烏爾里希聯合他的守林員一起看護這片黑林,不是為了追捕什么四足獵物,而是監察他懷疑正準備穿越邊界騷擾黑林的盜賊。通常在風暴之夜避居山谷的雄獐,這晚卻像被追的獵物般四處奔逃,而且那些慣于在黑夜中沉睡的動物也顯得有些躁動不安。森林中肯定出現了干擾因素,而烏爾里希可以猜到其所從何來。
他獨自離開山頂的崗哨,沿陡峻的遠坡穿過雜亂的野生矮木林而下,目光穿過樹干四處觀望,耳朵透過狂風的呼嘯、樹枝不斷的擊打聲聆聽,為的是看到劫掠者的身影,捕捉到他們的動靜。他要是能在這個狂野的夜晚,在這個黑暗、荒涼的地點撞上格奧爾格·茲納耶姆就好了,就他跟他兩個人,沒有目擊者——這就是他內心深處最強烈的渴望。而當他繞過一株巨大的山毛櫸時,當真迎面撞上了他在搜尋的那個人。

兩個仇敵各自原地站立,沉默地相互盯視了良久。每人手里都握著一支步槍,每人胸口都燃燒著仇恨,頭腦里都渴望殺戮。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給他們畢生的激情一個完全的發泄口。可一個在壓抑的文明規范下成長起來的人卻無法輕易鼓起勇氣,在話都沒說一句的情況下就將他的鄰居殘忍地射殺,除非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家庭和榮譽。而就在他們猶疑之際,在他們還沒來得及付諸行動時,大自然卻已先發制人,以其自身的暴力將他們倆一舉擊潰。隨著一陣暴風雪猛烈地狂嘯,只聽得他們頭頂咔嚓一聲爆裂,還沒等他們跳到一邊,傾倒的山毛櫸就在轟隆巨響聲中將他們壓在了底下。烏爾里希·馮·格拉德維茨發現自己癱倒在地上,身子底下的一條胳膊完全麻木,另一條深陷在縱橫交叉的樹枝之間,幾乎同樣動彈不得,兩條腿則完全被壓在了傾倒的大樹底下。他厚重的獵靴救了他的腳,否則他的腳早就給壓碎了。他受的傷雖不算致命,可顯然他眼下休想挪動一分一毫,只能坐待旁人來幫助他了。壓下來的細枝劃傷了他的臉,他不得不緊眨幾下眼,把血珠從眼睫毛上擠出去,這才大致看清楚他遭遇的這場飛來橫禍。在他身側就躺著格奧爾格·茲納耶姆,換了正常的情況,他都能伸手夠著格奧爾格了。格奧爾格還活著,在掙扎著,不過顯然跟自己一樣無助,被壓在了樹下。
他們倆四周鋪著厚厚一層碎裂的粗枝與折斷的細枝。
一半因自己還活著而感到慶幸,一半又因深陷困境動彈不得而惱恨,烏爾里希吐出一連串感恩與咒罵的奇怪雜燴。格奧爾格起先被血糊了眼睛,暫時停下掙扎,聽了一會兒,接著滿懷譏諷地短促一笑。
“這么說來你雖然該死,居然還沒死,不過終究還是被壓住了,”他叫道,“壓得牢牢的。哦,真是笑話,烏爾里希·馮·格拉德維茨被他偷來的林子逮了個正著。你這才叫罪有應得!”他再次哈哈大笑,充滿挖苦和憤怒。
“我是在我自己的林地里被壓住的,”烏爾里希反唇相譏,“等我的人趕過來救我們脫險之后,你也許寧肯自己被壓著,也不希望在鄰居家的林地里偷獵時被捉個正著了。你這個無恥小人!”
格奧爾格沉吟了片刻,平靜地答道:“你肯定你的人還能救你出來?今天晚上這個森林里也有我的人,就在我后頭,他們會先找到這里救我出來。等他們把我從這些該死的樹枝底下拖出來后,他們不用費多大勁就可以把這些枝干全堆到你身上。你的人會發現你死在一株傾倒的山毛櫸之下。為了好看,我會將吊唁信送至府上。”
“倒是多謝提醒。”烏爾里希反唇相譏,“我原命令我的人十分鐘后就跟上來的,有七個人應該已經到了,等他們把我救出來,我會記得你的建議的。只不過既然你是在我的土地上偷獵致死的,我想我就不必向尊府送什么吊唁信了。”
“好,”格奧爾格怒罵道,“非常好。我們總算一直打到了死,就你我還有我們的護林員,沒有什么可惡的外人摻和進來。去死吧,你個遭瘟的烏爾里希·馮·格拉德維茨。”
“你也一樣,格奧爾格·茲納耶姆,你個偷林賊、偷獵賊。”兩個人話音里都帶上了可能失算的悲苦,因為心里都明白自己的人可能還要很長時間才能找到這里,而且誰的人先到還說不上。
兩個人都不再掙扎了,因為他們倆都意識到想從壓得嚴嚴實實的大樹底下脫身純屬妄想。烏爾里希現在竭盡全力想將他那條還稍稍能動彈的胳膊伸得離外套的外兜近一些,想把他的扁酒壺掏出來。好不容易掏了出來,他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蓋子擰開,將酒灌進喉嚨里。眼下這酒可真好比天賜洪福!時值深冬,又在戶外,一直飄著零星雪花,喝上點酒感覺就好多了:酒能使傷者感覺暖和,精神也能振奮一下。他不禁帶著點類似憐憫的神情看著他仇敵躺的地方,盡量忍著不讓痛苦和疲憊的呻吟從嘴里冒出來。
“我扔過去,你能夠接到這個酒壺吧?”烏爾里希突然問,“里面可是好酒。人還是要有福同享。我們一塊喝幾口吧,哪怕今晚我們之中有一個得死。”
“恐怕不行,我幾乎什么都看不到。血把我的兩眼都糊住了,”格奧爾格道,“而且我從不跟敵人共飲。”
烏爾里希沉吟了幾分鐘,躺著靜聽讓人煩不勝煩的風聲。他腦子里慢慢形成了一個想法,他眼看著那個正拼死跟疼痛和疲憊做斗爭的人,這個想法也越來越清晰。在痛苦和無力之中,烏爾里希自己也開始覺得此前一直熊熊燃燒的仇恨似乎已經熄滅。
“朋友,”不久他開口道,“要是你的人先到,你愿意怎樣就怎樣吧。說來也算公道。不過就我而言,我已經改變了想法。如果先到的是我的人,我會讓他們先救你出來,把你當我的客人對待。我們自打生下來就像魔鬼一樣,為了這片愚蠢的林子爭執不休,這塊鬼地方被風吹得連棵樹都長不直。今兒晚上躺在這里,我開始覺得我們是兩個大傻瓜——生命中有多少好事,強過為了個分界爭奪得沒完沒了。朋友,要是你愿意幫我將舊怨徹底埋葬,我愿意請你做我的朋友。”
格奧爾格·茲納耶姆卻一直沒搭腔,烏爾里希還以為他疼昏過去了。然后格奧爾格緩慢而激動地開了腔:“要是咱倆并駕齊驅進入市場,整個區域的人都會目瞪口呆,議論紛紛。活在世上的人還沒有一個見過茲納耶姆和馮·格拉德維茨家族的人友好地搭過腔。我們倆今晚如果能一笑泯恩仇,林區的這些居民就都能盡享和平了。如果我們努力使我們的人享受到和平,那外面的人就誰都甭想摻和進來了……你可以來西爾韋斯特在我的屋檐下安眠,我也可以在節慶日到你的城堡里盡情歡宴……我絕對不會再在你的土地上開一槍,除非你請我跟你一起狩獵;你也可以到我那兒跟我一起在沼澤地里獵野鴨。只要我們倆立志維護和平,這整個鄉間誰也休想搗亂了。我原本一門心思地仇視你、痛恨你,可眼下我也改變了主意,就在這半個鐘頭之內。你還請我喝你的好酒……烏爾里希·馮·格拉德維茨,我愿意成為你的朋友。”
有一段時間,兩個人都沉默不語,翻來覆去地想著這次戲劇性的和解,以及將會帶來的所有奇妙的變化。在寒冷黑暗的森林中,狂風被光禿禿的樹枝扯成一縷縷的陣風,從枝干間呼嘯而過,他們倆靜待將使雙方同時獲救的人到達。兩個人都暗自祈禱自己的人先到,這么一來就可以首先向已化敵為友的對方表示關切。
趁陣風暫歇之際,烏爾里希打破了沉默。
“我們大喊救命吧,”他道,“趁這陣間歇,聲音可以傳得遠些。”
“怎么都穿不透樹林和灌木的,”格奧爾格道,“不過我們可以一試。來,一起。”兩個人抬高聲音發出拖長的狩獵呼喊。
“再一起來。”幾分鐘后烏爾里希道,剛才的呼喊并未帶來應答的聲音。
“除了這些瘟風,我什么都沒聽見。”格奧爾格嘶啞地道。
他們又沉默了幾分鐘,烏爾里希突然興奮地大叫。
“我看見有人穿過樹林過來了。他們跟我剛才下山走的是一條道。”
兩個人扯著嗓門再次大喊。
“他們聽見了!他們停住了。現在他們看見我們了。他們正從山上朝我們奔過來。”烏爾里希叫道。
“他們一共幾個?”格奧爾格問。
“看不太清楚,”烏爾里希道,“九個或者十個。”
“那肯定是你的人,”格奧爾格道,“我只帶了七個出來。”
“他們正拼力奔過來,真是好樣的。”烏爾里希高興地道。
“是你的人嗎?”格奧爾格問。
“是不是你的人?”見烏爾里希沒有回答,他再次耐不住性子地問。
“不是。”烏爾里希大笑道,可那笑聲卻是被極端恐怖的事物嚇破了膽的白癡般的笑。
“他們是誰?”格奧爾格著急地問道,一邊竭力睜開眼睛,想看看對方不愿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是狼。”
(兩個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薩基短篇小說選》一書,李曉林圖)